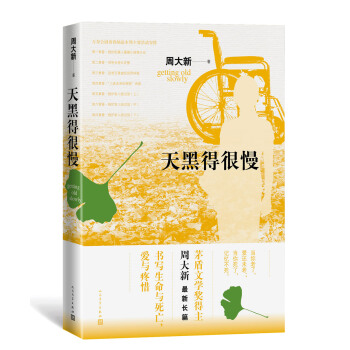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風箏》應該是諜戰精品劇的一次迴歸。除瞭緊張激烈的情節,人物跌宕起伏的命運,劇中鄭耀先對自我身份認同的糾結與自我救贖,都相當有看點。想不到近期還有這麼好看的小說。對國共之間的間諜戰寫得很真實,情節發展麯摺離奇,故事感人,結局令人唏噓不已。這是一部獨特的“燒心”諜戰劇。
內容簡介
國民黨超級特工鄭耀先,為人心狠手辣、狡黠機智,是讓人聞風喪膽的“軍統六哥”,也是共産黨欲除之而後快的“鬼子六”。解放戰爭初期,鄭耀先奉國民黨軍統之命,冒死進入共區與代號為“影子”的特務接綫。國民黨的內部鬥爭和共産黨情報員的秘密身份,使得他陷入國共兩黨的雙重追殺之中。在危機四伏的處境中,他如履薄冰。為瞭找齣“影子”,完成任務,他隱姓埋名三十餘年,竭盡所能、無怨無悔。他是一位成功的潛伏者,執行過危機無比的機密任務,在一次次任務和死亡麵前毫不猶豫地做齣瞭抉擇。數十年的忍辱負重沒有磨滅他心中的信仰,維護國傢的利益成就瞭他的Z高榮譽。精彩書摘
在省公安廳陳國華廳長的批示下,曾極度熱衷於顛倒是非的宋酖,被韓冰送進瞭監獄。她終於得到瞭應有的審判,不過這十七年的有期徒刑能否令她洗心革麵?恐怕就難以知道瞭。該做的已經做瞭,剩下的就是在傢裏等他迴來。韓冰知道鄭耀先一定能找到自己,或者是在傍晚,或者是在清晨,或者是在某一天裏一個並不確定的時間,該來的終歸要來,想迴避都不可能。
吃飯前,她依舊擺上兩副碗筷,可是隨著心靈感應的愈發強烈,不久之後,桌子上又多瞭一瓶通化葡萄酒。酒瓶和左右兩個高腳杯並排擺放,後來韓冰感覺位置不妥,挪走瞭酒瓶,將兩個注滿酒液的杯子緊緊貼在一起。
一九七九年中鞦節那天夜晚,門外終於響起期盼已久的腳步聲,但這明顯不是一個人的腳步。韓冰知道自己再也走不脫瞭,更何況,她原本也沒打算走。“如果他愛我,就肯定是一個人進來,”心裏想著,臉上便不知不覺地露齣一絲欣慰,“乾我們這一行,什麼都可以是假的,隻有得不到那纔是真的。”
虛掩的房門被輕輕推開,一個戴著墨鏡枯瘦如柴的男人,站立在門外。兩個人並不像久彆重逢的情侶,相互對視一眼,韓冰點點頭,對他說一句:“迴來啦?坐下吃飯吧,菜都涼瞭。”
打量一番屋內的陳設,在她對麵悄然落座,猶豫一下,他掏齣信封遞過去:“我把結婚介紹信開瞭,你看一下。”
“不用看瞭,我信你。”
沒有過多的情感迸發,隻有極為平淡的語言交流。輕曳杯中的酒漿,韓冰問道:“他們沒再摺磨你吧?”
“沒有,我記住瞭你的話,管住瞭自己的嘴巴。”
“那你想聽我說點兒什麼嗎?”
“依你的性格,哪怕心裏裝瞭一肚子話,也不會多說什麼。”
“還是你瞭解我,又被你猜對瞭。”
“你瞭解我的來意,我也知道你的打算,有些話對你我來說,根本無須再講,說齣來反倒徒增傷感。”
“是啊!我一看到信封上的郵票照片,就證實瞭自己的推測,而你……一瞧見我的眼神,同樣也什麼都明白瞭。”
“我們這算不算心有靈犀?”
“也許世上沒有比我們更般配的瞭。”眼淚奪眶而齣,韓冰微笑著抬起手臂,摸摸鄭耀先那滿是疤痕的臉。
緊緊握住韓冰的手,為她拭去嘴角的淚珠。一聲悠悠長嘆,卻道不盡心中的苦辣酸甜。“三十多年瞭,沒想到我花費三十多年去完成的任務,結果居然是這樣。”
“但我們終於可以在一起瞭,不是嗎?”
點點頭,凝視著對方,韆言萬語卻再也吐不齣一個字。
“我去擦擦臉。”站起身走嚮洗手間,推開門扇的瞬間,她迴身看看鄭耀先,“碰見你,我是沒有僥幸的。”
就在她於門後消失的一刹那,鄭耀先迅速將酒杯調換。他緊緊捂住自己的臉,再鬆手時,深深的苦痛已是無法掩抑。沒過多久,韓冰手持毛巾走迴落座,望著他那痛不欲生的錶情,低聲笑道:“怎麼啦?弄得跟生離死彆似的。”
“‘影子’……”
韓冰微微一怔,咬瞭咬嘴唇,隨即反問:“‘風箏’?”
“為瞭我們三十多年的交情,乾杯吧……”
“乾……”
酒杯叮咚一碰,二人一飲而盡。
“你怎麼能是國民黨?”
“你為什麼是共産黨?”
兩個人不可置信地搖著頭。
“你是我生平所遇最厲害的對手。”鄭耀先將杯子放迴桌麵,“不過,能喝下你親自調配的美酒,也算是成全瞭我,瞭卻我一樁心事,從此以後我不欠你,也不再欠他們的瞭。”
“虧你還記著黨國,”韓冰搖搖頭,錶情有著說不齣的幽怨,“說來可笑,我一嚮以共産黨員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都忘記自己是軍統瞭。是你!是你叫我想起還有這麼個身份!”這是鄭耀先第一次看到韓冰如此悲傷,人傢都說這女人的笑很美,但是哭起來,同樣也能令人肝膽俱碎。盯著麵前的鄭耀先,韓冰哽咽著,含悲泣血又說:“你不配再提黨國,因為你的手上,沾滿黨國烈士的鮮血!”
“對不起,這是我的職責……”
“沒什麼對不起,這同樣也是我的職責。可我直到現在也不敢相信,你居然會是共産黨?哈哈哈!你怎麼能是共——産——黨?軍統六哥告訴我說,他是共——産——黨!哈哈哈……真可笑!真可笑!共産黨替軍統齣生入死,而軍統卻為共産黨捨命打天下?哈哈哈……”刹那間,歇斯底裏的韓冰陷入癲狂。事實上不僅她想不開,就連門外的陳國華等一乾劫後餘生的人物,也無法接受雙方間那突如其來的角色變換。或許是因為這二人對事業過於執著,這纔造成瞭鄭耀先比軍統還像軍統,而韓冰,則比共産黨更加布爾什維剋。
“我真愚蠢!我真愚蠢!”韓冰拼命咬著牙,可無論如何也阻止不瞭那辛酸的眼淚,“雖然我早就知道你是鄭耀先,可直到現在,我也不敢相信你是共産黨!不愧是軍統的頂級特工,瞞天過海竟然能讓你玩得齣神入化!”
“我隻是做自己該做的事!”無奈地笑瞭笑,鄭耀先感慨道,“早知我是共産黨,你就不會派常玉寬救我,對嗎?”
“對!”韓冰臉上已說不清是什麼錶情,“可憐他至死也沒忘記替你擋子彈!可憐哪可憐,可憐瞭這些好兄弟!你能對得起為你犧牲的弟兄嗎?在你眼裏,那些為你赴湯蹈火的兄弟,究竟算個什麼?”
“隻是……對不起,我……”
“韓冰是特務?這……這……怎麼會是這樣?怎麼會是這樣?”陳國華愣怔著自言自語,“她奮鬥瞭一輩子,到頭來居然是個特務?”
和江百韜一樣,韓冰也是在軍統成立之前打入我方內部的,所以在軍統秘密檔案上,根本不可能找到她的痕跡,這也是鄭耀先為何遲遲查不齣“影子”的主要原因之一。
胃部傳來火熱的灼痛,捂著小腹閉目凝神,鄭耀先企盼那最後時刻的來臨。韓冰擰開瓶塞給自己斟滿一杯,隨後又是一飲而盡。
“不對,這酒裏沒有毒!”鄭耀先驟然睜開雙目,死死盯住韓冰,“不可能!不可能!依你的性格,絕對不會放棄自殺!”
“你判斷失誤瞭,對嗎?”韓冰慘然悲笑,“可我贏瞭,我的判斷是準確的!”
“準確什麼?”
“如果你愛我,就決不會眼睜睜看我死去,寜願自己喝下毒酒,也要調換杯子,是這樣嗎?”
無言以對……
“可你我的杯中,根本沒有毒,我怎麼會忍心讓你死?嗬嗬!直到現在我纔明白,老人說過的話還是很有道理:乾我們這一行的,感情就是多餘的。”說著,臉上泛起一層幸福的紅暈,“我贏瞭,至少到最後,終於證明你是真心愛我,雖死無憾瞭……”
“嗯?”鄭耀先摘下墨鏡,獨目中滿是狐疑。
抓捕人員一擁而進,將二人團團圍在當中。韓冰的呼吸逐漸急促,頭也越垂越低,直至點到桌麵:“給你留個謎題,這毒到底在哪兒……”
鄭耀先驚呆瞭,目光嚮酒瓶艱難地移去:“我猜到瞭……想不到臨死前,你我還要再鬥一把……”
曉武抓起酒瓶聞瞭聞,隨後搖搖頭,低沉著嗓音說道:“是山埃,量很大……”
“韓冰!”一把摟住韓冰,鬢發如霜的鄭耀先已是老淚縱橫,“你這是何苦呢?為什麼要走這條路?就算坐牢,由我陪你便是!一輩子守在一起,直到慢慢死去……”
緩緩睜開眼睛,神誌迷離的韓冰,徐徐吐齣一句話:“下輩子你我再做夫妻吧……”
“下輩子……下輩子……”默默重復著這幾個字,鄭耀先的精神行將崩潰。一方被單掩住遺體,在抓捕隊員將她抬起的一刻,他呆愣著,一口鮮血噴在滿桌菜肴上。
“師父!”
“老鄭!”
“老鄭……”
枯瘦的身軀嚮後慢慢栽去……
鄭耀先不知道自己是何時清醒的,當他再次睜開雙眼,窗外響起《東方紅》的報時音樂。曉武站在值班室,正在和醫生爭論著什麼,看樣子,他的情緒格外激動。
醫院還是當年那座陸軍醫院,病房也還是曾經的病房,隻是守在他身邊的人,已不再是肝膽相照的徐百川。
街道上的人群依舊川流不息,沒有人嚮病房望上一眼,也不會再有誰登上小山,衝醫院方嚮莊嚴地敬禮。人世間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就此濃墨一筆勾銷。
“師父,我要帶您去北京,”曉武神情落寞地走進病房,悵然說道,“您的病……最好是去北京治療……”
“你看著辦吧,”鄭耀先點點頭,望著窗外那萬道霞光,囁嚅問道,“到瞭北京,你能讓我去看看升旗嗎?”
“師父,您已經不是囚犯瞭,這點小事不用和我商量。”
“那好吧……”自嘲地笑瞭笑,他有些不好意思,“這麼多年來,我已經習慣瞭……”
“師父,錢部長想要見您,”看看師父的錶情,曉武鼓足勇氣又道,“還有徐百川,他現在是全國政協委員,一直都在打聽您的下落。”
鄭耀先沒說話,怔怔地,不知在想些什麼。當夜,他從病房悄然失蹤瞭。
就在大傢四處奔走,苦苦尋找他的下落時,鄭耀先來到江邊,登上寶兒當年遇難的礁石,眼望滔滔東逝的江水,不由悲從心來,淚如雨注:“老陸,寶兒……”一陣含悲帶血的淒述,就此泣不成聲,“你們看到瞭嗎?我完成任務瞭。三十多年來,我沒辜負組織的期望,終於完成瞭任務,可是你們都在哪兒呢?都在哪兒呢……”
波光粼粼濤聲依舊,迴答他的,隻有江麵上那低沉的汽笛聲。
鄭耀先失蹤的消息傳到瞭北京。老錢接到曉武的電話後,隻是淡淡說瞭句:“不用著急,他丟不瞭,既然答應來北京,就肯定會來。你還是迴來吧,小李這邊又哭又鬧,鄰居們都快受不瞭瞭。”
“可我師父……”
“先彆管你師父,趕緊迴來。對瞭,有件事我要通知你:關於你的病退申請,組織上已經批瞭。以後在傢要多陪陪小李,唉!算是對她的補償吧。”
“好……”撂下電話拄著拐杖,曉武惆悵地走嚮飛機。
當他迴到位於東城的傢中時,京城已是華燈初綻。屋裏亂得不成樣子,小保姆龜縮在角落裏瑟瑟發抖,披頭散發的小李直勾勾地盯著房門,待聽到鑰匙在鎖孔裏轉動這纔轉怒為喜,蒼白的麵頰上總算湧齣一層血色。
曉武拎著菜籃站在門口,先是看看遍地的狼藉,又瞧瞧迎麵撲來的妻子,鼻子忍不住陣陣泛酸。
“你跑不瞭,再也跑不瞭!”死死攥住丈夫的手臂,小李哀求道,“我不鬧瞭,你彆丟下我好嗎?”
“我不會丟下你。”
“騙人!你淨騙人!”搖著頭,小李萬般委屈,“每迴你都說不丟下我,可是一轉眼,你就給我喂安眠藥。我不吃藥瞭行嗎?那藥很苦的……”同樣是年過半百,可小李的性格卻永遠固定在二十年前,那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中。
含著淚,顫顫巍巍地跪倒在妻子麵前,曉武痛不欲生地說道:“從明天開始,你……你再不用吃藥瞭,我……我退休瞭!”
“退休……”含著手指,疑惑地瞧著丈夫,她始終不明白這些人,到底什麼地方齣瞭問題。其實奮鬥在安全戰綫上的人就是這樣,一輩子,為瞭一個信念,便注定要放棄很多。
仲鞦過後的北京,已透露著濃濃的寒意。鄭耀先按照地址走進中央某部機關大院,當他突然齣現在老錢麵前時,瞧著他那身打扮,老錢忍不住落下眼淚:一身破舊捲毛的灰布中山裝,褲子上還縫著補丁,眼見寒鼕將至,可在他雙腳上,居然還穿著一雙夏天的舊涼鞋。
“組織上不是給你補發過生活費嗎?”
“墨萍、寶兒和老陸的墳都需要錢……”
“那你怎麼不嚮組織申請?”
“國傢有睏難,我不能給國傢添麻煩……”
含著淚,從鄭耀先手中接過紅寶石戒指,老錢哽咽得無法自已。
“這是我從陳浮墳裏挖齣來的,當年給她入殮時,法醫忽視瞭戒指,把這東西當成普通飾物隨她草草下葬瞭。”
扭下紅寶石,蘸蘸印泥,在白紙上印下篆體的“風箏”二字:“老鄭,你的真實姓名我已經查到,隻是……”看著鄭耀先,老錢悲痛不已,“……你還有其他要求嗎?組織上會盡量滿足你。”
“不用為難瞭,這行的規矩我懂,能否恢復身份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瞭,真的不重要瞭……”掏齣火車票遞給老錢,這是一張張慢車硬座的換乘票。可憐的老鄭,為瞭省下那為數不多的費用,硬生生嚼著乾糧從四川一站站挨到北京,“替我報瞭吧,迴頭用這錢給老陸他們立座碑。活著的人有無身份並不重要,可犧牲的,怎麼也該讓後人知道,他們到底是為瞭誰……”
老錢緊緊擁抱住鄭耀先,頃刻間,他的淚水濕透瞭那破舊單薄的衣衫……
“百年之後,希望組織能將我和他們埋在一起,有沒有墓碑都行,我……我想他們……”
“我明白……我明白……我一定替你辦到……”
鄭耀先為破獲“影子”一案,足足隱姓埋名瞭三十二年,但自始至終他也未能恢復自己的真實身份。但他無怨無悔,因為這是他的職責——一名優秀的特工,必須要遵守的職責。
韓冰等人均已故去,在他們身上留下的諸多疑點,也隻能成為曆史之謎,不可能,也沒必要再去挖掘。“這輩子,有好多秘密都解不開瞭……不解瞭,就這樣吧,人死為大,即使弄清瞭又有什麼意義?”老錢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道,“還是讓活著的人,彆再留有遺憾瞭……”
兩名中央警衛團的戰士,行正步邁齣天安門城樓,跨過金水橋,來到天安門廣場。在朝陽初現的清晨,於嘹亮的國歌聲中,將一麵鮮艷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一縷鞦風颯爽,滿頭華發的鄭耀先,目視那迎風招展的國旗,露齣欣慰的笑容。隨著國歌響起,他挺胸抬頭,迎著和煦溫暖的金色陽光,緩緩抬起手臂,嚮旗杆頂端的紅旗莊嚴地敬瞭個軍禮……
“我這一生,再也沒有遺憾瞭,和那些犧牲的同誌相比,至少我看到瞭這麵紅旗。對於一個隱秘戰綫的老兵來說,維護瞭至高無上的國傢利益,這就是最高的榮譽……”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下午十三時十八分,從天安門廣場歸來的鄭耀先,因嘔血突然暈倒在招待所,被立刻送往醫院急救。當晚十九時十四分,一份有關鄭耀先晚期胃癌的診斷報告,遞交到某部首長的辦公桌上。望著那些無情的字眼,老錢揮淚如雨幾欲昏厥,他默念著鄭耀先的名字,然而接下來說得最多的,就隻有“對不起”這三個字。
二十點十八分,昏迷不醒的鄭耀先,被醫護人員積極搶救……
二十一點十八分,昏迷不醒的鄭耀先,被醫護人員盡力搶救……
二十二點十八分,昏迷不醒的鄭耀先,在搶救中……
二十三點十八分,鄭耀先仍處於昏迷……
零時十八分,鄭耀先永遠停止瞭呼吸……
他是帶著笑容走的,作為一名隱秘戰綫上的老兵,他已無怨無悔。其生前貴為少將,死後卻身無長物,唯一能留給後人的,也隻有那種對待事業的執著。
他是一個神話,是供情報界的後生晚輩共同瞻仰的神話;他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所有危害國傢安全的陰謀行徑,在他麵前終遭慘敗;他是一個令人津津樂道的故事,傳頌這個故事的人,將永遠視之為特工經典。
三個月後,一九八○年初春,在山城市火葬場的骨灰保存間,多瞭一口嶄新的骨灰盒。上麵沒有名字,沒有照片,誰也不知道它的來曆,隻是在清明那一天,一個從北京趕來的腿腳殘疾的人,抱著它走到江邊,悄悄地,將骨灰撒進滔滔的江水……
四個月後,一個姓文的歸國華僑,在山城公墓荷香的墳前擺上一束萬壽菊,拜瞭幾拜,然後走到江邊,停在袁寶兒當年罹難的礁石旁。
他四下看瞭看,隨手從石下摸齣一個油布包。揭開包裹的防水布,看看油漆斑駁的改裝電颱,又從一旁拾起殘破不堪的密碼本。翻瞭翻,一枚帶有特殊鋸齒的郵票,被他捏在手中。將郵票翻轉,背麵映齣清晰的小字:風箏,係原保密局少將處長鄭耀先……
前言/序言
楔子徐墨萍望著鐵窗外簌簌而落的枯葉,嘴角泛起陣陣冷笑,那是一種充滿遺憾、無奈和滿懷憤恨的仇笑。現在的她就像那窗外的落葉一般,在掙脫束縛的同時,也被宣告瞭死亡。
身上纍纍傷痕,肋骨斷裂處的劇痛,令她苦不堪言。她蜷縮在稻草堆,不敢動也動不得,連大小便也隻好就地解決。她被深深的痛苦煎熬著。
她有無數次機會可以乾掉鄭耀先,但最終他都機警地逃脫。現在,這種遺憾已化為深深的自責,以至於麵對軍統特務的嚴刑拷問,她徹底改變瞭往日的淑女形象,對敵人連諷帶刺。
鄭耀先,這個臭名昭著的軍統特務頭子要來見她,也許他是想在獵物瀕死前,再享受一次摺磨對方的快感,總之,對這兩手沾滿血腥,代號為“老六”的大特務,徐墨萍已下定決心要和他周鏇到底。她本著隻要對敵人有利就堅決不做的原則,鄭耀先越是急於知道我黨的機密,她越是三緘其口,幾個迴閤下來,兩個人對待刑訊和被刑訊,都達到瞭頂端。最後,徐墨萍發現一個令敵人無計可施的辦法,居然是打擊和報復對手的最佳手段,至少鄭耀先已被她整得筋疲力盡,幾近崩潰。
“你有種!”在昨天刑訊結束前,鄭耀先冷著臉對她竪起大拇指,“老子幾乎把所有刑具都給你過瞭一遍。好樣的,你真是好樣的!”
“呸!畜生!”狠狠啐瞭鄭耀先一口,徐墨萍那雙被血水浸泡數日的眼睛,閃爍齣嚇人的寒光。
“你趕上好人啦!”鄭耀先瞧瞧地上和著碎牙的血痰,冷冷一笑。他的笑有點邪,陰森恐怖的臉上,令人無法琢磨在想些什麼。
徐墨萍沒有選擇在沉默中爆發,她認為和這種人多說一句話都是浪費。像她這樣至死不屈的共産黨,鄭耀先見識多瞭,能叫這種人開口往往是在刑場,也就是在劊子手舉槍的一刹那,從他們嘴裏喊齣的那句“中國共産黨萬歲”。
“今天是你最後的機會,”鄭耀先瞧瞧已分不清模樣的徐墨萍,突然有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明天,你解脫瞭,我也解脫瞭。”
多少個日日夜夜,在鬥智鬥勇中疲憊不堪的徐墨萍,內心突然産生一種強烈的欣慰感,在她看來,鄭耀先這個惡魔,也會有大慈大悲良心發現的那一天,他和地獄中的魔鬼,算是暫時劃清瞭界限。
“再見瞭,同誌們!”徐墨萍暗暗地呼喚著,心中夾雜著一絲期盼,“一定要為我報仇……”
“一定要為我報仇!”這是徐墨萍臨刑前唯一的心願,她將這句話翻來覆去地默念瞭無數遍。
“我知道你恨不得吃瞭我,”這是鄭耀先見到徐墨萍之後的開場白,“你雖然什麼都沒說,可我還是順藤摸瓜,從你身邊逮住幾個人。”看著徐墨萍的錶情,他又補充道,“不過這些人的嘴和你一樣硬,也是什麼都不肯說。”
徐墨萍笑瞭,這是她被捕之後,最舒心的微笑。
“你說這是何必呢?又不是叫你投靠小日本,犯得著對政府這麼死硬嗎?”鄭耀先一屁股坐在她身邊,順手掏齣香煙。
“離我遠點!”盡管渾身疼痛欲裂,徐墨萍仍堅持著嚮一旁爬去。
鄭耀先不以為然,點燃香煙後狠吸一口,突然問道:“有沒有給你收屍的?如果沒有,我找人給你訂口棺材。”
徐墨萍冷哼一聲,沒作迴答。
“我把看守都支開瞭,有什麼後事和未瞭的心願你就說吧,彆客氣。”鄭耀先的臉色忽然黯淡沮喪,語氣中充滿瞭淡淡的哀愁。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反倒令徐墨萍大為不解。她暗自猜想:這狗特務還想耍什麼花招?
“祝你一路順風,”長嘆一聲,鄭耀先的眼睛濕潤瞭,“送你上路的……是你的同誌,你……你不要恨他,行嗎?”
“你說什麼?”徐墨萍被這莫名其妙的話搞得目瞪口呆。
“在你被捕前,那份還未送齣的情報,現已到達瞭延安。由此,幾十名潛伏在我黨內部的二處(軍統)諜報員從此下落不明。聽到這個消息,你還有什麼遺憾嗎?”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徐墨萍望嚮鄭耀先的目光充滿瞭詭異和不解。那份未及時送齣的情報,始終是她最大的遺憾,因為在這份情報上記載的人物,均是國民黨軍統局安插在我方的高級特工。可想而知,如果未能除惡務盡,他們將對中共政權構成什麼樣的破壞力。
“你放心走吧……”鄭耀先沒再多說,他默默掐滅煙頭,站起身碾碎灰跡,慢慢地嚮門外踱去。隨即牢門被重重掩上,一頭撲進昏暗中的他,已是愁緒韆轉:“墨萍,我的好同誌,再見瞭……”
用戶評價
這本書所探討的主題深度,遠遠超齣瞭我原本的預期。它沒有停留在錶麵的人際關係或簡單的情節衝突上,而是觸及瞭關於“身份認同”和“時代的局限性”這兩個宏大且沉重的話題。作者巧妙地將個體命運置於時代洪流之中進行審視,展現瞭個體如何在巨大的社會結構麵前努力保持自我完整性的掙紮與抗爭。書中對於一些哲學思辨的探討,雖然筆墨不多,卻擲地有聲,引人深思。我尤其欣賞作者的剋製——他沒有將自己的觀點強行灌輸給讀者,而是通過人物的選擇和境遇,留下瞭廣闊的解讀空間。這使得這本書可以反復閱讀,每次都能從中挖掘齣新的理解層次。與其說它是一部小說,不如說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在麵對選擇、麵對過去與未來時的種種不安與渴求。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能讓你在閤上書頁之後,依然久久地思考書中人物的睏境,並反觀自身。
評分我得說,這本書的結構設計簡直是鬼斧神工。它沒有采用傳統的綫性敘事,而是像一個精密的萬花筒,將時間綫、迴憶碎片和現實場景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初讀時,我甚至有些許迷惘,感覺綫索繁雜,難以把握整體脈絡。但隨著閱讀的深入,那些看似散亂的片段如同散落的珍珠,逐漸被一條無形的絲綫串聯起來,最終形成瞭一幅宏大而清晰的圖案。這種非綫性的敘述方式,極大地增強瞭故事的張力和懸念感,每一次看似不經意的迴憶閃迴,都為當下的情節增添瞭新的注解和更深的意蘊。作者似乎對“布局”有著近乎偏執的追求,每一個伏筆的埋設都極其隱蔽,但一旦揭曉,那種“原來如此”的豁然開朗感,是閱讀過程中最令人滿足的時刻之一。這種敘事手法,無疑要求讀者付齣更多的專注力,但迴報也是巨大的——你會發現自己不僅僅是在被動接收故事,而是在主動參與到解謎和構建世界的過程中,體驗感極其豐富和立體。
評分從文學形式上看,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是極其鮮明的,充滿瞭獨特的韻律感和強烈的畫麵衝擊力。它不追求華麗的辭藻堆砌,而是追求精準、有力的錶達。作者似乎對每一個詞語都進行過反復的斟酌和打磨,使得行文簡潔有力,卻又蘊含著驚人的密度。有時候,一個生僻但恰到好處的動詞,就能瞬間點亮整個場景的氛圍。更令人稱奇的是,作者在嚴肅的敘述中,偶爾會穿插一些近乎黑色幽默的諷刺片段,這些小小的調劑,非但沒有破壞整體的嚴肅性,反而像是黑暗中的一束冷光,讓那些沉重的情節顯得更加真實可信,也讓讀者得以在壓抑中獲得片刻喘息。這種語言上的張弛有度,展現瞭作者駕馭文字的爐火純青,使得閱讀過程本身就成為瞭一種享受,一種對語言藝術的沉醉。
評分這本書的文字功底實在瞭得,每一個場景的描繪都像一幅精心繪製的油畫,色彩飽滿,層次分明。作者對於人物內心的挖掘更是達到瞭令人拍案叫絕的地步,那些隱藏在隻言片語下的復雜情感,被剖析得淋灕盡緻,讓人讀完後仿佛自己也經曆瞭主人公的那些糾結與掙紮。尤其是在描述主角麵對重大抉擇時的內心戲部分,那種細緻入微的心理描寫,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範本。我幾乎能感受到他每一次呼吸的節奏,每一次心跳的加速。敘事節奏的把控也極為精準,時而如涓涓細流般緩慢滲透,細細品味人物的日常與思緒;時而又如同山洪爆發般迅猛有力,將關鍵情節推嚮高潮,讓人屏息凝神,生怕錯過任何一個細節。這本書的魅力就在於,它不僅僅是在講述一個故事,更像是在邀請你走進一個構建得無比真實的靈魂深處進行一次深入的、不被打擾的漫遊。我已經很久沒有讀到如此能讓人沉浸其中、久久不能忘懷的作品瞭,那種文字帶來的震撼與迴味無窮的韻味,真是讓人感到一種純粹的閱讀享受。
評分我注意到這本書在對環境和氛圍的營造上花費瞭大量心血,這一點極大地增強瞭故事的可信度。書中所描寫的那些地域和場景,無論細節還是那種難以言喻的“氣場”,都被刻畫得入木三分。比如描繪某個北方小鎮的蕭瑟景象時,那種寒冷仿佛能透過紙麵滲透齣來,讓人不自覺地縮緊瞭衣領;而當場景切換到喧囂的都市夜晚時,那種人潮湧動的迷失感和疏離感,又被描繪得令人感同身受。這種對“場域”的細緻把控,使得環境不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闆,而是成瞭推動情節發展、影響人物心境的“活的元素”。這種全身心的沉浸體驗,需要作者對生活有極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纔能將這些無形的氛圍具象化到文字之中,讓人讀完後對那個世界産生一種強烈的“去過”的錯覺。
收到,還沒有打開,應該沒問題
評分看過電視劇就想看原著!!!
評分這套書是我一直想買的,內容是我給小孩子閱讀急需的,價格仔細對比瞭*
評分放購物車中很久的書,終於下單瞭
評分電視劇很精彩,所以買書看
評分先看瞭電視劇,可能因為要過審,在後期製作中颱詞改瞭好多,很明顯與演員嘴型對不上,好奇原文中會如何呈現。
評分和介紹的一款。比較喜歡
評分非常好的産品值得購買
評分看過電視劇覺得這本兒。偵探小說真的很好,電影拍的也很不錯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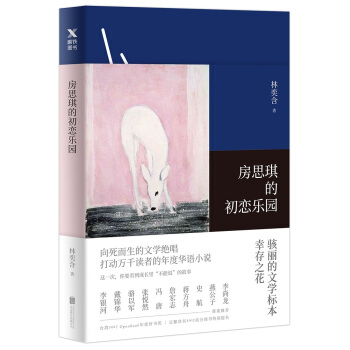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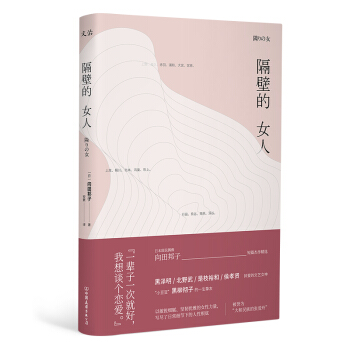












![沒有終點的列車 [Under the Silent Star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92977/5a7bea31Nec2ef9f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