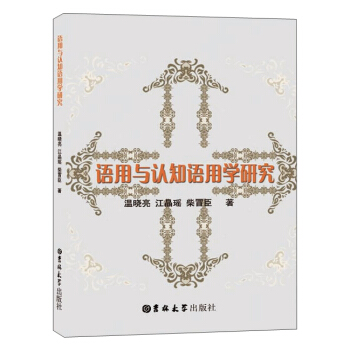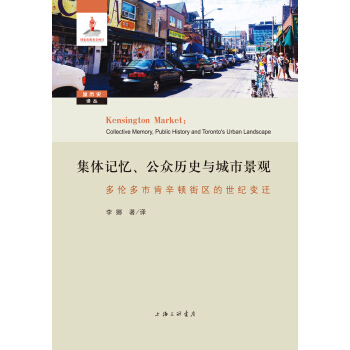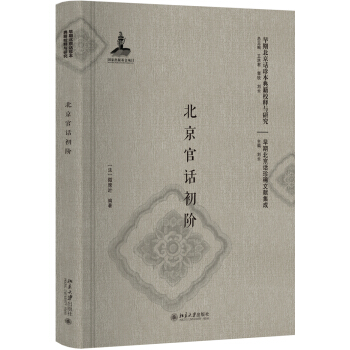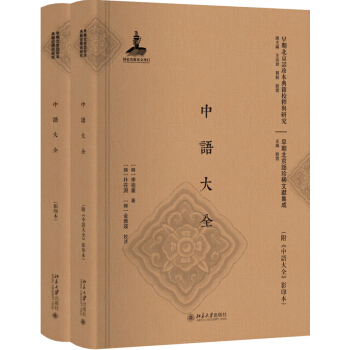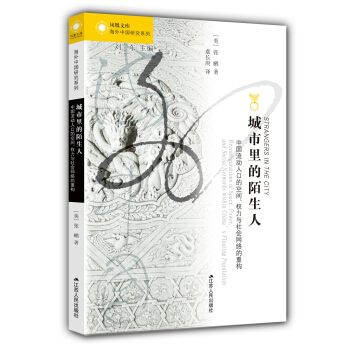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作者从地域研究、应用研究、灾害研究、认知研究、宗教研究等多角度出发,尝试建构出细致的民族走廊以及走廊中羌族社会·文化的地域社会综合研究范式,借以展示岷江上游羌族地域的社会、文化实质,同时也对汶川地震后羌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思考。作者简介
张曦,男,四川理县人,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阅读与写作》《佛教精华故事大观》《台湾小说鉴赏辞典》《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中国少数民族风土漫记》等。//张曦,羌族,1964年生于四川省理县薛城镇,1982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学习,1986年留校任教。1996年进入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学习文化人类学,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到母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
目录
民族走廊的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路径——以藏羌彝走廊为例藏羌彝走廊中的文化残存·“毒药猫”
民族走廊中藏族传统文化与观光开发
羌族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
灾害·文化生成与羌族民间故事
自主与非自主的羌族移动
汶川“5·12”地震灾害的记忆及叙事
地域变迁与影像记录
羌族民俗宗教与民间传承
20世纪90年代前羌族聚居区茂县社会镜像
后记
前言/序言
自 序步入人类学学科的世界,现在看来大概是我个人的宿命了。若以终极结果论来看宿命论的话,其实宿命论也并不是消极的、偶然的所谓单方面的命运接受论,其中也包含了个体的诸多积极的努力。自1996年在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以外国人研究生身份开始学习人类学课程,到2006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再到今年,屈指算来已有21年,以小时计超过了18万个小时。这期间,通过课堂学习、田野调研、阅读、写作,以及与国内外人类学同行的交流、学习,再加上回国后的本硕教学,一不小心就跟人类学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只拿“光阴再难留”之类的惯用句来说,似乎逝去的岁月就有些苍白无力了。王铭铭先生曾言,要把人类学做到绝望,其实在我而言,根本就没有绝望二字,永远都是期望,一直都在追求把自己的人类学研究、教学能够做到自己的期望值。
1986年大学毕业之时,其实根本没有要读研究生的打算。毕业后留校预科部汉语文教研室任教,担任“阅读与写作”与“中国古典文学”两门课的教学,虽有徐殿文老师、陈重老师等诸位前辈的细心指点,但因自身原因,终究觉得教学进步不大,尤其是在需要厚重积累的古典文学上,感到积累还是相当薄弱。那时幸得本科的古典文学老师裴家麟先生容许旁听他的研究生课程,于是常常去北大燕园先生住处听先生深入细致的讲读。同时,课上课下与裴先生的弟子蓝旭、杨昌牛诸人也时常交流。在这段听课学习经历中收获颇多,也感觉到自己还是有读研继续深入学习的必要,也就是从那时起大致有了考在职研究生的想法,但是1993年的赴日打断了这个计划。
赴日后因诸事蹉跎了两年时光,待语言有所进步、生计稍安时,觉得还是应该进入日本的大学继续学习,一来是期望在日本获得另一个上进的台阶,二来是了却在北京时就有的读研的愿望。但当时对日本的大学毫无认知,只知道清末中国留学生最多的早稻田大学。不得已,尝试着问了身边的日本朋友,他们大都说日本最好的大学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而且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历史研究最强,话里话外都透露着这两所大学可不容易考的意思。因京都在日本关西,所以大着胆子决定去东京大学试试运气。
由于本科阶段是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里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时得裴家麟、王扶汉、李佩伦等诸先生教诲,选修课甚至还有《日语学习》杂志主编李思敬老师的课,加之80年代时代清净,无他事纷扰,因此自认为学习也有所获。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近现代散文家丽尼作品的艺术特色分析,由鲁迅研究者王冠英老师指导。王老师是忠厚长者,指导论文时意见中肯,也使我获益匪浅。因此在申请进入东京大学时也想偷懒,希望在东京大学中国文学学科的研究生课程中继续进步。那时虽然没有网络,但也没费多大周折,就打听到了一位东京大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方面比较有名的教授。然后急忙去书店买回一本他的书,借助日汉辞典仔细阅读了一番。其诸多观点对于只接受过80年代国内的近现代文学研究教育的我而言,当时不单单是新颖,而且展现出了另一种思考维度。于是在1995年的10月用当时还十分蹩脚的日文写了一封信,大致表示了景仰他的研究,非常愿意跟随他学习、研究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并按照日本的习惯,随信还附了一个已贴好邮票的回信用信封,可是我始终没有等来回信。2008年夏天我有机会在北京见到了这位老师,一起吃饭时,我只是告诉了他我差点去他所在的文学部读研究生。
眼看着离东京大学的入学申请期限越来越近,偶然的一天,与时在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文化人类学专业学习的民大校友王永红通电话时,跟她说了文学部还没有回音。她却说你也是少数民族,还不如来人类学研究室学人类学呢。由于当时也没有预备要申请别的学校,所以病急投医也慌,于是在申请期限到来之前,给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文化人类学专业寄去了申请材料。这期间还麻烦大学时代的学兄杨春先生从中央民族大学给我寄来了我的大学本科成绩单,也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黄成龙先生帮我找人写了一封入学推荐信。后来才知道东京大学的人类学教育始于1954年,其教学、研究的历史还不短,而那时正是中国大学院系调整,社会学等学科被取消的时期。
1996年2月17日早上7点,我在东京武藏野市的蜗居里接到了末成道男老师打来的电话,先生先用汉语、后改日语、再换英语告知我4月1日起可以跟随他学习。我道谢后的心情相信大家都能猜出。随后没两天,我就收到了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的外国人研究生的入学许可书。3月下旬去学校报到时,刚进东大驹场学校校门,就遇到了早我两年进入大学院地域文化专业学习的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79级的杨志强。待我办完报到手续,他已经摆好酒菜在校园内的驹场学寮他的房间等我了。就这样,1996年的4月我开始了文化·社会人类学的学习。
因末成道男老师的研究室在本乡校区东洋文化研究所,所以也就跟随末成老师,在东京研究所的8楼度过了最初的两年学习时间,其实也是强化日语口语、日文表述以及恶补学科知识的两年。在东京大学的外国人研究生学习阶段只需要听指导老师的课,老师们往往也只开一门课,因此只需每周去一次学校。末成老师又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帮他整理他的诸多资料,其实就是将容量小的磁盘里的资料转存到大容量磁盘中,所以我还需要去研究所工作一天,当然工资待遇不错,高于我当时打工的小时工资。
末成老师的课面向硕博士研究生,1996年主要是精读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中国东南宗族组织》)一书的原版。于我而言这也是第一次接触人类学英文原著,诸多论述大多不懂,只是囫囵读下,师生的讨论也难以插言,对于中国东南部的社会、文化、历史也没有任何知识积累,因此困惑也多。还好在北京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无非是找书来读,再者就是认真听末成老师及同学的讲述,再以中文、日文混合体做笔记。周复一周地重复着,渐渐地有些入门了。末成老师的课一直有众多旁听者,有校外的、有校内的,中日学生的比例大致是五五开。因此除了王永红、麻国庆、王建新外,也自然就认识了常来听课的外校的何彬、谢荔等中国学生。正是因为听课者多,讨论踊跃,因此课程也常常延时。下午3点开始的两小时的课,有时要上到晚上8点。一旦延时,晚饭自然就得在离研究室最近的本乡校区的学士会馆解决,10多个人的饭,学生们象征性地一人出500日元,剩下的就归末成老师负责了。也记不清吃过老师多少次饭了,记忆犹新的是,麻国庆教授当年的结业论文最终发表后,一众人又去了学士会馆,其间喝掉了末成老师珍藏的两瓶25年绍兴老酒。
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上课的两年间,也随末成老师参加过一些学术会议,见识过日本及其他国家(西方居多)的一些人类学学者,算是打开了眼界。最难忘的会议应该是1997年在本乡校区山上会馆由末成老师主办的日、中、美、蒙、越五国人类学会议。会议上蒙古、越南、中国的参会学者都用母语发言,再由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翻译为日语。广东省民族研究所马建钊学兄(中央民族学院79级历史系毕业生)也来参会,他是自己从广东带了日语翻译。而日本、美国的学者用英语发言,发言内容又需要翻译为日语,再翻译为蒙古语、越南语及汉语。结果一到讨论、提问阶段,各种语言交错,使得时间大为延长。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末成老师告诫我和王永红千万要加强英语口语的练习。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我的英语口语进步都不大,很有些辜负末成老师了。
1997年本应参加进入博士前期课程的考试(相当于中国直博的硕士阶段),但因末成老师远在越南做田野调查,留的河内的传真号码也无法接通,我的申请材料因无导师盖章,所以一直无法提交,只好另外申请了研究生延期。不久末成老师回东京,但只说了一句话:“再在我这里读一年吧。”就这样我又跟着末成老师在本乡校区多待了一年。当然,这一年也没白过。除了继续上课读书讨论外,还参加了末成老师任大代表的日本台湾顺益原住民研究会的“台湾原住民研究资料丛书”的翻译工作,大概是末成先生认为我是学中文出身,也把丛书总序的翻译任务交给了我。至今仍记得先生在总序中所言:“日本的台湾研究以殖民地统治为背景而展开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因此而将过去的调查及调查成果都看作是毫无价值,并加以抛弃的态度也非正确。尽可能客观地把握这些材料并使之流传后世,才是弥补前人所付出牺牲的可行之路。”近年来的由中生胜美、三尾裕子等学者所展开的日本殖民地人类学研究充分证明了末成先生言之不虚。
1998年1月,在提交两年研究生学习结业论文后,我参加了人类学的博士前期课程入学考试,通过了有200余人参加的初试,随后进入复试圈,最后与大川谦作、森田敦郎等一起通过了复试。2月底收到了入学通知书,此时方才明白末成老师让我多待一年的真意。在这一年里我不仅在专业上有了一些进步,日语的表述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结业论文也就成了我第一次用日文写作的论文。同时也要感谢末成老师给我安排的日本同学的细致的考试辅导,当时主要用的是弘文堂出版的石川荣吉编的《现代文化人类学》(『現代文化人類学』)与合田涛先生编的《现代社会人类学》(『現代社会人類学』)两本书,这两本书现在在日本也堪称人类学经典之作。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其中清水昭俊老师的“文化的构成”、须藤健一老师的“性差”等章节内容。可惜的是这位日本同学后来选择了去法国留学,直至今天,我都没有再见过他,也没能感谢过他。在进入正式课程学习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因我在国内小学只学了5年,初中、高中加起来只学了5年,大学前的学习年限不够日本的12年,在入学资格审查时被追问到,好在在我之前已有中国留学生的先例,略作解释也就过了。
然而正是此年,末成老师已年满60,依照当时日本公职人员的退休年龄规定(2006年后改为63岁)必须退休,因此先生不得不离开东京大学,转去了私立大学东洋大学任教,同时也介绍我转入伊藤亚人老师门下。退休前的一次见面,末成老师郑重表明,自此以后,欢迎来听课,欢迎来探讨问题,但是有关博士论文的写作问题一概免谈,我也知道这也是为了尊重伊藤老师。依照东京大学大学院不成文的传统,当自己的指导老师退休去别的大学后,如果学校在东京,原来的学生得去新学校给老师捧场,所以1998年4月至1999年2月,又与王永红、田村和彦等去东洋大学旁听了末成老师一年的课,这期间也认识了先生在东洋大学新招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年近50岁、好学的斋藤和尚,他也时常邀请大家去他在千叶县的寺庙,也就是在那里,我见识到了原来只在教科书上读到过的日本老妇人佛教信徒的“观音讲”。“讲”在日本原来是基于同一信仰的一种较为松散的社会组织,也是一种社会互助的组织,没成想日本社会中历史非常长的“讲”能在东京附近的现代社会中观察到。
1998年3月开学前我去紧靠东京繁华地涉谷的驹场校区(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所在地)伊藤老师那里报到。此时方知,其实在我申请外国人研究生资格时,他也看到了我的申请材料,只是末成老师先要了我。自此以后,伊藤老师无论是开会还是聚会在介绍他的学生时,总会指着我说,这是羌族学生,羌在甲骨文上都有记录,自然他知道此羌非彼羌。另外,当时我的日语敬语运用十分糟糕,加之在居酒屋打工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市井用语,因此在课堂上有时会显得与教室严肃的学习气氛不合,十分滑稽。每当此时,伊藤老师就会打趣称一个在山上待惯的人,能学会汉语还在北京教书,已经很不错了,敬语嘛,慢慢来。
由此开始的驹场校区硕士课程是两年内至少需学到20个学分,第一年还需去东洋大学白山校区听末成老师的课,加之还需去新宿、涉谷的几个语言学校教授汉语,所以外国人研究生时代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一周有四天需要坐“井之头线”电车去学校。每到星期五因为我上午在早稻田外国语专门学校教中文,所以下午西装革履去研究室上课时,刚开始大门口的校警以为我是老师总要向我敬礼,后来又见我着便装频繁出入,再以后就不敬礼了。 硕士课程的两年中除伊藤老师的发展人类学的课程以外,我还选修了山下晋司、关本照夫、并木赖寿、福岛真人等先生的课程,诸先生都懂英文,因此英文文献偏多,要占70%以上。学习也就变成了不分白天黑夜的英文、日文文献的阅读、理解,好在那时还算年轻,也就挺了过来。
最后在完成硕士论文写作时,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的第一日语翻译李志勇先生外派东京,正好与我同住在久我山的“太田纪念寮”(在1999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前,此寮只接受从北京来的中国留学生),经中日联合培养的北师大毕业生李志勇先生的日语口语及书面语都十分优秀,因此拜托他最后逐章把关、修改,好在他从繁忙的公务中抽出了休息时间,总算在提交期限前一天全部完成了有点像样的论文稿。上交论文那天一大早赶到学校时,研究室里都是众同学忙碌的身影,制作封面目录的、改订参考文献的、打印装订的,本来空旷、冷清的复印室显得十分拥挤,这也是一年一度难得的景象,早早就交了论文的同学大川谦作诸人一大早也来帮忙,所以非常佩服较我年轻得多的大川谦作诸同学学习、写作的游刃有余。
在通过了论文答辩后,便开始等待后期课程的入学通知书,当然它如期而至了。随后便是长达6年的博士阶段的学习。博士课程的学分获取因有充足的时间,已经不像硕士阶段那样紧张了,所以有时间去听了一些非人类学专业的课程,也算对得起不菲的学费。由于读博时我已年过35,没好意思去申请35岁以下才有资格的任何奖学金。只是在第三年因为成绩全优获得了东京大学一年的学习奖励费,每月75000日元,可惜的是此奖励只奖一次。因此学费需要辛苦教中文挣出,不能浪费,要用听课听回来。上博士课程时,在福岛真人老师的课上获益匪浅,其实他也是2000年刚拿到博士学位。福岛老师当时讲授ST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就是关注现代性的制度的社会人类学,人气很高,几乎所有的硕士、博士课程的学生都来,因此作为教室的会议室也挤得满满的,讨论也十分热烈。另外印象更为深刻的一门课就是名和克郎老师的“社会人类学”,据名和老师自己所言,他在以前申请去喜马拉雅地区做田野调查时,当时的审查官中根千枝找来一位印度学者与他聊天,当发现他听得懂印度学者的英语时,马上就批准了他的田野调查申请。因为名和老师刚在研究室开课,加之其专业是喜马拉雅研究,所以只有我和大川谦作选了他的课。课上的精读材料是利奇(E.R.Leach)的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师徒三人轮流坐庄,一周读讲一章,算是我读得最为辛苦的一本书了。尽管三人努力,如果没记错的话,课堂上也只读到了第三部分的第九章“Myth as a Justification for Faction and Social Change”(为组织派系及社会变迁辩护的神话)。为了读懂利奇,我还去东京神保町著名的旧书街买回了他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的长岛信弘翻译的日文版,原价800日元的书,最后以5700日元买下,被店主狠宰了一刀。在东京大学承蒙末成道男先生、伊藤亚人先生指导学业,也幸得诸先生教示,同时尚有与日本、美国、韩国、荷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各位同学的积极互动,在井之头学寮也常与埃及、孟加拉国、法国的其他专业的留学生相互学习,我虽愚顽,但日日浸淫,也有进步。
学习人类学自然少不了田野调查,我的第一次人类学田野调查是1996年7月开始的,也就是入学后的3个月的暑假时,先跟现在京都大学的池田巧老师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沙德乡做木雅语调查,之后自己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当时准备去看看费孝通老师的弟子徐平博士的调查地羌锋村。但在汶川县威州镇时,得知附近的秉理村有一场传统葬礼,所以直接爬坡去了秉理村。拥有近100户人家的秉理村在汶川县威州镇西南的半山上,距离约6公里,徒步需一个多小时。村里因交通事故,刚刚失去了一位即将任教小学的年轻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因此村子的整体气氛很压抑,丧主家是我朋友的亲戚,因而同意了我的拍照请求。虽然刚刚接受过初步的田野训练,出发前也读了克兰(J.G.Crane)与安格洛西诺(M.V.Angrosino)的《人类学田野调查》(Field Projects in Anthropology),然而实际观察与记录时,却是手忙脚乱,完全抓不住非正常死亡者的葬礼案例的头绪,只是记录了葬礼中自己所观察到的部分,以及一些简短的问答,连秉理村的基本状况都没能把握。回到东京,在课堂上给大家汇报时,被各位听课者提问问到崩溃,那时候才知道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的不易。不想末成老师在总结时只是慢条斯理地说,第一次谁都会那样,多做做就好了。实际也如末成老师所言,就是在不断的重复实践中,我的田野工作慢慢找到了状态。其后在课堂上及平时大量人类学民族志原本的补读,对于民族志撰写的前期材料的广泛收集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我也能够较为专业地展开观察、材料搜集、访谈等工作了。再之后的德格印经院调查、羌族地区的调查也都较为顺利了。
经2002年2月至2003年3月一年多的茂县黑虎乡鹰嘴河上寨、理县桃坪村、理县休溪村的调查后,我将在四川、北京搜集到的相关纸质资料打包寄回东京,随后回到日本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本以为可以在2005年3月毕业,博士论文写作的艰难事先真没想到,其实在2005年的年初才写出初稿。2003年、2004年我还按惯例做了追踪调查。博士论文的撰写从始至终,很让伊藤老师操了不少心,章节内容数度调整。伊藤老师去英国开会时,也带着我的初稿,抽空就作修改。2009年不幸因病去世的並木赖寿老师(1948—2009)更是从日语语法到专业表述细心批注,博士论文的初稿上几乎每页都有先生留下的红色笔迹,仿佛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藤野先生,这本初稿我至今珍藏着。並木赖寿与末成道男老师都是东京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镇,都精通中文,也都来过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对中国留学生也是出奇地关照及负责。並木老师的一部分骨灰还被他的学生杨志强带回了贵州被供奉着。
2005年的初夏,博士论文大致成形,连同归国的护照签证复印件(一整年田野调查的时间证明)提交给了研究室,请求“中间发表”(相当于中国的预答辩)。还好“中间发表”通过,匿名评审的老师们都还认可论文成形稿,并提出了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由此正式进入黑白颠倒的写作冲刺阶段。其间,韩国学兄朴东诚又从首尔回到东京来赶写他的博士论文,因为都住在东京大学的井之头学寮,我们也经常切磋探讨,他虽然做的是日本渔村的研究,但在研究方法、框架方面对我也有诸多启发。所以回国后每次去韩国开会时,都愿意在首尔跟他喝上几杯。2013年6月底,正好伊藤老师也来首尔作“脱北者”的口述史调查,师徒三人在首尔畅饮了一晚。由于日语书面语十分复杂,因此也请了我的中文班学生、《朝日新闻》的编辑竹内纯先生帮助做了语法、表述的订正。这是一次面对面的、讨论式的修正,对我而言相当于是日文的深度学习课,热心的竹内先生还帮助我做了些章节结构的调整。
自然,最为关心论文写作的就是伊藤老师了,因为2006年他面临退休,而且已经决定好了要去冲绳的琉球大学继续教书,因此想在退休时把我以及坂垣龙太、朴东诚送出校门。因此时时追问写作进度。2005年7月的一天,朴东诚学兄去伊藤老师那里讨论论文,伊藤老师问张曦在干什么?学兄说在写论文,每天晚上都看见他在煮面条。伊藤老师说面条哪有营养,结果学兄只好开着老师的车来寮里接上我,去外面爆吃了一顿烤肉。其实我吃的面条是有豆腐、澳大利亚牛肉丸子、蔬菜、乌冬面的混合物,伊藤老师知道后才不担心我的营养问题了。最难忘记的是2005年9月的一天,半夜三点多接到伊藤老师的电话,问在干什么?我说正在写论文呢。伊藤老师说我就在你楼下,我急忙下去把他请上楼,他一看两台电脑开着、榻榻米上摆了一地的书,终于放心了。接着又跟我讲了导论中重点要强调的问题。这是伊藤老师第一次来我的学生宿舍,也是最后一次。当他看到我满屋书架时,还是吃了一惊,其实在一楼还有一间6个榻榻米的房间堆满了我的书呢。这些书我最后都用集装箱运回国了。后来伊藤老师夫妇来北京,我当着师母的面问他,为什么半夜来监督我写论文。他说,第一,全家人都去了欧洲,就剩他一个人在东京,所以时间自由;第二,如果半夜都不写论文的话,估计白天更没时间写了。就在这样的支持及监督下,终于在答辩申请期限内完成了论文。我自己也没想到最后竟是厚厚的一大本。
然后就是答辩的等待,那是一段不太好过的时间,我估计答辩时我会被批得很厉害。答辩前那几天除了准备可能被问及的问题的时间外,大多是愁眉难展。当时学寮里还有来自中国台湾的学友蔡易达,年纪较我长,其政治主张虽偏向民进党,但与我私人关系非常好。有天他开导我说,你都花了6年时间了,还怕被骂两小时?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答辩那天,本以为是狂风暴雨的节奏,实际上是风和日丽,诸位答辩老师大多只指出细节上的不足,并提供了切实的修改意见。答辩老师之一的东京女子大学的学姐聂莉莉也指出了论文的诸多不足,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再针对诸位老师的意见作出进一步修改后,我提交了博士论文最终版,3月23日拿下了从前在北京时都没想过要的学位。
2006年5月归国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在诸多繁杂的手续办理完毕后,7月中旬正式回归母校——中央民族大学,至今也有11年了。回国之初,似乎有些如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所称的“归国文化休克”(Reentry culture shock),也许是在日本待的时间太长的原因吧,感觉与自身周边环境格格不入,难以获取共感,加之又换了一个从头到尾都是在日本学的专业,专业表述也存在差异,因此又花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来适应自己的母校环境。现在想来,也觉背寒,多亏当初没去别的学校,幸而是在自己待过11年的母校,还有诸多老师、学友以及从前的同事,不然就不知道要休克、调整到什么时候了。后来在《科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留学生回国:海归与重返文化休克》,方知自己不是特例,而是大多数的归国者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不适应的问题。
在东京大学十年间,囫囵吞下诸多东西,加之自身喜欢阅读各类杂书,因此更加没有头绪。所写博士论文,虽然篇幅长、涉及面广,但也算是为了学位的应景文章。唯一可取的是田野经验的积累。归国后,非常感谢母校的本科及研究生课程的教学,特别是本科生的教学,使我在与“归国文化休克”斗争的同时,得以较为系统地整理了从前所学,从中也获取了诸多论文写作的线索。也得益于中央民族大学以潘蛟老师、张海洋老师、王建民老师为首的强大的人类学团队以及国内外的诸多同人的学术刺激。特别要感谢清水昭俊老师、池田宽二老师在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授课,山下晋司老师、伊藤亚人老师来中央民族大学做学术报告,在中国我也能继续得到老师们的教示。
拉拉杂杂地写下上述我自己的求学经历,是要鞭策自己,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还有诸多地方需要向我的老师及周边的同学、朋友学习。尤其是自己还带有硕士研究生,更是要向末成道男、伊藤亚人、並木赖寿老师学习。将自己这些年与藏羌彝走廊相关的研究所得汇成本书,一是向诸位老师、同学、同人、朋友乃至于学生汇报,二是鼓励自己继续坚持、坚守。过去的21年已经不会再回来,但留下的雪泥鸿爪便是这本小册子。
张 曦
2017年8月9日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虽然低调,但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完全超越了外在的包装。它给我的感受是沉甸甸的,不是那种阅读完就丢在一边的快餐读物,而是需要反复品味、时常翻阅的工具书。作者的学术功底毋庸置疑,但更可贵的是他将这些复杂的概念转化为清晰易懂的论述,这种能力是真正的大师级的表现。读到某些关于地域发展和文化认同的篇章时,我甚至会忍不住去查阅地图和更多的历史资料,那份由阅读激发的探索欲,是阅读一本好书最美好的体验之一。这本书,无疑是近年来我读过的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
评分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搭建得极为扎实,但阅读起来却丝毫不枯燥,这实属难得。作者的洞察力非凡,他总能从看似琐碎的日常现象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原理。这种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完美结合的能力,使得整本书充满了智识上的魅力。每一次翻页,都像是在解开一个又一个谜题,那种抽丝剥茧的快感让人欲罢不能。我特别留意了书中对特定仪式和习俗的探讨,那种详尽的考据和独到的解释,让我对这些文化现象有了全新的认知。这本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重塑。
评分说实话,刚拿到书时,我对它抱持着审慎的态度,毕竟市面上同类主题的书籍太多了。然而,这本书很快就用它独有的深度和广度征服了我。作者的笔触非常老练,他没有陷入故作高深的文字游戏中,而是用一种非常坦诚和直接的方式与读者进行对话。他提出的许多观点都极具启发性,仿佛是为我内心深处长久以来的困惑提供了解答。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记录,更是在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归属的群体和解,并寻求一种可持续的共存之道。我强烈推荐给所有对人文社科感兴趣的朋友们。
评分阅读体验上,这本书带来的冲击是深远的。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偏向学术研究的著作,但它读起来却像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充满了人情味和故事性。作者似乎拥有某种魔力,能够穿透表象,直抵事物的本质。他对于社会群像的刻画尤其精彩,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与坚持,都让人感同身受。我尤其欣赏作者那种不带偏见的叙述方式,他以一种近乎人类学家的严谨态度,去观察和记录,却又充满了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读完后,我感觉自己的世界观被拓宽了许多,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乍一看有些朴实,但我翻开内页才发现,这简直是一场视觉与思想的盛宴。作者的文笔流畅而富有张力,对细节的描摹入木三分,仿佛能让我置身于那些遥远的地域,亲身感受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脉络。他并非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巧妙地将历史的厚重感与现代的社会变迁交织在一起,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尤其是关于文化传承的那几个章节,那种细腻的情感流露,让人读来不觉心潮澎湃。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精妙的句子,思考它们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也极具匠心,逻辑严密,层层递进,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作者的思辨能力所折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