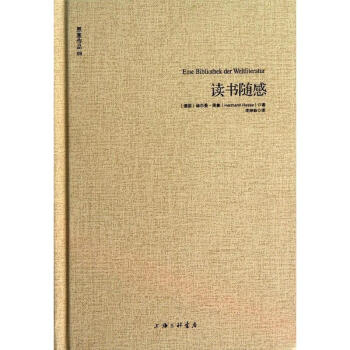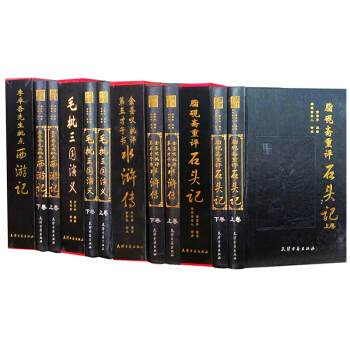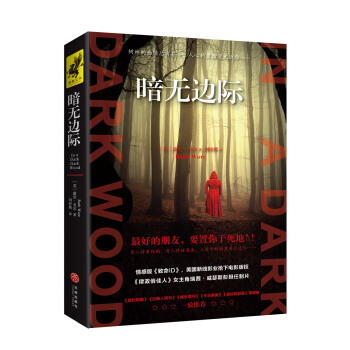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犯罪小说作家诺拉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偶然的一天,她收到一封婚前女子单身派对的邀请函,女主角是她失联了十年的曾经最好的朋友。48小时后诺拉在病床上醒来,脑子里只剩下有人被杀的模糊记忆。一片诡异的树林,一栋玻璃房屋,几个神经质的派对人士,诺拉时刻都在后悔来参加派对,但为时已晚。
漆黑寂静的晚上,好像有人潜入,也许是人,也许不是。屋子里的人莫名紧张,有人开了一枪,倒下的却是婚礼女主角的未婚夫,也是诺拉十年前的男友。
有人死去,有人受伤,有人自杀,而诺拉成了嫌疑人……
作者简介
露丝·韦尔 Ruth Ware在苏塞克斯郡的路易斯长大,从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后搬到了巴黎,之后在伦敦北部定居。她曾经做过女服务员、书商、英语老师和发稿文宣,已婚并育有两个小孩。
《暗无边际》是露丝·韦尔的首部悬疑推理小说,一经出版即引发广大读者一致追捧,被媒体称赞为“完美承继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风格”。
新作《十号舱的女人》(THE WOMAN IN CABIN 10)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21大脑记不清楚。它讲故事。它填补缺口,把那些幻想当作记忆植入其中。
我必须得努力得到真相。
我不知道自己会记起发生过的事,还是我希望发生过的事。我是个作家。我是个专业的骗子。很难知道什么时候收手,你懂吗?你在故事里看到一个缺口,你想要把它填上,用一个原因和一个动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而我越是紧逼,真相就越多地在我手指下消散……
我知道自己猛地惊醒了。我不知道当时几点,但天色昏暗。我身旁的妮娜端坐在床上,深色的眼睛大睁着闪闪发光。
“你听到了吗?”她低声说。
我点点头。楼梯口有脚步声,然后是一扇门轻轻打开的声音。
我把羽绒被向后推,抓起睡衣,此时我的心在嗓子眼儿跳动着。我想起厨房门大开,雪里的脚印。
我们之前应该把房子其他地方检查一下的。
我在门边站着听了片刻,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克莱尔和弗洛正站在外面,她们大睁着眼睛,脸被吓得煞白。弗洛举着枪。
“你们听到什么了吗?”我小声说,尽可能把声音放到最低。克莱尔明显地点了一下头,指了指楼梯,手指向下戳着。我努力听,试图让自己颤抖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平静下来。一阵剐蹭声,然后是清晰明确的“哐”的一声,就像是一扇门轻轻关上的声音。楼下有人。
“汤姆?”我做了个口型。但正当我这么做时,他的房门打开了一条缝,汤姆的脸朝外面窥探出来。
“你们……那个声音?”他低声说。克莱尔严肃地点了点头。
这一次没有开着的门,没有风。这一次我们都能听到:有人穿过铺着瓷砖的厨房,走过门厅的镶木地板时清晰的脚步声,然后是明确的一只脚轻轻踩在第一级台阶上的咯吱声。
我们设法聚拢成一小团,我感觉到有谁的手摸索着我的手。弗洛在中央,举起了枪,尽管枪口剧烈地抖动。我伸出另一只手把它扶稳。
楼梯上又传来“咯吱”一声,我们所有人倒吸了一口气,然后楼梯中柱旁一个上到一半的人影映在俯视森林的平板玻璃上。
是一个男人——高个子男人。他穿着某种连帽衫,我看不到他的脸。他正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手机屏幕在黑暗中发着鬼魅的白光。
“滚开,别烦我们!”弗洛尖叫道,枪响了。
一声灾难性的“砰”震耳欲聋,伴随玻璃碎裂的声音,枪像马匹一样向后反冲。我记起——我记起有人摔倒。
我记起自己抬头看到——这讲不通啊——巨大的平板玻璃窗碎了——玻璃向外溅落到雪上,哗啦啦落在木制楼梯上。
我记起那个楼梯上的男人哽住一声惊呼——比起疼痛,似乎更多的是被吓了一跳——然后他一下子摔倒,像电影里的特技演员般砰然跌下楼梯。
我不知道谁开了灯。但它们让高高的门厅充满了令我畏缩的光明,我遮住双眼——我看到了。
我看到结了一层霜的苍白的楼梯上溅落着血渍,看到破碎的窗户,还有那个男人滑落到一楼的所经之处缓缓留下了的长长血迹。
“我的天哪,”弗洛呜咽道,“枪——上了膛!”
当护士回来时,我正在哭泣。
“发生了什么?”我支撑着说,“有人死了——请告诉我,请告诉我谁死了!”
“我不能告诉你,亲爱的。”她看起来由衷地抱歉,“我希望我能,但我不能。不过我把米勒医生带来了,让他来看看你。”
“早上好,利奥诺拉。”那个米勒医生边说边来到床边,轻柔的声音里充满怜悯。我想要挥拳打他和他那该死的同情心。“我很抱歉我们今天有点儿悲痛。”
“有人死了,”我非常清楚地说道,努力保持呼吸均匀,避免大口喘气和啜泣,“有人死了,没人要告诉我是谁。警察正坐在外面。为什么?”
“现下我们不要为那个担心——”
“我就是担心!”我大喊道。走廊里的警察转过头来。医生伸出一只抚慰的手,轻拍着我盖在毛毯下的腿,他拍的方式令我想战栗。我瘀肿带伤,穿着一件后开口的病号服。我失去了尊严,连同所有其他东西一起。别他妈的碰我,你这个屈尊俯就的混蛋。我想回家。
“听着,”他说,“我理解你很难过,警察将有望给你一些答案,但我要给你做个检查,确保你可以跟他们讲话,而只有你冷静的时候我才能那么做。你明白吗,利奥诺拉?”
我默默点点头,然后当他检查我头上的敷料,对照着机器上的读数查看我的脉搏和血压时,我把头转向墙。我闭上眼睛,让屈辱消退。我回答他的问题。
我的名字是利奥诺拉·肖。
我二十六岁。
今天是……这里我不得不求助了,护士给了我提示。是星期天。我到这里甚至还不到十二小时。也就是说,今天是十一月十六日。我想比起失忆这该算是迷乱。
我,我不恶心。我视力没问题,谢谢。
是的,我对某些记忆的恢复遇到了困难。有些事你不该被迫想起。
“呃,你似乎恢复得极好。”米勒医生最后说。他把听诊器挂到脖子上,小手电放回上衣口袋。“夜里所有的观察结果都没问题,你的扫描也让人放心。记忆的问题有一点儿令我担忧——失去冲撞前几分钟的记忆是很典型的,但听起来你的问题似乎比那更往前一点儿,对吗?”
想到整个晚上爆炸式涌入我脑海的零零散散、断断续续的影像:树、血、晃来晃去的照明灯,我不情愿地点点头。
“嗯,你也许会发现记忆开始回来了。并非所有导致记忆故障的原因——”他避开了“失忆症”这个词,我注意到了。“——都归结于物理创伤。有些更多的是和……压力有关。”
不久后,我第一次抬头直视他的眼睛:“你是什么意思?”
“呃,你懂的,这不是我的专长——我从事的是和头部物理创伤有关的工作。但有时候……有时候大脑压制那些我们没太准备好去应对的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应对机制,如果你愿意的话。”
“什么样的事件?”我的声音冷冰冰的。他笑了笑,又把手放回到我的腿上。我抑制住畏缩的冲动。
“你经历了艰难的时刻,利奥诺拉。现在,我们能打给什么人吗?你想要什么人陪你吗?你妈妈已经收到通知了,我理解,但她在澳大利亚,对吗?”
“没错。”
“其他亲属呢?男朋友?同伴?”
“没有。拜托……”我咽了咽口水,没道理再拖下去了。不知道带来的烦闷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了。“拜托,我现在想见警察。”
“嗯。”他站着,看着他的图表。“我不确信你能应对,利奥诺拉。我们已经告诉过他们你不适合回答问题。”
“我想见警察。”
他们是唯一会给我答案的人。我不得不见他们。我盯着他,此时他假装研究眼前的图表,拿着主意。
终于他呼出一口气,一口沮丧的半叹气式的长气,把图表塞进了床脚的支托里。
“那好。他们最多只能有半小时,护士,我不想有任何有压力的东西。如果肖小姐开始觉得会谈困难……”
“明白了。”护士轻快地说道。
米勒医生伸出手,我握了握,试着不去看自己胳膊上的擦伤和血渍。
他转身离开。
“哦——等等,对不起,”当他走到门口时我脱口而出,“我能先冲个澡吗?”我想见警察,但我不想像这样面对他们。
“泡个澡。”米勒医生说着简略地点了点头,“你头上有敷料,我比较不想让你碰到它。如果你保持头在水面之上,是的,你可以泡个澡。”
他转身走了。
解开连在机器上的所有东西花了好长时间。有传感器、注射针,还有我两腿之间的失禁垫,当我把腿摆到地上时,感觉到它的体积,这让我羞愧地忽冷忽热。我夜里尿床了吗?没有强烈的尿味,但我不能确定。
当我站起来时护士把一只胳膊伸过来,尽管我想推开她,却发现自己对此感激涕零。我不愿意承认,当我蹒跚着痛苦地走进浴室时,那么重的倚靠在她身上。
浴室里,灯自动打开了,护士放了洗澡水,帮我解开病号服的带子。
“剩下的我可以自己来。”我说。想到要在陌生人面前脱衣服,即便是专业人士,也让我很难为情,但她摇了摇头。
“我不能让你没有帮手地进浴盆,抱歉。如果你滑倒……”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在我已经受创的头上又是一次重击。
我点点头,离开那个令人厌恶的成人尿布(我还来不及担心它是不是脏了,护士已经快速地把它移走了)。我任病号服落到地板上,光着身子瑟瑟发抖,尽管浴室里热得让人流汗。
有股味道,我惭愧地意识到。我有股恐惧加上汗和血的气味。
当我摇摇晃晃地走进浴盆时,护士握着我的一只手,在我放低身体浸到滚烫的水里时她抓住了扶手。
“太烫吗?”当我倒抽一口气时护士马上问,我摇了摇头。不算太烫,没有什么能太烫。如果能用热水给自己杀菌消毒,我愿意。
终于我仰靠在水里,用力发着抖。
“我能不能……我想要一个人待着,拜、拜托。”我尴尬地说。护士深吸了一口气,我能看出她就要拒绝了,而突然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忍受不了他们的监督,他们的好意,他们持续不断的注视。“拜托,”我粗暴地说,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不会在六英尺的水里淹死的。”
“好吧,”她说,语气里透着不情愿,“但连想都别想试着自己出来——你要拉绳子,我会进来帮你。”
护士走了,把门留下刚好一个微开的缝隙。我闭上眼睛,沉入冒着热气的水里,把门外警惕的她屏蔽,把医院的气味和声音,还有荧光灯的嗡嗡声屏蔽。
当我躺在浴盆里时,双手摸过所有的伤口、刮痕和瘀青,感受着血块和结痂在我手掌下面变软、溶解,我努力回想是什么让我双手沾着血跑步穿过树林,我努力回想。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承受真相。
在护士帮我从浴缸里出来后,我一边看着自己熟悉的身体还有上面不熟悉的伤口和缝针的痕迹,一边轻轻地用毛巾把自己擦干。我两条小腿上有割伤。它们既深又凹凸不平,似乎我曾跑着穿过荆棘或是带刺的铁丝网。我的双脚和双手上都有伤口,或是赤脚在玻璃上跑留下的,或是为了遮挡朝脸部飞来的碎片留下的。
终于,我走到镜子前,拭去水蒸气,自从事故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
我从来不是引人侧目的类型——不像克莱尔有着让人难以忽视的美貌,也不像妮娜以清瘦又有男子气的方式引人注目——但我从来不是一个怪物。现在,当我凝视水蒸气扩散的镜中的自己时,我意识到如果在街上看到自己,我会因为同情或者惊恐而转过身去。
我发际线上的敷料没帮上忙——看起来仿佛我的脑子几乎没放在适当的位置——遍布在我颧骨和额头上斑驳的更小的伤口和擦伤也没帮上忙,它们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的眼睛——两个深红棕色的乌眼青从鼻梁处绽放出来,在我两个下眼睑底下过滤成黑眼圈,经过颧骨以后褪成黄色。
右边的那个很是惊人,左边的好一点儿。我看起来像曾被人用拳头反反复复地捶在脸上。但我活着,有人死了。
是那个念头让我穿上了病号服,系上带子,拖着脚走到外面去面对这个世界。
“在欣赏你的乌眼青吗?”护士安逸地笑了笑,“别担心,它们做完了所有的扫描,没有颅底骨折。你只是脸部遭到一次重击,或者两次。”
“颅,颅底…?”
“头颅骨折的一种。可能会非常严重,但他们已经排除了它的可能性,所以别发愁。车祸后有黑眼圈并不罕见,几天以后它们就会消退了。”
“我准备好了,”我说,“见警察。”
“你确定你能行吗,妞?你不是非得那样。”
“我能行。”我坚定地说。
我回到床上,手拿一杯护士所谓的“咖啡”坐着——除非头部创伤损坏了我的味觉——那并不是咖啡,这时有人敲了敲门。
我猛地抬起头,心怦怦跳着。外面,透过门上带铁丝网的玻璃窗格,一个女警正在微笑。她四十几岁,容貌不可思议地标致,是那种你也许会在T台上看到的经过雕刻般的样子。感觉极端不协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警官不应该有大卫·鲍威1老婆那样的脸?
“进、进来。”我说。别结巴,妈的。
“你好,”她打开门进到房间里,仍然保持着微笑。她有着长跑运动员般苗条的格雷伊猎犬框架。“我是拉玛尔探员。”她的声音温暖,元音是紫红色的,“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些了,谢谢。”好些了?比什么好些了?我在医院,穿着一件没有背面的袍子,顶着两个黑黑的眼睛。我不确定还能更糟到哪
1?译者注:大卫·鲍威,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
儿去。
然后我纠正了自己:我从机器上解绑了,他们也撤走了尿布,显然相信我可以自己小便了。这,的确,好些了。
“我和你的医生们聊了,他们说你或许可以应付回答几个问题,但如果太过了我们可以停止,只要说出来就好。这样可以吗?”
我点点头。她说:“昨晚……你能把你记得的告诉我吗?”
“不记得,我什么也不记得了。”这句话说出来比我的本意要生硬和紧绷。令我恐惧的是,我感到喉咙哽塞,猛烈地吞咽了一下。我不会哭!我是个成年女人,看在那个该死的原因上,不是某个在操场擦伤膝盖哀号着叫爸爸的小孩。
“喂,那不是实话。”她说,没用指责的口吻。她的声音是老师或者姐姐那种温柔鼓励的语调,“米勒医生跟我说你对导致事故的事件很清楚。你为何不从一开始说起呢?”
“一开始?你不想听我童年的创伤等等那些吧,想吗?”
“也许啊,”她不顾医院的规定,坐在床脚。“如果它们和发生的事有关联。要不这样吧,我们为什么不从一些简单的问题开始呢,只是热一下身?你叫什么名字,这个怎么样?”
我挤出一个笑,不是因为她认为的原因。我叫什么名字?我以为我知道自己是谁,我变成了谁。现在,这个周末过后,我不再那么确定了。
“利奥诺拉·肖,”我说,“叫我诺拉就好。”
“那很好啊,诺拉。你多大了?”
我知道她一定已经知道所有这些了。也许这是某种测试,看看我的记忆实际上有多差。
“二十六。”
“现在告诉我,你最后怎么到了这里?”
“什么,到医院里?”
“到医院里,在这里,实际上主要是诺森伯兰。”
“你没有北方口音。”我所答非所问地说。
“我在萨里出生的。”拉玛尔说。她用被拉下水的表情对我笑了笑,告知我这不太符合程序,她应该在提问,而不是回答问题。这是什么事的小预兆,我不太想得出是什么。一个交换:她的一点换我的一点。
只可惜这让我听起来精疲力竭。
“所以,”她继续说道,“你最后怎么到这里了?”
“是……”我把一只手放到额头上。我想揉它,但敷料挡在那里,我怕把它弄歪了。底下的皮肤又热又痒。“我们本来在过单身女子周末,她在这里上过大学。克莱尔,我是说,派对的主角。听着,我能问你点儿什么吗——我是嫌疑人吗?”
“嫌疑人?”她丰富多彩的美丽声音把这个词说得像音乐一样动听,令这个阴冷尖刻的名词变成了优美的音符。然后,她摇了摇头,“在调查的这个阶段,不是的。我们仍然在收集信息,但没排除任何可能。”
翻译:不是嫌疑人——目前还不是。
“好了,告诉我,关于昨晚你记得什么?”她切回主题,像一只非常美丽且有良好教养的猫围着老鼠洞转一样。我想回家。
敷料下面的痂刺痛瘙痒,我不能集中精神。突然我用余光看到了储物柜上没吃的小柑橘,我不得不看向别处。
“我记得……”我眨了眨眼睛,让我害怕的是,我感觉到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我记得……”我猛烈地咽了咽口水,把指甲戳进撕裂带血的掌心里,让疼痛驱散他躺在蜂蜜色镶木地板上往我胳膊上渗血的记忆。“拜托,拜托告诉我吧——谁——”我停住了。我说不出来,说不出来。
我又试了一次。“是——?”那个字卡在我的喉咙里。我闭上眼睛,数到十,把指甲戳进掌心的伤口里,直到整只胳膊因为疼痛而抖动。
我听到拉玛尔探员呼了一口气,当我睁开眼睛,她看起来,第一次,有些担心。
“在把水搅浑之前,我们希望能从你的视角了解整件事。”她最后说,神情焦虑,我知道,我知道她不被允许说出来的是什么。
“没关系。”我勉强说,体内有什么东西正在瓦解、破碎,“你不需要告诉我。哦,天,天啊——”
然后我说不出话了。眼泪流啊流啊流啊。那是我怕的。那是我知道的。
“诺拉——”我听到拉玛尔说,我摇了摇头。我的双眼紧闭着,但我能感觉到眼泪沿着鼻子往下流,刺痛了脸上的伤口。她发出一小声无言的同情的声音,站了起来。
“我会给你点儿时间。”她说。我听到房门“嘎吱”一声打开,然后“啪”地关上了,在两个合页上摆动。我一个人了。我哭啊哭啊,直到眼泪流干了。
用户评价
初读此作,我最大的感受是文字的密度和冲击力。不同于市面上很多追求流畅叙事的作品,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像经过了千锤百炼,信息量大得惊人,需要我反复回味才能真正捕捉到其深层含义。作者似乎钟爱使用一些冷僻的意象和晦涩的修辞手法,构建了一个宏大却又极度私人化的世界观。这本书仿佛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构建一个思维迷宫”,读者需要不断地在作者抛出的线索和碎片之间建立联系,才能拼凑出大致的图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背景设定和哲学思辨,它们就像是深埋在叙事之下的暗流,驱动着整个故事的走向。这本书对读者的智力要求相当高,它拒绝被轻易消费,更像是邀请你进入一场深奥的智力角力。我尤其欣赏作者对时间维度的处理,那种时空错乱感,让人时常分不清此刻是过去、现在还是一个永恒的循环。读完某一章节后,我常常需要合上书本,静坐许久,消化那些沉甸甸的思考,这绝对是一本需要“啃”而不是“读”的书。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个性化”,我感觉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阅读者自身的恐惧和不安。它没有提供明确的道德指引,也没有提供一个能让你安心跳脱出来的“局外人”视角。相反,它把你死死地钉在那个充满瑕疵和缺陷的现实之中,让你去体验那种无力改变既定格局的挫败感。我发现作者在描述那些日常场景时,总是带着一种刻意的、近乎病态的精确性,比如对某种气味的捕捉,或者对特定光线折射的角度的描写,这些微小的“过曝”反而让整个故事的底色显得更加阴郁。我最欣赏它的一点是,它拒绝给予廉价的安慰。当故事进入高潮时,那种爆发不是“释然”,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坍塌”,让人在情感释放之后,留下的只有更深的虚无感。这本书成功地营造了一种“后真相”时代的氛围,你无法完全相信任何一个叙述者,包括那个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上帝之声”,一切都是模糊的、可疑的,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构成了它最强大的魅力。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就像是一座精密的机械钟,每一个齿轮——无论是人物的对话、环境的渲染,还是突然插入的内心独白——都咬合得严丝合缝,共同推动着一个看似永无止境的进程。我发现作者在处理角色的内心冲突时,用了大量的意识流手法,那感觉就像是直接潜入了人物的大脑皮层,看到了他们最原始、最混乱的念头。这种处理方式带来的好处是极端的真实感,坏处则是偶尔会让人感到迷失方向,我好几次得翻回去重新阅读某一段落,才能重新锚定角色的情感状态。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多次出现关于“循环”和“重复”的主题,仿佛命运本身就是一个被写好的剧本,无论角色如何挣扎,最终都会回到原点。这种宿命论的基调,让每一次的努力都显得徒劳而又悲壮。而且,这本书的配乐(如果可以这么比喻的话)是极其低沉的,它没有给你喘息的机会,始终保持着一种紧绷的、几乎令人窒息的张力。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文学尝试,它挑战了传统叙事的舒适区,强迫读者去面对那些不愿触碰的生命本质问题。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极其冷峻,像冰冷的钢铁划过皮肤,留下一道清晰的、但不会立刻流血的伤痕。我注意到作者似乎偏爱使用长句和复杂的从句结构,这使得阅读过程变成了一种智力上的马拉松,每一个句子都需要细细品味其内在的逻辑和情感走向。它不像很多畅销书那样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反而像是在故意设置障碍,考验你的耐心和专注力。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它提供的“哲学后劲”上。读完之后,你可能会忘记具体的情节细节,但那些关于存在、虚无、以及个体在宏大结构下的渺小感的思考会像烙印一样留在你的脑海里,久久不散。这本书似乎在挑战一种普遍的乐观主义,它告诉你,有些痛苦是无法被治愈的,有些黑暗是无法被驱散的,而接受这一点,或许才是真正的“清醒”。我喜欢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它拒绝用任何形式的美化来稀释主题的残酷性,全篇弥漫着一种近乎禁欲主义的克制与力量。
评分这本书的开篇就展现出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压抑感,那种感觉就像是作者把整个人生中的晦暗角落都挖出来,摊在了你面前,毫不留情。故事的主角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读起来让人心惊肉跳,生怕下一秒就会万劫不复。我特别喜欢作者对细节的描摹,那些灰蒙蒙的街道、雨水打在破旧窗户上的声音,都好像能透过纸面渗入你的感官,让你身临其境地体会到那种无助和挣扎。整个叙事节奏非常慢,但这种慢却不是拖沓,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铺陈,让那种绝望感层层递进,直到你几乎要窒息。情节上的转折点处理得极其巧妙,往往在你以为找到一丝曙光的时候,作者又毫不留情地将其熄灭,让人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我猜想,作者一定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他笔下的人物,无论善恶,都带着一种病态的真实感,让你无法轻易地去评判他们,只能默默地跟随他们的轨迹,见证他们的沉沦。这种阅读体验,与其说是享受,不如说是一种煎熬,但正是这种煎熬,让人欲罢不能,想要知道那无边的黑暗尽头,究竟藏着什么。
评分嗯,不错
评分好评,五星。物流速度快,东西包装好。物美价廉!
评分一直相信京东的商品,送货也快很好哦
评分还不错,快看内容简介。。。
评分很好的书,装帧精美,排版合理,字迹清晰,很适合闲暇时好好阅读,收获很多。
评分为周末读书时间准备的
评分很快送达,还没来得及读。
评分很快送达,还没来得及读。
评分京东物流给力,搞活动性价比高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