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阅读经典,就是阅读灵魂,就是把一个人的生活和伟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著名诗人西渡先生编选的这本《名家读新诗》践行的就是这项工作。本书不仅集中了《再别康桥》《死水》等经典诗歌,以及艾青、冯志、北岛、顾城等名家的精品佳作,还将唐晓渡、臧棣、废名等多位知名学者对于诗歌的解读置于文章之后,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质量上乘的精神食粮。
内容简介
中国新诗或称现代诗,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以白话写作,反映现代中国人的经验,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一种崭新的诗歌形式。伴随着民族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启蒙的要求,中国新诗从旧诗的衰微中蜕化演变而来,同时受到外国诗歌尤其是西方现代诗歌的启示与影响,逐步走向成熟。新诗历经几代人上百年发展,先后涌现了大批优秀诗人和诸多经典作品。
本书精选新诗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23家,如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何其芳、穆旦、北岛、顾城、海子等,包括30多首名作和3部代表性诗集,以及现当代名家的精彩赏析。
新诗经典之作+经典评论,让您全面了解新诗的发展历程和不同的新诗流派,学会理解和欣赏新诗的方法,品味现代诗歌无尽的丰富与复杂之美!
作者简介
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十月》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批评奖等。
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1998)、《草之家》(2002)、《连心锁》(2005)、《鸟语林》(2010),诗论集《守望与倾听》(2000)、《灵魂的未来》(2009),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2012)。
目录
郭沫若
《女神》( 选 7 首 ) /002
闻一多 《女神》之时代精神/010
何其芳 谈郭沫若的三首诗/019
徐志摩
再别康桥/027
唐晓渡 亦幻亦真,似幻还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030
闻一多
死 水/037
唐晓渡 化腐朽为神奇——闻一多的《死水》/038
戴望舒
萧红墓畔口占/045
臧 棣 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046
冯 至
冯至诗二首/055
蛇/055
南方的夜/055
何其芳 谈冯至的两首诗/057
十四行集/061
朱自清 诗与哲理/082
废 名 《十四行集》/086
(德)沃尔夫冈?顾彬 给我狭窄的心 一个大的宇宙——论冯至的十四行诗/102
卞之琳
诗 选/110
李健吾 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120
朱自清 解 诗/133
朱自清 诗与感觉/137
废 名 《十年诗草》/144
李广田 诗的艺术——论卞之琳的《十年诗草》/161
艾 青
太 阳/202
唐晓渡 飞旋的再生礼赞——艾青的《太阳》/203
林 庚
破 晓/209
林 庚 甘 苦/211
何其芳
扇/219
吴晓东 西 渡 扇上的烟云/221
穆 旦
春/224
诗八首/225
郑 敏 诗人与矛盾/229
孙玉石 解读穆旦的《诗八首》/243
林亨泰
风 景(其二)/257
熊秉明 一首现代诗的分析——林亨泰《风景(其二)》/258
商 禽
鸡/280
欧阳江河 命名的分裂:商禽的散文诗《鸡》/281
昌 耀
鹿的角枝/291
洪子诚 昌耀《鹿的角枝》评析/293
北 岛
旧 地/295
欧阳江河 读北岛《旧地》/297
多 多
十头。死了十头/305
张远山 析多多《十头。死了十头》/307
冬夜的天空/310
西 渡 犹如从半空落下……——析多多《冬夜的天空》/312
顾 城
远和近/315
熊秉明 论一首朦胧诗——顾城《远和近》/316
王家新
伦敦随笔/329
赵 璕 还需要多久,一场大雪才能从汉语中升起/337
张 枣
悠 悠/345
欧阳江河 站在虚构这边/347
边 缘/363
臧 棣 聆听边缘——张枣的《边缘》解读/364
海 子
亚洲铜/373
奚 密 海子《亚洲铜》探析/375
黑夜的献诗/387
崔卫平 真理的祭献——读海子《黑夜的献诗》/389
臧 棣
菠 菜/400
张桃洲 日常生活之歌——简析臧棣的《菠菜》/402
新建议/406
西 渡 析臧棣的《新建议》/408
西 渡
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423
臧 棣 记忆的诗歌叙事学——细读西渡的《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427
蛇/452
周 瓒 反向进化的自我之歌——西渡《蛇》解读/457
公共时代的菜园/464
敬文东 公社、大集体和隐秘的快乐——解读西渡的《公共时代的菜园》/466
桑 克
夜泊秦淮/477
张桃洲 命运的诗歌浮世绘——简析桑克的《夜泊秦淮》/484
朱 朱
楼梯上/491
张桃洲 黑暗中的肖邦/492
精彩书摘
徐志摩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1920年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影响下开始写作新诗。1922年回国,参加文学研究会和新月社。1931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主要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有《徐志摩全集》行世。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在郭沫若之后,徐志摩的新诗创作进一步提高了新诗在读者中的声望,成为新诗中以颂扬爱、美和自由为主要任务的代表诗人——当然,徐志摩的实际创作要更复杂一些,其主题、题材都表现出一定的丰富性。诗人所属的新月派的创作和理论,出现在郭沫若的《女神》之后,对校正当时诗坛上因《女神》而来的过分直露的呼喊诗的倾向,探索新诗的形式规律,有一定积极的意义。徐志摩的诗音节和谐、词藻华美而情感轻灵,很受一般读者欢迎。
再别康桥a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亦幻亦真,似幻还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唐晓渡
康桥(Cambridge),又译“剑桥”,是英格兰的一座城市。著名的剑桥大学就坐落在这里。1921年,诗人出于对哲学大师罗素的仰慕,放弃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转道来此。原想做罗素的弟子,不果;遂经人推荐,在剑桥大学旁听一年。1922年回国后,曾写有《再会吧康桥》一诗,收入1925年初版的《志摩的诗》集中。1928年《志摩的诗》再版,原来收录的18首被他删得只剩下《沙扬娜拉》一首,被删去的自然也包括《再会吧康桥》在内。《再别康桥》是他1928年第二次旅欧归途中写的。他这次旅欧是否又去过康桥不得而知。从诗题“再别”和诗中“寻梦”一问看,似乎是去过;但“再别”和“寻梦”的方式有多种:可经由故地重游,亦可经由追忆。作为读者,倒是宁愿他没有再去过;在追忆中“寻梦”较之实地“寻梦”总要多一层梦幻色彩;而本已告别过一次康桥,又在追忆中“再别”一次,不是显得更有诗意吗?遗憾的是手头没有初版《志摩的诗》,否则将《再会吧康桥》和《再别康桥》两相对照,会是很有趣的。
徐志摩在新诗史上是一个颇多争论的人物。胡适曾为他概括出“爱”“自由”和“美”的“单纯信仰”;卞之琳先生认为这“不免从空到空”,理由是“他的思想,‘杂’是有名的,变也是显著的,他师事过梁启超,求教过罗素,景仰过列宁,佩服过罗兰,结识过泰戈尔,等等,他搬弄过柏拉图、卢梭、尼采等等,杂而又杂,变来变去,都不足为奇”(《〈徐志摩诗选〉序》)。这或许从一方面解释了他何以会引起那么多争议的原因。另一方面,无论他如何“杂而又杂,变来变去”,“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19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同上),大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诗歌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说这是万变不离其宗。而如果“自由”和“美”确实是浪漫主义诗学的两个核心范畴的话,胡适的概括应该说还是不无道理的。
这就为解读《再别康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英国浪漫主义对自由和美的追求集中体现为对自然的强烈而真挚的爱(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读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5卷有关章节);而在徐志摩的笔下,人工的,或者说人文荟萃的康桥首先被自然化了。它不再是那个曾经使他的“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头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的康桥,而化成了一个金柳在波光里摇曳的康桥,一个“沉淀着彩虹似的梦”的康桥,一个焕发着神奇的自然魅力的康桥。所有这些意象在现实中都和康桥城所傍的康(剑)河有关,但诗人从众多可能的意象中独标出这些自然意象以作为康桥的表征,却不可能不深藏着一种独特的美学旨趣。
诗的第一节前三行连用了三个“轻轻的”。按照一种非常糟糕的解读法,这是因为诗人在康桥只度过了一年,时间很短,还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离别时也不曾惊动了谁。这位解读者似乎忘记了,诗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呆的时间比在康桥也长不了多少,那么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类似的感情,甚至没有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一点痕迹呢?进一步说,假如诗人使用如此强化的笔法,只是为了交代或突出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的话,那么他也太不懂得珍惜笔墨了。
撇开诗人当初去康桥的动机遗痕不论,这三个“轻轻的”也足以表达了某种近乎圣洁的心情,且带有显明的梦幻感。他不是在告别地理上的康桥,而是在告别他理想中的一方净土!二、三两节的意象(“金柳”“新娘”“艳影”“青荇”“招摇”“柔波”)基本上都是女性的;所表现的感受(“荡漾”“甘做一条水草”)也都是女性所激发的感受;如果说在徐志摩的大部分诗作中都或明或暗地闪动着一个女性的倩影的话,那么,这里浓烈的女性意味却既不同于《沙扬娜拉》中那种刻骨的温柔,又不同于《雪花的快乐》中那种依恋的销魂,更不同于《别拧我,疼》中那种肉麻的儿女私情;她要广阔、深厚和神圣得多!一方面,她和浪漫主义把女性作为自然的集中象征予以礼赞、膜拜的普遍倾向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以康桥的人文特色为背景,通过荡人魂魄的彼此交融、涵咏(在第二节中,是“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第三节则倒过来,“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水草”),暗示出她对于诗人生命的爆发、人格的形成曾经起过的催生作用,及其在他精神生活中不可替代,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这却是诗人正在“作别”(再别)的!这一行为因此而具有了远远超出特定事件自身的意义。第一节末句使用了“西天的云彩”这一美丽而空幻的借喻。说这是在借用“云彩”的来去无痕、了无牵挂来反衬诗人此刻难言的依恋和惆怅,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也是只及其一,不及其二。从末节以“悄悄”呼应开头的“轻轻”,以造成整体上回环的效果,以及“不带走一片云彩”句看,诗人的心境比通常想象的要宁静平和得多;即使说到依恋和惆怅,也不宜过于就事论事。这背后有许多未经道出的东西,需以互文的眼光与1922年首别康桥归国后写的那些诗参看。卞之琳先生不无讽刺地指出:“回国他的‘理想主义’,(还是‘主义’!),所谓要‘诗化生活’,在现实面前当然会碰壁。碰壁是好事,他的深度近视眼里也没有能避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人间疾苦”。因此,在他的“轻轻的”来去中,实有着被隐去的沉重和苦闷;表面的宁静平和之下,是某种巨大的心理反差:他越是试图把康桥诗化成一块净土,就越是意识到现实的混浊卑污;反过来,他越是体验过现实的混浊卑污,这曾经寄寓过诗人理想的康桥就越是显得纯洁无瑕,像诗一样遥不可及。不仅是第一节的“西天的云彩”,第二节那“夕阳”中的“波光”、第三节那“在水底招摇”的“青荇”,也都带着某种亦真亦幻、似真还幻的空迷色彩。及至第四节,诗人对这一点的表现更是到了不顾常理的程度。他断然否定“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而“是天上虹”,是“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他所“告别”的究竟是现实中的康桥,还是梦幻中的康桥,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还应注意到第一节中一处小小的悖谬。通常作别的姿态是挥手,但诗人却说“我轻轻的招手”。这种错乱只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在幼儿身上,一是在梦中。诗人的用意是否兼而有之?(在精神上,康桥或可视为他暗暗认可的父母之邦?)至少这是他故意留下的一处可供品味的含混:循着这种失态,聪明的读者能从表面的清纯中还原出背后的混乱。
第五节中突然出现了“寻梦”的短促一问,这是瞬间清醒的诗人对一直沉浸在梦幻中的另一个自己发出的诘难。它像凌空突降的猛烈一击,把涟漪荡漾的梦幻水面打出了一个深坑,使我们在一瞥中看见了水底的坚硬现实。这个水坑随即合拢。遭到诘难的梦中之人不但不愿醒悟,反而更趋沉迷,要“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漫溯”一词很有意味。“漫”者,无目的也;“溯”者,逆流而行也;梦中人执著于梦,是企望在某种出神状态中抵达遥远的过去(这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该诗是一首追忆之作);而这种抵达的企望,恰恰和诗中表现的“作别”场景构成了某种与所说的心理反差相呼应的矛盾反讽。那似乎是错乱的“轻轻的招手”也因此显得合情合理——“我”其实是在和那明知已逝向遥远,却又满心想挽留,甚至截获的过去(梦)打招呼呢!以下“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更是一厢情愿的梦中梦、幻中幻了。从诗艺的角度考虑,这虚幻的凯旋场景正是诗人刻意制造的情感上的“假高潮”。欲抑先扬,臻于巅峰才能摔得平实。实际上,经过了“寻梦”的一问,谁都明白,这“星辉斑斓里”的“放歌”是唱不出,也不可能唱出的了。
“星辉”的意象在这里具有双重的指向。一方面它承继了梦境,并把它接引到更加纵深的所在;另一方面它使开头绚烂的黄昏场景暗转到黑夜,在微温的柔情中渗进了丝丝冷峻的寒意。待到第六节诗人明言“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时,那种虚幻的破灭感已经沛然而出了。“笙箫”所引发的悲苦、伤感和无可奈何透露了诗人一直试图遮掩,甚至着意回避的真实心绪,从而把“今晚的康桥”化为一片沉默。梦到此刻,不醒也得醒了——无论是真实的康桥,还是诗化的康桥,无论是把它象征为自然,还是把它象征为梦境,所有这些都与诗人的现实没有太大的关系,都被归结到必须“作别”这一严酷的事实上来。现在他真的要走了,而且走得如此彻底:“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整个儿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但谁能说得清,在这一闪即逝的衣袖挥动过后,留下的究竟是真正的飘逸超脱,还是根本上的绝望无奈呢?诗人尽管“在诗思、诗艺上没有越出19世纪英国浪漫派的雷池一步”,但他毕竟不是一个19世纪的英国浪漫派诗人。他毕竟要回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
徐志摩的创作在语言上对新诗的贡献,这首诗是一个典范。前人已多有解说,此处不赘。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在建行上的考虑。其时经过了1926年北京《晨报》对诗的形式问题的讨论。尤其是看到了闻一多谨严的新诗格律实验,诗人已经“憬悟”到“自己的野性”,并深受影响,更加致力于创作中的形式因素。这种影响多属“消极的”似不客观,恰恰相反,他原先的“野性”倒是在“镣铐”的束缚下被逼出了某种“灵性”。同样追求“建筑美”,闻一多所提倡的不免机械呆板,而徐志摩则运用得比较灵活。《再别康桥》的建行两行间以二字之距参差开来,就有着在视觉上造成某种和诗的语境相一致的趑趄徘徊的意味。而类似的考虑在其他也注重“建筑美”的诗人那里是很少见到的。
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州人。1922年开始诗歌创作。在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下,他发展了初期象征派和新月诗派的诗歌实验,将新诗的艺术探索推进到所谓的“现代派”时期。戴望舒是“‘现代派’诗坛的首领”,同时还是著名的诗歌翻译家,翻译了波德莱尔、洛尔迦、果尔蒙、道生等诗人的大量作品。主要著作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译诗集》等。《戴望舒全集》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30年代诗坛的“现代派”,不同于西方现代派。中国的“现代派”主要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并因为这个诗派的核心刊物《现代》杂志而得名。施蛰存将这个诗派的诗歌特征概括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这个诗派对“现代”感的追求虽然与西方现代派有共同之处,但在“现代”的具体内涵上,两者却很不相同。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所定义的“现代”是基于中国的具体现实,针对中国初期象征派和新月派脱离现代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言的。卞之琳将戴望舒的诗歌追求总结为“在亲切的日常生活调子里舒卷自如,敏锐,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有节制的潇洒和有功力的淳朴”。戴望舒对新诗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日常口语的调子融入诗歌的节奏。这种节奏既不同于《女神》的呐喊式节奏,又不同于“新月派”过于规整和书面化的节奏,为新诗引进了一种亲切、自然的音乐。
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
臧 棣
90年代初(本文年代均指20世纪),关于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余光中曾经有过一番发难。大意是说,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有许多缺陷,远远没有达到成熟;而这样的有着致命语言缺陷的诗人,居然占据着新诗史上一个显赫的位置,是很奇怪的。由于诗歌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竞技场,所以,后来的诗人意识到前驱者的语言局限,不仅意味着他自身的成长,而且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后来者对先驱者所依傍的语言资源和所处的语言环境缺少必要的同情心;不仅如此,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语言才能的判断也极有问题。而最大的疑问在于,当我们用今天的关于诗歌语言的标准去衡量戴望舒那一代诗人时,我们所运用的尺度本身是否具有充足的客观性。
问题不在于戴望舒的语言是否成熟,或者是否完美,因为这太像是一种趣味之争。在余光中对戴望舒的责难中,让我感到不够公允的是,他的批评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的语言趣味;并且,他把自己的趣味当成一种客观的审美标准来运用。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戴望舒的诗歌语言不成熟,便令人疑窦丛生了。因为在新诗史上,就绝对的语言才能而言,大概只有两三个诗人能和他匹敌。当然,由于戴望舒所处的时代,新诗语言的整体水准比较低,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在个别的文本中,他的语言确实有不少毛病,但必须意识到,无论这些毛病有多少,它们和戴望舒对诗歌语言的自觉意识相比,和他所拥有的语言才能相比,甚至和他自己的另一些更优异的文本相比,都是非常次要的。在我看来,戴望舒目前在新诗史上享有的显赫的位置,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比如,不是由于他在主题上的开拓精神,不是由于他在风格上的创新意识,恰恰是因为他在诗歌语言上显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造诣。如果人们要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为诗歌语言的进展和成熟树几块纪念碑的话,很多名声显赫的人都可以被忽略,但戴望舒的这一块碑是一定要树的。
也许,更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省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新诗语言的成熟?为什么很少有人指责小说的语言不成熟,或是抱怨散文的语言不成熟?新诗的语言,在本质上和小说、现代散文的语言是一致的。尽管有过一些短暂的偏离,如新格律诗运动,但在总体上,它根植于“五四”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语言观及其实践:即用来创作新诗的语言,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语言,而是一种和用来创作小说的语言没有什么本质差别的语言。不要小瞧这其中界限的消弭,它预示了一种新的诗歌理想,也揭示了一种新的语言态度:诗歌的语言应该趋同于日常语言。它更极端的主张是,新诗的语言应该口语化。
忽略这样的前提,或者,不认同这样的语言观(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美学),当然也可以。然而,倘若把这忽略作为一个出发点,笼统地说这样的诗歌语言实践本身存在致命的缺点,并进而从总体上断定新诗的语言不成熟,这样的结论就未免给人雌黄之感。这里,问题不仅涉及有关诗歌语言的分歧,而且也涉及相关的争议:什么是新诗?什么又是新诗的成熟?我经常听到来自各种文学势力的人物说,新诗还不成熟。而一旦验查他们所使用的文学标准,就会发现他的对新诗的理解充满偏见。
在我看来,20年代后期,新诗的语言在徐志摩、闻一多、冯至那一代诗人手中就已经显得很成熟了。尽管现在流行的文学史和诗歌批评喜欢对徐志摩说三道四,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夭折的大诗人,而不是人们所习惯认为的什么二流诗人。进入30年代,卞之琳、艾青、戴望舒在诗歌语言上取得的成熟,更是锦上添花,令人称羡。以现今的眼光观之,也许稍嫌菲薄,但它们绝对有金子般的质量,是一笔令人难忘的语言遗产。如果对这些诗人的成熟视而不见,大谈什么新诗不成熟,或新诗的语言不成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这些诗人在语言上是否成熟有什么问题,而是责难者自身关于诗歌的观念有问题。
回过来再说戴望舒。作为一个诗人,他的优异常常令我吃惊。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生的诗人,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天生的诗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对现代情绪有着特殊敏感的诗人。沉默,曾经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一个基石。而同样的沉默,也是戴望舒的诗歌的基点。在评价戴望舒时,艾青的取舍非常耐人寻味。他称赞戴望舒是“一个正直的、有很高的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这里,“教养”一词,不仅涉及对戴望舒作为一个诗人所具有的品质的评价,而且也涉及戴望舒与新诗史的关系。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在艾青的意图里,肯定部分地包含着这样的感叹:新诗历史上,也许有过一些诗人写出过不错的作品,但是有素养的诗人是非常罕见的。而戴望舒是这样一个诗人,他不仅展现了他对于新诗的素养,而且也体现了诗歌本身的素养。在论及戴望舒的语言时,艾青的称赞更是毫无保留:“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语言的魅力。”
无疑,在看待戴望舒的诗歌语言的问题上,艾青和余光中的言论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比照,但也必须明白,这种比照也许有趣,却并不构成反驳的逻辑。也就是说,艾青对戴望舒的诗歌语言的赞誉本身还不足以反驳余光中的非难。它只是从一个侧面表明,如何衡估戴望舒的语言成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很可能,还牵涉到对整个新诗语言的发展状况的判断。如果考虑到两位诗人的语言趣味,那么,在他们的评价中出现的反差确实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在驾驭诗歌语言方面,艾青的才能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余光中的诗歌语言也很有特色。
戴望舒的诗歌语言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它真的如余光中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不成熟的问题吗?或者干脆这样问吧:相对于什么样的语言标准,相对于什么样的诗歌美学,戴望舒的语言才是不成熟的呢?
在戴望舒的诗歌中,他的语言才华展露得不平衡,是一个事实。但这种现象普遍地存在于每个优秀的诗人身上。也不妨说,无论多么优异的诗人,他都会遭遇类似的问题。如果仅仅以一位诗人在某些作品中的语言缺陷,来判断他的诗歌语言不成熟,这样的视角在批评方法上就非常可疑。对戴望舒这样的语言高手而言,这样的批评视角尤其显得不够公允。从新诗历史的角度看,如果说到诗人对语言的感觉,那么我要说,戴望舒的同代人很少能与他比肩。他是他那一代诗人中对语言考虑最多的诗人之一,也是在诗歌中将语言运用得最纯熟的诗人之一(虽说并非总是如此)。当然,不是说戴望舒没有自己的语言局限,比如在措辞中,他有偏于甜腻和夸饰的缺点。但这些瑕疵,与他对诗歌语言所拥有的强烈的自觉意识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戴望舒一生写作的新诗不过百首左右。仅凭这些诗,他也许还不能成为一个大诗人,但却足以跻身新诗历史上最优秀的诗人的行列。这些诗中,有十来首是极其优异的诗歌,其中至少有一首短诗够得上伟大的标准。当然,无庸置疑地,它们也是成熟的诗歌,无愧于正在形成的新诗的传统。作为后进的诗人,可以避开这样的传统,但有所损失的,肯定不是戴望舒,而是这些后进诗人自己。
这里,我只想谈及戴望舒的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1995年中,余光中来北京大学做讲座时,在质疑他对戴望舒的语言评论时,我曾举出过这首诗,指出它在语言上不仅成熟,而且这种成熟还延伸到风格的层面,并说它是新诗历史上最伟大的短诗之一。我很难想象,真正懂诗的人在读了戴望舒的这首诗后,还会说戴望舒的语言不成熟。或者,还会泛泛地谈论什么新诗的语言不成熟;或者,更拙劣地笼统地谈论什么新诗不成熟。
80年代早期,当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我就会背这首诗。但是更经常地,我会鬼使神差般走到书架前,把《戴望舒诗集》抽出来,翻到第1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默默地读上几遍。无疑,这情景带有某种仪式的色彩,我喜欢用目光面对这首诗,凝看它滞留在语言中的那物质的一面。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现在谈论诗歌时,我已很少使用听起来过分的言辞,但是我仍然禁不住想说,这首诗是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
《萧红墓畔口占》只有短短的四行: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
前言/序言
中国新诗或称现代诗,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以白话写作,反映现代中国人的经验,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一种崭新的诗歌形式。它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区别,既是语言形式上的,又是内容上的。从语言形式上说,新诗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是以白话写的,因此凡是因循旧诗的体制格式,以文言写作的诗歌,仍属旧诗,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新诗的范畴。从内容上说,它反映的是现代中国人独特的感觉、情绪、思想和意识,因此那种反映陈腐的士大夫趣味的诗歌,即使它是用白话写的,也不属于新诗的范畴。但是由于对内容的判断往往见仁见智,所以从语言形式上区分新诗和旧诗还是最可靠的。
从新诗发生的社会学背景上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心目中,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是二位一体的,共同服务于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总目标。文白之争在当时是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之一,而白话诗的确立又是“新文学运动中对抗最尖锐因而意义最典型的白刃前哨战。”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一种语言的诗歌的成立,也意味着这种语言的成熟。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新诗的确立使文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大促进了旨在使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统一的“国语运动”。因此,新诗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最坚实的成果之一。
从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说,新诗是从旧诗的衰微中蜕化演变出来的。旧诗发展到清末,它的语言、体式,它所能传达的经验,都已发展到了极致,在它的语言系统内已很难翻出什么新花样了。另一方面,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现实与古典中国相比,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旧诗囿于它既有的语言和体式,对这种变化的反应是无力和病态的。这也是晚清的“诗界革命”终于止步于对宋诗派的模仿风气的原因。正是近代中国面临的特殊的历史现实和这一现实下形成的特殊的心灵现实,迫切要求创造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种诗歌既要能反映上述变化了的事实,并且应该有一种与人们的口语节奏相一致的新的诗歌节奏,也就是诗歌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一。这也是新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很快站稳脚跟,并日益发展成熟,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新诗的产生和发展也受到了外国诗歌,特别是西方现代诗歌的深刻启示与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始终伴随着新诗发展的历史。这一方面是因为新诗与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天然联系,而这一思想启蒙的实质是一个向西方学习、使民族思想意识逐步现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西方现代诗歌正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而产生的,集中表现了现代人的生活经验,他们的情绪、感觉、意识和心理,对渴望使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和诗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外来的影响同时伴随着中国现代诗人对外来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变异和融化。正是这吸取和创造的过程,使中国新诗的发展融入了世界现代诗歌发展的整体过程,同时在新诗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又对外释放这种影响,这后一点如今业已成为现实而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可能性。
胡适是新诗最早的作者,他于1920年3月出版的《尝试集》是第一本新诗集。初期白话诗的作者除胡适外,还有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周作人等人。这一时期的白话诗大都以白描和比喻手法描绘社会现象、自然风景,以及诗人对这些社会现象的看法、对自然的感受。形式上以散文化为特点,表现直露,好发议论而立意浅显,艺术手法单一,缺乏想象力,也大都没能形成鲜明的诗歌节奏,因而没有多少诗味。这种情况到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有了彻底的改变。《女神》充满了狂放恣肆的想象力,鲜明强烈的诗歌节奏,并表现出驾驭白话的高超能力。《女神》不仅标志着新诗作为一种诗体的确立,它所代表的时代也成为新诗史上几成绝响的短暂的天才时期。《女神》出版的第二年,湖畔诗人(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出版了他们的诗合集《湖畔》。他们是“五四”唤起的一代新人,在精神上摆脱了旧思想的包袱,诗歌形式也较少受到旧诗的束缚。他们的诗以爱情诗和写景诗为主,风格明丽轻快,在精神的自由上和《女神》一致,在主体意识的某些方面甚至对《女神》有所超越。在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小诗也是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诗歌现象。这类小诗以反映刹那的情绪、感觉和印象为主,完全没有形式的敷衍,是对旧诗最彻底的反动。小诗的代表诗人是冰心。
《女神》的出现引出了众多的模仿者,而其末流流于空洞的叫喊,这种现象引起了一部分诗人的不满,导致初期象征派和新月派的反拨。初期象征派的穆木天和王独清倡导纯诗,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和早期白话诗的实践提出了批评,并强调诗歌表现要以含蓄、暗示为特征。早期象征派创作上的代表诗人是李金发。新月派针对当时诗坛上流行的叫喊诗,提出“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格律化”的主张,试图找到新诗自身的形式规律。新月派的主张对校正上述叫喊诗的流弊,探索新诗的形式规范无疑有其十分积极的意义,而其末流又不免走向极端,徒具形式而缺乏真实感。30年代初(本文所说年代均指20世纪),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批判地继承了早期象征派和新月派艺术探索上的成就,在新诗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现代”的主张,将“现代诗”定义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派”在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关注和表现的含蓄与暗示方面是早期象征派的继承者,同时强调以“现代的词藻”,即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自然而有特点的诗歌节奏,这又是对新月派过分强调“形式的均齐”的反拨。这一派的主要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冯至等。40年代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促成了新诗史上另一个重要流派——中国新诗派(九叶派)的诞生。中国新诗派继承了现代派在艺术探索上的成就,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这种探索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国新诗派强调对现实的直视(而不是逃避)和知性在诗歌中的作用,使现实、玄学(对世界的抽象思考)和象征在诗歌中得到融合。这一派的代表诗人是穆旦。
以上是1949年以前新诗中偏于探索个人内心世界一脉的发展线索,它起于早期象征派对内心世界的强调和新月派的形式探索,到40年代发展为“九叶派”诗人在个人内心世界、社会历史现实和理性思考之间的平衡和协调。
新诗史上的另一脉,继承了早期白话诗“平民化”的主张并将其发展到极致,强调诗歌为现实人生服务,要求诗歌直接从外部世界吸取诗情,并在意识上与时代主流意识保持同步,成为新诗史上现实主义的源流。这一派的早期代表诗人有蒋光慈。30年代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继承了这一传统。中国诗歌会诗人群之外,属于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还有臧克家。臧克家的诗歌在形式上受到新月派的影响,讲究词句的锤炼,把感情、倾向性凝聚、隐藏在诗的形象里,因而克服了这一派诗人过分直露的缺点,较耐咀嚼与回味。抗日战争的烽火将更多的诗人,包括一部分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卷入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在这一时代洪流中成长起来的重要诗歌派别是七月派,其代表诗人有鲁藜、阿垅、曾卓、罗洛、牛汉等。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人是艾青。艾青的诗最集中、强烈地表达了抗战的时代主题,传达了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的心声。在诗艺上,艾青完成了历史的综合的任务,他一方面坚持并发展了中国诗歌会诗人忠于现实的传统,克服了这一派诗人“幼稚的叫喊”的弱点,另一方面吸收了欧洲象征主义诗歌和我国30年代“现代派”诗人在诗艺探索上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新诗艺术。
1949年以后,新诗史上强调内心探索的一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压下日益萎缩并趋于消失。另一脉与来自解放区的民歌体新诗汇合,在国家意志的驾驭和鞭策下,进一步走上了高度政治化和伦理道德化的道路,诗歌的主题、题材、抒情方式日益单一,直至“文革”期间诗歌创造力的彻底衰竭。这种现象引起了一批敏感的青年人的不满和反叛。“文革”后期,在地下传播的西方现代诗和我国三四十年代现代诗歌的影响下,一些青年诗人开始了恢复诗的真实性的努力。这些诗人中较早的有食指等,而更具代表性的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多多等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这一诗歌潜流在80年代初期涌出地面,形成了当时引起激烈争鸣的朦胧诗现象。朦胧诗是以五六十年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诗歌的反叛者的姿态出现的,其目标是恢复诗人的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前者表现为对个人的感情经验和内心世界的特殊经验的重视,后者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在艺术表现上,朦胧诗人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和我国三四十年代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强调审美特征的个性化,试图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对应的“诗的世界”。朦胧诗人多采用意象化的表现方法,语言以典雅、优美为主。诗体多为自由诗,但诗行相对整齐,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朦胧诗人的创作实践使新诗发展重新接续了被中断了近30年的传统。由于朦胧诗在诗歌表现的内容上响应了时代的要求,在表现方法上和我国古典诗歌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朦胧诗之后,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对朦胧诗人过分关注社会现实的倾向、英雄主义气质和集体代言人身份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诗人对于诗歌语言和形式实验的责任,强调诗人与日常生活的关联。这就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第三代诗歌”和后朦胧诗歌。后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有柏桦、骆一禾、海子、西川、韩东、吕德安、张枣、陈东东、欧阳江河、孙文波、肖开愚、臧棣、戈麦等。八九十年代之交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迅速商业化的社会现实使许多诗人放弃了写作,但另一部分诗人在社会的普遍漠视中,一直执着于诗艺的探索。他们在反思“第三代诗人”普遍激进的诗歌姿态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写作立场进行了调整。他们一方面强调诗人对语言和诗艺的特殊责任,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诗人只能生活在历史中的基本事实,以及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排拒姿态的虚幻性。在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中,他们既强调历史对个人的特殊压力,同时又指出个人对历史作出回应(而不是回避)的可能性及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诗歌想象力对维护个体自由的特殊作用。这些诗人在诗艺上的执着探索到90年代末逐渐引起诗坛的关注,被称为“90年代诗歌”。90年代诗歌的代表诗人有王家新、孙文波、肖开愚、臧棣、陈东东、欧阳江河、西川、黄灿然、桑克、清平、朱朱等。
以上我们简单地回顾了新诗发展80多年的历史。总结这一历史,我们会发现新诗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十分耀眼的特征,使两者处于截然不同的审美系统中。这些不同集中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新诗所反映的经验的特殊性。古典诗歌以反映人们的世俗经验为主,它所表现的内容和散文并无本质的不同。古典诗学中所谓“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正好道出了古典诗歌的一个根本特征,即诗歌所反映的经验是公共的,而表现这一经验的方法是特殊的。古典诗歌作为当时一般士人必须具备的文化修养,带有很大的实用倾向,作诗也是士人阶层世俗礼仪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一种生存手段。新诗的情形则根本不同。新诗反映的是超越了世俗经验的生命经验,以表现个体的意识为己任,它表现的内容正好是世俗经验的反面。由于生命经验的个人化,古典诗歌的公共性在新诗中趋于瓦解。也就是说,诗歌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公共的文化想象,读诗和写诗都变成了一件专门的事情。
新诗经验的特殊性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它所反映的人的意识现代化。新诗在它的倡导者胡适手中,十分强调表现写作者主体的性情见解,强调“有我”“有人”。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胡适的“有我”“有人”的主张进一步发展为对个人内心世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探索,并强调表现诗人个体作为一个现代人的特殊的经验与意识。这种对“有我”的强调导致了诗歌趣味上的极端性。诗人常常对感情、经验和意识进行夸张和变形处理,并将其发展到极端。这与古典诗歌“无我”、恬淡静穆的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现代人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现实,又使其意识总是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对称于这种生存和意识的复杂性,现代诗的主题表现出突出的综合与复杂的倾向。另外,为了表现意识的流动与含混的特征,当代诗歌又发展出一种所谓的无主题诗歌。这种类型的诗歌,并无明确的主题,诗意的完整主要依赖于其一致的情绪和氛围。这些都带来了理解新诗的特殊困难。
二是美学趣味上的复杂和多样化。在新诗的内部存在一个追求现代性的强大的内驱力。新诗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开始就加入了企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在“人的现代化”,特别是在思想、意识和心理的现代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诗对言文合一的迫切愿望,以及在言文合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口语节奏为基础的诗歌节奏,都能在这一现代性的诉求中找到依据。事实上,“现代性”的诉求一直是新诗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同时,它也是新诗的审美意识与古典诗歌迥异其趣的根本原因。现代性的追求中包含一个对新奇的追求,它集中体现为对想象的新奇性的追求。现代物质文明和以理性为基础的科技文明的发达对人的想象力施加了特殊的限制。为了解除现代文明对想象力的这种束缚,现代诗普遍采取的策略是充分发挥想象、联想和幻想的作用,以新奇的意象来刺激、唤醒人们沉睡的想象力。现代诗中的比喻也多从远取譬,通过想象在相距遥远的事物之间驾起沟通、理解的桥梁。现代诗想象的这种新奇性也是现代诗的另一特征——神秘性的来源。它也是一部分读者抱怨现代诗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作为现代性追求的另一个侧面是知性在诗歌表现中的特殊运用。现代诗歌一方面强调直觉、无意识在诗歌想象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理性、意识在诗歌中的作用。知性在现代诗歌中的特殊作用,不仅体现在诗歌的结构及主题和意识的表现中,而且渗透于现代诗的想象中。现代想象不同于古典诗歌的直觉和联想(它是无意识的和被动的),其中充分融合了知性的特殊作用,是在理性分析基础上对想象力的主动发挥。知性对诗歌创作的这种全面参与,强化了现代诗综合和复杂的特点。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诗在审美趣味上也趋向于复杂和多样化,和古典诗歌单纯以典雅和优美为指归的美学理想有了很大的距离。这也是一部分习惯了把“优美”看作诗歌美学标准的读者对新诗感到无所适从的原因。
三是新诗的实验性和开放性。由于白话诗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毫无前例可循,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待于诗人的实验。因此,一部新诗史就是一部诗体的实验史。新诗的成就与局限,都与它的这种实验性紧密相关。新诗形式上的散文化、自由化或格律化,都统一于这种实验性之中,并成为新诗创造力的一个主要来源。这样也就造成了新诗在形式问题上的没有标准,从而也影响了一部分读者对新诗的接受。新诗又是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影响构成了新诗发展的另一重要动力,正是对它的摒斥造成了五六十年代新诗创造力的普遍衰竭。新诗的这种开放性使它的发展融入了世界现代诗歌的整体进程中,从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世界性。当然,中国新诗人接受和吸取外来影响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对这种影响加以改造、利用、转化和融合的过程,上述过程是紧密结合、互为正反面的。由此也引出了一个关于新诗的民族性的问题。中国古典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但并不存在民族性的问题,因为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进行创作的。民族性问题在诗学理论上论争的焦点表现为“横的移植”与“竖的继承”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获得最后的定论。而这种没有答案或者答案不确定的状态某种程度上正是推动新诗发展的动力。由于现代诗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的新的诗歌形式,因此,对现代诗的阅读也必须采用与古典诗歌不同的方法。新诗应该怎么读的问题可以说一直贯穿着新诗发展的历史。各个时期的新诗批评除了试图完成新诗自身的理论建设之外,也总是试图为如何阅读新诗提供解决的方案。可以说,新诗就是伴随着批评一起发展的。新诗的批评文本和新诗文本一样是新诗发展的见证,对我们理解新诗具有同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本书选择了一部分在新诗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把它们和针对它们的批评文本编辑在一起,让它们一起为新诗的发展作证,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如何理解新诗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我在选择批评文本时有意偏重对具体诗作的解读,以为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新诗作品提供更多实用的指导,同时兼顾对几部在新诗发展历史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诗集的批评和解读。全书涉及郭沫若以来的新诗人23家,作品包括新诗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诗集三部(郭沫若的《女神》、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冯至的《十四行集》),其他单篇作品30多篇。收入本书的这些诗作大部分都是新诗史上备受关注的,而针对他们的批评文本也都在不同的时期对新诗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由于本书的编选宗旨,我们在文本的选择上偏向于那些意义比较复杂,在批评中得到较多关注的篇章,所以就造成了一些重要的诗人入选篇目不多,还有一些重要诗人没有入选的情况。这也是不得不如此。好在我们并不是在编选一个诗歌选本,我想这种情况是会得到读者鉴谅的。
西 渡
用户评价
读到这本《名家读新诗》,我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念头就是“这帮老家伙们,还能玩得这么嗨!” 毕竟,我对“名家”的印象,总是带着点古板、严肃,好像他们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得像颁奖感言一样庄重。结果,翻开这书,简直就像一个惊喜的炸弹。他们聊起新诗,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学术分析,而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带着一种“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那种亲切感。我特别喜欢其中一位先生,聊到年轻时对某些意象的误解,那种笨拙又充满真诚的坦白,让我觉得,哦,原来大师也不是神,他们也有迷茫,也有犯傻的时候,这样一来,那些晦涩的新诗,好像也没那么遥不可及了。他们用自己的成长经历,用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为我们这些还在摸索的读者铺了一条路,虽然这条路并不平坦,但至少有人打着火把,照亮了前方的些许迷雾。书里那种自由对话的感觉,就像几个老友围坐在一起,喝着茶,聊着各自的爱好,你能感受到他们对诗歌那份不减的热情,那种从心底涌出来的喜爱,不掺杂任何功利,纯粹得让人动容。这种感觉,是很多书里很难找的。
评分不得不说,《名家读新诗》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我一直对新诗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既好奇它的新意,又常常被它的陌生感所阻挡。但这本书,就像是一扇窗户,让我得以窥见新诗世界背后那些鲜活的生命力。书中的几位名家,他们并非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去评判新诗的优劣,而是以一种更为平易近人的方式,分享他们与新诗“对话”的历程。我尤其欣赏其中一位评论家,他聊到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如何被某位新锐诗人的某句诗所“击中”,那种情感的共鸣,那种智慧的碰撞,被他描绘得淋漓尽致。他不是在分析结构,不是在考据出处,而是在讲述一个“人”与“诗”之间的故事。这种叙事性的评论方式,让我觉得,原来诗歌评论也可以如此有温度,如此具有感染力。它不是让你去“学”诗,而是让你去“感受”诗,去体验诗带来的冲击和启发。这种“感性”的引导,恰恰是很多初学者最需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吸引的。
评分《名家读新诗》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对“诗歌评论”的认知。我一直以为,诗歌评论就应该是那种一本正经,用一大堆专业术语把你绕晕的文字。但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它更像是一群经验丰富的“领路人”,带着我们这些对新诗感到好奇又有点不知所措的读者,一点点地走进这个新奇的世界。我最欣赏的一点是,书中的名家们,他们不是在“说教”,而是在“分享”。他们分享了自己曾经如何被某首新诗所打动,如何从一首诗里读出了某种情感共鸣,甚至如何因为对一首诗的误解,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这种“以身说法”的方式,让我觉得,原来理解诗歌,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功底,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和体验。他们就像是在为我们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让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新诗作者的意图,也更容易地找到自己与诗歌的连接点。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引导,比任何生硬的分析都来得更有效。
评分读完《名家读新诗》,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盛大的诗歌“派对”上,亲眼目睹了不同风格、不同年代的“明星”们,是如何看待和品鉴当下涌现的诗歌新力量。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选择那种枯燥乏味的学术论述,而是选择了更为鲜活、更为个人化的“对话”形式。我非常喜欢其中一位老先生的视角,他以一种非常“长者”的口吻,却又充满了“孩童般的纯真”,去描绘他对某些新诗的初次印象,那种带着审视,又带着惊喜,甚至带着一点点“不服气”的语气,让整个阅读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他不是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分享他的“纠结”和“顿悟”,引导我们去思考,去探索。这种“过程展示”的写作方式,让那些原本可能被视为“晦涩”的诗歌,变得有迹可循,仿佛有了导游,我们可以沿着他的足迹,去发现诗歌隐藏的乐趣。这本书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盲盒”拆解,每次翻开,都有新的惊喜和启发。
评分这次偶然翻阅的《名家读新诗》,彻底颠覆了我对“评论”的刻板印象。以往读诗歌评论,总觉得像在啃一本厚厚的教科书,充斥着各种我不懂的术语,读起来费力不说,还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距离感。但这本书完全不同,它更像是几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着我们这些初探新诗丛林的读者,悠哉悠哉地行走其中。他们不是在“指导”你该怎么理解,而是在“分享”他们自己探索的过程,那些曾经让他们驻足、让他们困惑,最终又让他们豁然开朗的瞬间。其中有位学者,竟然把我一直觉得“故弄玄虚”的一首诗,用一种极其接地气的方式解读开了,让我恍然大悟,原来诗歌的精妙之处,是可以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而非只能靠“悟”。这种“解构”式但又充满温情的解读,让我对新诗的那些“刺”,不再感到畏惧,反而跃跃欲试,想去亲自体验一番。这种“去神秘化”的处理方式,就像是为那些“高冷”的艺术作品,披上了一件亲民的外衣,让人觉得,原来艺术离我们这么近,触手可及。
评分书不错,值得一读。
评分我们的生活方式
评分书不错,值得一读。
评分我为什么喜欢在京东买东西,因为今天买明天就可以送到。我为什么每个商品的评价都一样,因为在京东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导致积累了很多未评价的订单,所以我统一用段话作为评价内容。京东购物这么久,有买到很好的产品,也有买到比较坑的产品,如果我用这段话来评价,说明这款产品没问题,至少85分以上,而比较LJ的产品,我绝对不会偷懒到复制粘贴评价,我绝对会用心的差评,这样其他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会作为参考,会影响该商品销量,而商家也会因此改进商品质量。
评分我为什么喜欢在京东买东西,因为今天买明天就可以送到。我为什么每个商品的评价都一样,因为在京东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导致积累了很多未评价的订单,所以我统一用段话作为评价内容。京东购物这么久,有买到很好的产品,也有买到比较坑的产品,如果我用这段话来评价,说明这款产品没问题,至少85分以上,而比较LJ的产品,我绝对不会偷懒到复制粘贴评价,我绝对会用心的差评,这样其他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会作为参考,会影响该商品销量,而商家也会因此改进商品质量。
评分我为什么喜欢在京东买东西,因为今天买明天就可以送到。我为什么每个商品的评价都一样,因为在京东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导致积累了很多未评价的订单,所以我统一用段话作为评价内容。京东购物这么久,有买到很好的产品,也有买到比较坑的产品,如果我用这段话来评价,说明这款产品没问题,至少85分以上,而比较LJ的产品,我绝对不会偷懒到复制粘贴评价,我绝对会用心的差评,这样其他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会作为参考,会影响该商品销量,而商家也会因此改进商品质量。
评分我们的生活方式
评分我们的生活方式
评分书不错,值得一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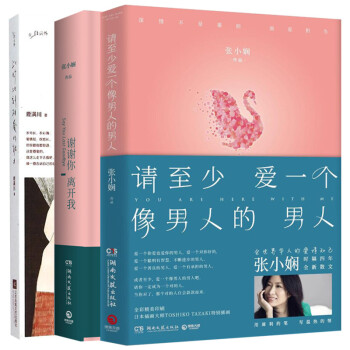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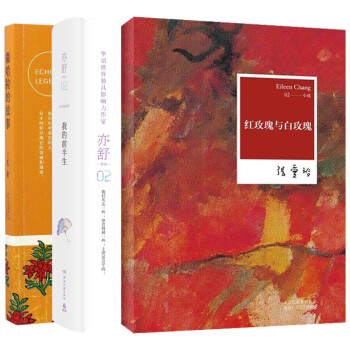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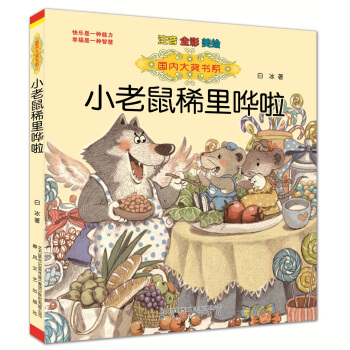
![蜗牛童话房子 东瓜西瓜汤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08309/5a38b906N44f5e15e.jpg)
![蜗牛童话房子 柿子灯和相思鸟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08341/5a38b6b9Ncce9f94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