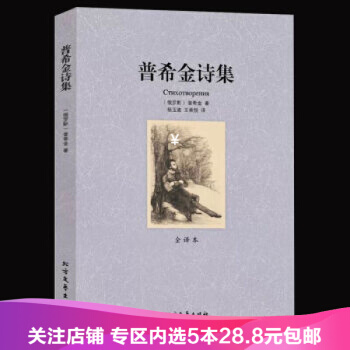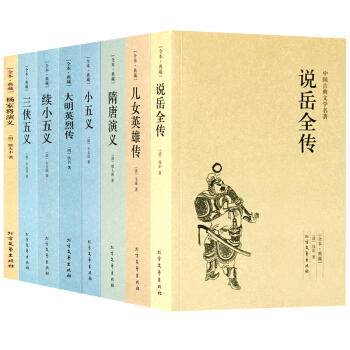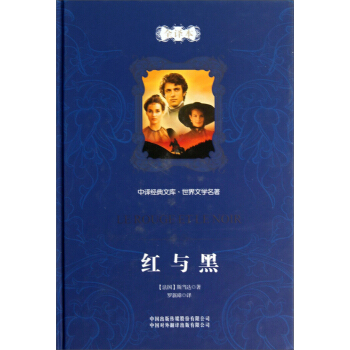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知乎、豆瓣逾百万粉丝,腾讯《大家》超人气作者张佳玮倾情翻译D.H.劳伦斯zui著名、争议zui大的小说——20世纪经典名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个“将可观的才华虚掷于色情小说之上”的家伙,被同时代的人称为“zui伟大、zui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写的一个“与自家先生性生活不和谐的贵族夫人,跟一位质朴粗豪的下人偷情”的故事。
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人RichardHoggart说:“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要当成淫秽物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玷辱的不是劳伦斯,而是我们自己。”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因其性描写长期遭禁,它在美国的出版历程,被誉为“一场性运动革命”。解禁后,成为20世纪经典名著,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畅销至今。
张佳玮首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全新的视角、语言和审美,打造适合当下阅读的全新译本,致敬30年前饶述一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开启《查》在中国的新阅读时代!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若要一言以蔽之,并不难:年轻的康妮因为贵族丈夫克利福德瘫痪阳痿,于是与丈夫的猎场看守成了情人,同居,图谋提出离婚。仅此而已。
许多读者,是冲着“禁书”字样来的。著名的性爱场景,奔放的肉欲,偷情的妻子——听起来很刺激。这大概也是同时代英国人的观感。
但劳伦斯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写的,是工业时代正在被机器屠灭的自然、感官与欲望,是机械文明压制下一个女性从肉欲到精神的觉醒,是人类内心本能与现代文明的对抗,与断然的决裂。
内容简介
面对半身不遂、对性爱不屑一顾的丈夫,敏感热情的查特莱夫人感到迷惘而不满。形而上的虚假爱情并非她想要,她想追求的是真诚、身心相契的感情。日日生活在庄园中,终于,查特莱夫人遇见了守林人梅勒斯,就此展开一段禁忌的、阶级不对称的不伦之恋……作者简介
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20世纪zui独特和zui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他生于诺丁汉,父亲是矿工,母亲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父母价值观念迥异,导致婚姻关系失和。畸形的家庭关系影响了劳伦斯对婚姻家庭和性爱的观念,也让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持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写出了多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劳伦斯提倡人性自由以及和谐的两性关系,反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其主要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游记和书信,zui著名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张佳玮,1983年7月生于无锡,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有随笔集《无非求碗热汤喝》《代表作和被代表作》等,小说《爱情故事》等,传记《莫奈和他的眼睛》《伦勃朗1642》等,以及译作《浮生六记》。
精彩书评
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要当成淫秽物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玷辱的不是劳伦斯,而是我们自己。——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我总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一件事情,就是把性关系描写得健康宝贵,而不是羞耻丢人。这部小说是我在这方面所取得的zui大成就。我觉得,它像裸体本身一样美丽,一样温柔,一样脆弱。
人们要反对只管反对,我却要表白这部小说是一本纯正的、健全的、我们今日需要的书。有些字眼,起初是令人震惊的,过了一会儿便毫不可惊了。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地给习惯所腐化了呢?
——D.H.劳伦斯
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我们的时代根本悲惨不堪,所以我们拒绝伤惨度日。大灾难席卷而过,我们处身废墟中,开始建起些微小的栖居地,培育些微小的新希望。这工作颇为艰难:当下并无通向未来的坦途;但是我们迂回前进,翻越障碍。我们得活下去,无论多少人的世界已经天塌地陷。
多多少少,这便是康斯坦斯?查特莱的处境了。战争摧毁了她的生活。于是她意识到,人真得活到老学到老。
1917年她嫁给了克利福德?查特莱,就趁着他回英国的一个月假期。他们共度了一个月的蜜月,克利福德回到一战的弗兰德斯前线,六个月后,再被支离破碎地运返回英国来:康斯坦斯,他的妻子,时年23岁,而他29岁。
他对生命的执着堪称奇迹。他没有死,支离破碎的身体还看似复原了。整整两年时间,他命悬医生之手,后来被宣布痊愈了,活过来了。只是腰部以下的半身,就此瘫痪。
1920年,克利福德和康斯坦斯回到他的世代老家拉格比去。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克利福德袭了爵位,成了克利福德男爵,康斯坦斯成了查特莱男爵夫人。他们回归到颇为凄凉的查特莱老家,执掌门户,过起了婚后生活,收入不太充裕。克利福德有个姐姐,然而已经搬出去了,此外并无熟络的亲友。他的长兄在一战中阵亡。克利福德自己永世残疾了,也确知已不可能再有孩子,回到烟雾沉沉的中部地区的家里来,也就是尽尽人事,维系查特莱家的香火。
他并不因此颓废。他可以坐在轮椅里,推着自己行走,他还有个装了发动机的自动轮椅,可以载着自己,慢慢地绕过花园,到他引以为豪但又假装不在乎的猎园中去:那美丽又凄清的猎园。
受过那么多罪后,那些苦痛某种程度上似乎都离他而去了。他还是带着好奇、活泼、愉快,差不多可说是快活的神情,红润的脸孔看上去还健康,灰蓝的眼睛撩人而闪亮。他的肩膀宽而结实,双手有力。他衣着奢华,戴着邦德街买来的帅气领带。然而,从他的脸上,你依然看得见一点儿残疾者的呆滞与空虚。
他曾经如此生死一线,所以劫后所余的残生,对他异常珍贵。他眼神中的焦虑光芒,流露出他死里逃生的自豪。但他伤得过于严重,体内有些什么已经死灭了,有些感情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有麻木的空白。
他的妻子康斯坦斯,健壮,仿佛乡下姑娘,褐色软发,身体结实,举止缓慢,精力旺盛非凡。她有一对大大的、好奇的眼睛,声音温柔,像是刚离开乡村。
其实压根儿不是。她的父亲老马尔科姆?里德爵士,曾是著名的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她的母亲在拉斐尔前派流行的岁月,曾是个有教养的费边社社员。身处艺术家与有文化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康斯坦斯和她的姐姐希尔达,受了可称为美育的非传统的教育。她们被父母带去巴黎、罗马与佛罗伦萨,呼吸艺术的空气;她们也被带去过海牙、柏林,参加社会主义的大会,听演讲人使用每种文明语言,面无愧色。
如此这般,姐妹俩度过了一段饱含艺术与理想政治的童年。那是她俩生活的天然氛围。她们既国际化又不失乡土本色,这种乡土气的国际化艺术气质,与纯粹的社会理想并行不悖。
康斯坦斯15岁时,姐妹俩被送去德国德累斯顿,学习音乐等科目。她们在那里过得挺愉快。她们自由地在学生中间生活,她们和男人们争论着哲学、社会学和艺术问题。巾帼不让须眉,甚至因为是女孩子,所以更显出色。她们徜徉林间,与背着吉他的健美青年为伴,弦乐鸣动。她们歌唱,她们自由。自由!伟大的词汇!她们在旷野,在清晨的森林,与精力充沛、歌喉卓绝的年轻男伴,为所欲为,以及最重要的:畅所欲言。谈话是最重要的,尤其那令人动情的言谈交流;爱情,不过是件次要的陪衬品。
希尔达和康斯坦斯都在18岁时初尝爱情。那些青年们与她们热情交谈、为她们欢悦歌唱、与她们在林中自由野宿后,自然都想更进一步。她们踌躇过,但是她们畅谈过了男欢女爱的问题,这事显得如此要紧,况且,男生们又如此谦卑与恳切。那么,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就不能享受女王待遇,慷慨地赐点儿恩惠呢?
于是她们将自己赐出去了,赐给平时各自辩论问题最通透、最亲密的男人。辩论探讨很是风雅,恋爱和性交则只是一种原始的本能,事后还多少让人失望。事后,姑娘们对伴侣的爱情冷淡了,简直有点憎恨他们,仿佛男人侵犯了她们的秘密和内心自由。当然了,一个女孩所有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都在于获得绝对、完美、纯粹、高贵的自由。若一个少女的生活不能摆脱老式的、污秽的两性关系,不能摆脱可耻的从属状态,还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人怎样感情用事,性爱这东西,都属于最古老、最污秽的结合和从属状态。歌颂性爱的诗人们,大都是男性。女人们一向知道,世上有比性爱更好、更高贵的东西。如今,她们知道得更明确了。一个女人美丽纯洁的自由,比任何性爱关系都美妙。唯一不幸的是:男人们对于这点的看法太落后了,他们在性爱的事上格外坚持,像狗似的。
于是女人不得不让步,因为男人就像是贪馋的孩子。女人必须为男人所欲求的让步,供其所需,否则男人便会变得恼人、暴躁起来,像个孩子,糟蹋一段好感情。但一个女人可以表面顺从男人,却不在她内在自由的自我上退让。那些谈性说爱的诗人和其他论说家,似乎没考虑过这点。一个女人可以跟一个男人欢爱,同时并不任他支配。当然,她还可以利用这性爱,支配男人。她只需要在性爱时忍耐,让男人先逞了威风,她便可以接管战场,延长交欢,把男人当作工具,去满足她自己的高潮。
一战爆发时,姐妹俩都有了各自的初次性爱经验,匆忙赶回家去。她俩的恋爱对象,都曾对她俩热切追求、亲切谈心。她们此前从未意识到:与真正的聪明男人,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热情交谈,这是何等惊人、深刻又不可思议的美妙。从未有人对她们说过天国的诺言:“您将有可以谈话的男人。”却在她们明白其意义之前,已经成真了。
经过这些生动、直白又亲密的讨论,性爱多少变得水到渠成了,那就做吧。性爱标志着一个章节的结束,它本身也令人战栗:那是肉体深处一种奇特的、美妙的震颤,一种自我决定的痉挛。就像激奋的文章收尾词,用以意味着段落终结的一排星,一个主题终止。
她们于1913年暑假回家时,希尔达20岁,康妮18岁。她们的父亲明白无误地看出她们有过性爱体验了。一如有句法语说的,“爱已经做过了”。他自己是个过来人,便让生活顺其自然。至于她们的母亲,那时正焦虑地度过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只希望她的女儿们能够“自由”,能够“成就自我”,虽然她自己从没有成就过什么:命运没给她机会。天晓得为什么,她本来有自己的收入,有自己的生活。她将此归咎于丈夫。但事实上,她不能解决的,是她自己心灵中的某些老观念与桎梏,那和马尔科姆爵士无关:他只任她紧张又亢奋的妻子自说自话,自管自过日子。
于是姐妹俩“自由”了。她们回到德累斯顿,回到她们的音乐、大学和年轻男生们中间去。她们各自爱着她们的男伴,她们的男伴也以全副热情爱着她们。所有青年男子所能想出、说出、写出的美妙字句,他们都献给这两个姑娘了。康妮的情人好音乐,希尔达的情人懂科技。但他们都只为这二位姑娘活着,至少在精神上如此。肉体方面,他们有点讨人厌,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很明显:他们经历的性爱,在两对男女的身体上引发了奇异、微妙又显而易见的变化。女人变得更明丽,更有微妙的圆润感,少女时代的棱角软化了,面上的神色或是渴望,或是胜利;男人沉静多了,更内敛了,肩与臀也不再刚硬,而显得沉稳。
在性爱的快感中,姐妹俩几乎屈服于奇特的男性力量。但很快,她们自拔而出,将性快感看作一种感觉,于是得以保持自在。
至于她们的男伴,因为感激她们所赐予的性经验,便将灵魂交托给她们。但是不久,他们似乎觉得得不偿失。康妮的情人开始有点坏脾气,希尔达的那位则说些风凉话。男人们就是这样!忘恩负义,永不满足。你不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憎恨你,因为你不要他们;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憎恨你,为点别的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反正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什么,无论女人如何尽力,男人都不会满意。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了。希尔达和康妮,继5月回家那次后,又匆匆返乡,奔赴母亲的葬礼。她们的两个德国情人,都在1914年圣诞节前死掉了,让姐妹俩饮泣一场,情热于中,但内心深处却将他们就此忘了。他们不复存在了。
她们都住在肯辛顿她们父亲的房子里——实际上产权归她们的母亲。她们与剑桥大学某个团体的学生往来,看他们拥护“自由”,穿着法兰绒裤,法兰绒衬衣在脖子处开领,宣扬无政府主义,说话声音仿佛嗫嚅又仿佛耳语,仪态灵敏。希尔达忽然和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结了婚:此人是该剑桥学生团体的一个老成员,甚是殷富,且在政府里有个好职位,也写点哲学论文。她与他在西敏寺区的一所小屋里同居,交往的都是政府人物:那些人虽非顶尖,但都是,或即将是,国内有权威的知识分子,说起话来都头头是道,至少表面如此。
康妮做了份轻省的战时工作,与那些穿法兰绒裤、绝不妥协、嘲弄一切的剑桥学生常在一处。她的朋友是克利福德?查特莱,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原在德国波恩研究煤矿技术,刚刚匆忙归国。他先前在剑桥大学待过两年,当下是个陆军中尉,穿着军服,更可以名正言顺目空一切。
论社会地位,克利福德?查特莱比康妮要高。康妮属于小康的知识阶级,他却是贵族成员。虽非高门大户,但总算是贵族。他的父亲是男爵,母亲是一个子爵的女儿。
虽然克利福德比康妮出身更高,交涉更广,却比康妮显得更小气,更胆怯。身处狭窄的“上流社会”,即是说,地主贵族群里,他便自在些;去到充满中产阶级、民众和外国人的大社会里,他便羞怯紧张。直说吧,他有点害怕中下层阶级的大众,以及与他不同阶级的外国人。他明明挺有保障,却总有种自觉麻木的自我保护意识,挺奇怪,但在我们这时代就有这等怪事。
因此,康斯坦斯?里德的从容温柔令他迷醉。在那混沌杂乱的世界里,她的自持,比他要沉稳多了。
然而他也算个叛逆者,甚至叛逆了他自己的阶级。或者,也许,叛逆这词过于言重了。他只是跟着普罗青年,一起愤世嫉俗、反抗权威罢了。父辈们都可笑,他自己的顽固老爹尤其如此。一切政府都滑稽,我们那走一步看一步的英国投机政府,特别滑稽。军队滑稽,老头子将军也是,那红脸的陆军部长基钦纳将军,简直滑稽得登峰造极。甚至战争也是可笑的,虽则战争里要死相当不少的人。
事实上,一切都有点可笑,或十分滑稽:一切有权威的东西,无论是在军队、政府还是大学,都滑稽到了极点。至于那些故作统治状的统治阶级,也可笑。而乔弗里男爵,克利福德的父亲,尤其可笑:砍伐着自家的树木,把煤矿场里的矿工当茅草送上战场,他自己在后方安全地爱国;为了爱国,花钱花到入不敷出。
当查特莱小姐——名叫艾玛,克利福德的姐姐——从中部地区到伦敦去担当护士工作时,她私下里鄙薄着乔弗里男爵和他刚愎的爱国主义。男爵的长子兼继承人赫伯特,则公然嘲笑父亲,虽然属于他的树木都被砍下填壕沟去了。克利福德只就此不安地轻笑了一下。一切都可笑,事实如此;但这可笑若离自己太近,以至于自己都变滑稽了呢?至少其他阶级的人们,比如康妮,是挺认真的;他们有信仰。他们对于军队,对于征兵的威胁,对于儿童缺砂糖、缺糖果这些问题,很是认真。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当局可笑的错误。但是克利福德并不上心,对他而言,当局本身就是可笑的,倒不是因为糖果和军队。
大概当局者自己也觉得滑稽,于是也抽了一阵子风,局势混乱了一段时间,直至前线问题大了,劳合?乔治出来救场。这已经超越可笑了,于是目空一切的青年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1916年,克利福德的长兄赫伯特去世了,于是克利福德成了继承人。他甚至连这个都怕了起来。
身为乔弗里爵爷的儿子、拉格比世家的一员,这身份何等重大,他一直明白,他永远无法逃避他的命运。然而,他也知道:在这广阔沸腾的外界眼中,这也很可笑。现在他是继承人,得为拉格比世家负责,这事听来岂不是很可怕吗?听来堂皇,同时,还有些荒唐?
乔弗里爵爷并不以为此事有荒唐之处。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地执拗着,想拯救他的祖国、改善他的处境,不管在位的是劳合?乔治还是谁。他如此隔绝,如此闭塞,连博顿利这样臭名昭著的股票推销人,他都觉得还不错。乔弗里爵爷拥护英格兰和劳合?乔治,正如他的祖先们拥护英格兰和圣乔治;而且,他永远搞不懂这其中的区别。于是乔弗里爵爷继续砍他的树,拥护英格兰和劳合?乔治。
然后呢,他要克利福德结婚,好弄个继承人出来。克利福德觉得他父亲不合时宜,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比父亲新颖多少呢?也不过就是能嘲弄一切,再用更极端的自嘲态度对待自己罢了。无论是否真心愿意,克利福德带着最后一点儿严肃劲头,承了爵位,接掌拉格比的家业。
一战初期的巨大狂热消失了,死灭了。太多的死者,太多的恐惧。男人需要支持与抚慰,男人需要一个铁锚,好停泊在安全的港湾。男人还需要个老婆呢。
查特莱兄妹三人,以往离群索居,孤僻得令人诧异,他们认识人多,却孤独封闭在拉格比。他们都觉得孤独,因此更加亲密:虽然他们有爵位和土地,或者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会感到时时自危。他们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中部地区的工业区全然隔绝;他们甚至被父亲隔绝了与同阶级的人的往来:他们那古怪、固执、天生不爱说话的父亲,那被他们嘲笑,但又很在意的父亲。
兄妹三人先前说过,要永世住在一起。但这会儿,赫伯特死了,乔弗里男爵要克利福德结婚。他很少正式提起,他说话很少,但他静默沉郁的坚持,让克利福德难以对抗。
但是艾玛对此事说了“不”!她年长克利福德十岁,她觉得克利福德的婚姻,会背叛他们姐弟当初的约定。
然而克利福德还是娶了康妮,和她度了一个月蜜月。那是可怕的1917年,他俩亲密得仿佛将沉的船上并肩而立的受难者。成婚时克利福德还是处男,性爱对他意义不大。除了性爱方面,他俩很是亲爱。康妮还颇对这种超乎性欲、不追求男人“性满足”的感情,感到过欢欣呢。克利福德也不像别的男人,只埋头于自己的“性满足”。不,亲怜密爱比性爱更深刻,更带个人感情。性爱简直算一种意外,是附带品,是种笨拙又执拗的感官作用,没那么不可或缺。
康妮倒愿意要孩子,好稳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来对抗大姑子艾玛。然而1918年到来不久,克利福德支离破碎地被送回家来,孩子当然没指望了。乔弗里男爵于是死于忧郁。
……
前言/序言
译后记1930年3月2日,大卫?赫伯特?理查兹?劳伦斯(David Herbert Richards Lawrence)以44岁的年龄逝世时,英国公众相信他是个“将可观的才华虚掷于色情小说之上”的家伙。不登台面,略嫌可惜。
然而当时的大散文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却在他逝世27天后的信里,如此说道:“他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剑桥的评论家弗兰克?雷蒙德?里弗斯则说他的小说代表“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
这种奇妙的冲突,恰好足以概括大卫?赫伯特?理查兹?劳伦斯——即D. H. 劳伦斯——的文学人生。
1885年,D. H. 劳伦斯生在诺丁汉一个矿工家庭,母亲莉迪亚是个女工,此前当过老师。父母关系并不算好,一如他的成长环境:噪音、幽暗、肮脏、机械、英格兰的群山、森林与荒野。
他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煤矿工人的孩子一样贫穷,抬眼只能看见莽荡荒原。他的父亲像土地一样贫瘠而血气旺盛,他那做教师的母亲得不时承当丈夫的求欢之请,然后一个接一个生孩子,让家庭越来越贫穷……D. H. 劳伦斯是家里第四个孩子:对一个穷家庭来说未免多了点。
D. H. 劳伦斯是个浪漫主义者,这很奇妙:他开始写作,去雨果彩笔大绘《巴黎圣母院》已有八十年,离勃朗特姐妹们满怀自然主义情感、叙述英国庄园与不屈女性形象也已有半个世纪。
1910年他25岁,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小说《白孔雀》,同年他母亲逝世。有传说他亲手将安眠药递给母亲,以成全那可怜妇女的安乐死。此后,这个女人一直活在他的小说里。《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到处可见他母亲的痕迹。他那部带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儿子与情人》中,莫雷尔夫人的死去成为主角人生的转折点,这不妨视为劳伦斯的自况。
1911年,劳伦斯着手写他第二部小说《侵入者》,小说题材来自劳伦斯的朋友海伦?科克,描述她与一个已婚男人惨烈的爱情故事。这是他对婚外情题材感兴趣的开始。
1912年3月,劳伦斯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大他六岁的弗里达?维克利。弗里达本是劳伦斯的现代英语教授恩斯特?维克利的妻子,她与劳伦斯私奔逃去德国。1914年,弗里达得以与丈夫离婚,1914年7月13日,弗里达与劳伦斯正式结婚。
1916―1917年,劳伦斯写作《恋爱中的女人》时——这部小说和《虹》出版时都曾遭禁——他与一位叫威廉?霍金的农民感情好得过分。弗里达相信他俩发展出了同性性爱。与此同时,一战期间,反战的劳伦斯被当局刁难。这一点令他对一战留下了彻底的糟糕记忆。
进入20世纪20年代,劳伦斯身体多病。他常居意大利,多次回英国旅行都不太快乐。1928年,他出版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他最后一本大部头小说。小说最初在佛罗伦萨杜丽印刷,1960年才得以在英国公开发行——那是劳伦斯逝世三十年后的事了。至于此前此后,被禁被删改引发的轩然大波,足够另外写一本比小说更长的论述。仅仅在美国,《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便被誉为“一场性运动革命”。
但那是1930年过世的劳伦斯,所无法料及的。
不难发现,劳伦斯人生中的许多印记,都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闪现:煤矿家庭;温婉有学识的母亲;拐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女人私奔;等候离婚;结婚……《儿子与情人》也许自传体色彩更浓郁,但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投注了劳伦斯自己的神魂血气,谅来相去不远。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若要一言以蔽之,并不难:年轻的康妮因为贵族丈夫克利福德瘫痪阳痿,于是与丈夫的猎场看守成了情人,同居,图谋提出离婚。
仅此而已。
但这就是小说的妙处了:一句故事梗概,并不能带出小说的全貌。
许多读者,是冲着“禁书”字样来的。著名的性爱场景,奔放的肉欲,偷情的妻子——听起来很刺激。这大概也是同时代英国人的观感。
但劳伦斯的野心,不止于此。
小说的大量篇幅,集中在风景。这是浪漫主义小说家们的爱好。在劳伦斯这里,风景有了情绪,有了愤怒。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相信民族、血统、神秘主义、悬崖、古堡、山庄、雷雨、家族故裔、海盗。而康妮与两腿瘫痪、家资巨富的先生一起经过萧索的平原,目之所及,不是流水或草坪,而是煤矿。小说前六章的宴会、煤矿和小小的偷情故事,无非在暗示:工业时代的机械叮当声,正在屠灭自然、感官与欲望。
小说虽是全知视角,但主视角,基本在康妮。一个细节:小说里的奥利弗?梅洛斯,基本以“他”或“猎场看守”的字样出现。故我们不妨说,这是一个康妮苏醒自立的过程——从肉欲,到精神,逐渐醒转。在男欢女爱之中,她找到了久已被机械文明压制的自己。
似乎生怕读者不明白,劳伦斯周而复始地,借着猎场看守之口,布道般地强调这一点。一战的阴影,机械文明吞噬英格兰大地的噪音,被煤矿生活异化得仿佛鬼魅的普通人,都是他要攻击的对象。终于在漫长的对决后,瘫痪后满脑子利益的克利福德与质朴的猎场看守,机械文明与自然主义,精神至上与狂野肉欲,康妮选择了后者。
但还不止于此。
在小说中,康妮觉醒的肉欲,带有一种母性的、土地的色彩。一个斯文的女人,投入一个带有浓重口音的、“粗野的”猎场看守的怀抱,而且发现了生活的激情和乐趣。他带着恋慕的调子,描写康妮的动人形象:母性的温柔,对世界略带懵懂,在山林天风的呼啸中,找回自己的血气与灵魂。爱情是辉煌的,而爱的尽头是性。用性与爱将情绪蒸熏而起,进入他所擅长的抒情节奏。
——我们不妨理解为,这是他怀念母亲的方式。带着绝望,但生机勃勃。
劳伦斯对现代文明,有一种断然的决绝。他笔下的工业时代和煤矿,代表着他粗野的父亲,以及令大地变得丑陋又现实的文明。所以康妮与克利福德的对抗,可以理解为英国传统自然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对抗,也是劳伦斯自己强调的:人类内心本能与机械文明的对抗。
所以某种程度上,小说真正的主角,是被机械文明开拓到荒芜粗野的英国大地。劳伦斯钟爱这片大地,钟爱女性的本真的温柔。因为对抗强烈,所以他笔下决绝。劳伦斯小说中的人或事,美妙中总伴随残缺。出版本书三年前的1925年,他如是说:
“一个人写作是因为他无法忍住不写作……他觉得他内里有些必须说的东西,比他以往所说的更好;如果你有才华而不与世界分享,那是绝对的错误。”
一般评论家都认为,劳伦斯有许多缺点:长篇小说的结构经常紊乱,对内心描绘孜孜不倦到几乎忘我,进入抒情节奏后一发不可收拾。但你很难不被他的情绪所感染:“我不需要上天和天命的怜悯,我从骨子里是一个斗士。”
他是燃烧自己的天才,喷薄的热情胜于叙述的理智;天生的诗人,所以小说的语感奇妙得绚丽又柔美;世界忙于描绘文明与社会时,他却返回内心的世界。他不是编年史家的陈述者,而是创造者。他从来拒绝妥协,令人意外地鲁直,态度与小说一样激情而突兀。
他著名的《凤凰》这样写:
你是否乐于被遗忘、被擦除、被取消、消失无踪?
你是否乐于消失无踪?
湮没无闻?
如果不,你将永远无法真正改变。
凤凰恢复青春,
只有当她燃烧,活活燃烧,直至烧尽,
然后,鸟巢里新的小家伙带来微的生机,
显示着,她正恢复青春,如同鹰——那永生的鸟。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就是他作为凤凰,最华丽的一次自我燃烧。暴雨,森林,肉欲不灭的火焰。这股热情会灼伤一些人,却令另一些人热血沸腾。这就是大卫?赫伯特?理查兹?劳伦斯,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所谓“我们这一代最伟大、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
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以及一个普通的劳伦斯爱好者,本书是我第一次试图翻译英文长篇小说——我都不好意思称之为译作。2015年秋天到2016年春天的翻译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我感受到了作为译者的绝望与惶恐:翻译能表达意思,而如劳伦斯这样诗意盎然的小说家,其或磅礴,或微妙的音韵,着实难以一一照搬。
半个世纪前,查良铮(穆旦)先生,曾与丁英一先生辩论翻译。查先生如是说:
“有时逐字‘准确’地翻译的结果并不准确。……译诗不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风格表现出来……要紧的,是把原诗的主要实质传达出来。……为了保留主要的东西,在细节上就可以自由些。这里要求大胆。……译者不是八哥儿;好的译诗中,应该是既看得见原诗人的风格,也看得出译者的特点。”
傅雷先生也抱持过类似的意思:“理想的翻译,应当是想象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将此书再写一遍。”
所以翻译一道,实在没有止境。音韵与节奏既无法翻译,译者只能追求无限接近,却无法彻底还原。与原文珠联璧合、意韵皆衬的翻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对原作者越是崇敬,翻译时的惶惑感愈重。
所以本书若有可取之处,都是劳伦斯先生的功劳。若有糟糕的地方,应该全是我的责任吧。
2017年1月7日,于巴黎
用户评价
坦白讲,这本书的叙事手法非常大胆,甚至有些让人感到不适——但正是这种“不适”,才构成了它独特的魅力。作者似乎完全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情节驱动,转而专注于对人类心理复杂性的解剖。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读一个故事,而是在进行一场深入的心理学实验。那些对话,往往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表面上谈论的是天气、是家务,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权力、渴望和深深的压抑。每次我以为自己把握住了人物的动机时,作者总能用一个突如其来的内心独白,将我推翻重来。这种不断自我否定的阅读体验,极其耗费脑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智力满足感。它不给你确定的答案,它只是将冰冷的、未经修饰的真相摊开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拼凑、去定义。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这种“碎片化”的叙事节奏,但一旦进入状态,那种仿佛窥探到人性最隐秘角落的兴奋感,是其他通俗小说无法给予的。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密度极高,几乎每一句话都承载着多重的含义,读起来有一种“咀嚼”的质感。它的语言风格典雅、考究,但又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直白,尤其是在揭示社会虚伪性这一点上,毫不留情。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频繁地查阅一些词汇,因为作者使用的词语往往精准地捕捉到了一种特定的、难以名状的情绪状态,是日常口语无法替代的。这种阅读上的挑战性,反而成了吸引我的地方,它迫使我跳出舒适区,去学习一种更精确的表达方式。它探讨的主题宏大而永恒——关于自由、关于妥协、关于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自我实现——但所有的探讨都落实到了最具体、最私密的人物互动之中,使得宏大叙事没有沦为空谈。整本书读下来,就像经历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蜕皮过程,虽然过程艰辛,但最终带来的那种精神上的洗涤感,是极为深刻和持久的。
评分我通常偏爱结构紧凑、节奏明快的作品,所以一开始对这本的厚度和它那近乎散文诗般的章节感到有些犹豫。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它的结构虽然松散,却有着内在的、非线性的逻辑。它更像是一部音乐作品,有反复的主题(比如关于社会阶层和女性处境的探讨),有高亢的变奏(那些爆发性的、情绪失控的瞬间),也有漫长的、近乎冥想的休止符。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人物的成长和环境的变化,都显得异常真实和渐进,而不是突兀的转折。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在于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贵族阶层内部生活细节的洞察。作者显然做了大量的考据,无论是服饰、餐桌礼仪还是社交潜规则,都描绘得入木三分,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那种被繁文缛节束缚的窒息感。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读完”,不如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压抑的季节。
评分初接触这类题材时,我总担心会陷入刻板印象的窠臼,但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极为出色。它避开了所有廉价的戏剧冲突,转而深入挖掘那些微妙的、几乎无法用语言捕捉的“失位感”。主人公们看似拥有了一切,但实际上却被困在由自己或他人构建的精致牢笼里。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于“沉默”的运用。很多时候,情节的推进不是靠激烈的争吵或明确的行动,而是靠长时间的沉默,靠一个眼神的闪躲,靠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所暗示的巨大信息量。这要求读者必须具备极高的情商和解读能力,去倾听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这绝对不是一本能让你放松地“躺平”阅读的书,它需要你全神贯注,像对待一份复杂的历史文献一样去审视每一个词语。读完后,我甚至开始反思自己日常交流中那些被我忽略掉的非语言信号,可见其对现实感知的冲击力之大。
评分这本小说,说实话,初读时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那种细腻入微的笔触,描绘的场景和人物内心活动,简直就像一幅幅慢镜头下的油画,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我记得有那么一个章节,主人公在雨中的花园里徘徊,那种潮湿、阴郁,又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期待感,被作者用一种近乎诗意的语言捕捉到了。你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腥味,感受到雨滴打在皮肤上的冰凉。但这种慢节奏并非拖沓,而是一种刻意的雕琢,它强迫你放慢呼吸,去体会那种缓慢滋长的情感张力。它不是那种一目了然的激情故事,而是更像一部深潜入海底的探险,你必须适应水压,才能看到那些深藏在幽暗中的瑰丽珊瑚。我尤其欣赏作者对环境氛围的营造,那种隐秘的、带着古典气息的庄园背景,似乎本身就成了故事的一个无声角色,见证着一切暗流涌动。读完后,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那种带着湿气的、古老建筑特有的味道,以及人物之间那种欲言又止的、克制到极致的情感交流,非常考验读者的耐心,但回报也绝对值得。
评分纸质很棒,里面还有一张油画书签。
评分不知道咋样,朋友交代买的,京东送货超快
评分名著 值得一看
评分很不错的书籍!
评分知乎、豆瓣逾百万粉丝,腾讯《大家》超人气作者张佳玮倾情翻译D.H.劳伦斯zui著名、争议zui大的小说——20世纪经典名著《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评分翻译很到位!你懂的!五星评价!
评分还不错
评分还没看,冲着翻译这买的,关注其微信公众号
评分还可以吧,随手给个五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