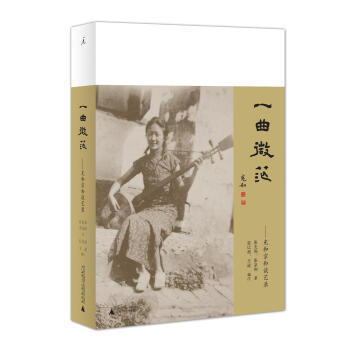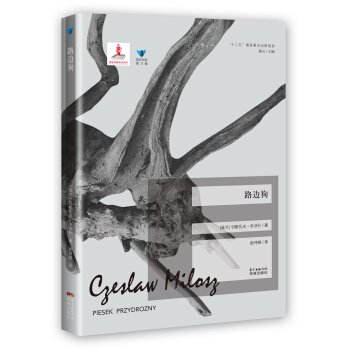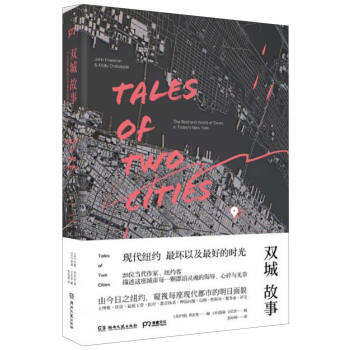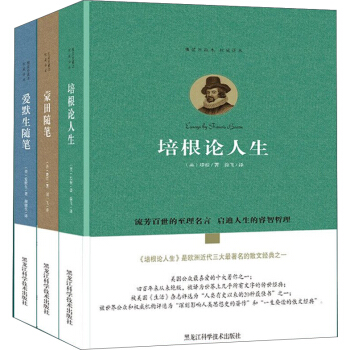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奥斯卡金像奖、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得主,电影大师费里尼人生自述
★只有费里尼,同时征服艺术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只有费里尼的作品,四次获奥斯卡蕞佳外语片奖
★讲述费里尼电影内外的写意人生,像《蛤蟆的油》一般趣味满溢,像《雕刻时光》一般执着动人
★费里尼的文笔让卡尔维诺赞誉有加,费里尼的电影让侯孝贤赞不绝口
★我的生活就是拍电影。那是我,那是我的生命——费里尼
★新经典电影人书系全新力作,精心设计,精装典藏,带你走近真正的电影大师
内容简介
《拍电影》是电影大师费里尼的人生自述。
他出生在意大利的小城里米尼,与小伙伴用书本做武器排演《伊里亚特》,用黏土和纸壳做人偶,还躲在屋子里给自己化妆,钦佩世界上每一位真正的小丑。他从不觉得自己会长大,更没想过能拍电影,然而当喊出那句“预备,开机,停”,便仿佛天生就应该干这一行。
他,就是费德里科·费里尼,电影世界的魔法师。
在《拍电影》中,费里尼追忆了自己的似水年华,讲述了对电影的奇思妙想,以及电影与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羁绊。透过他直率幽默的话语和对艺术的个性化解读,我们将在字里行间重新领略迷人的“费里尼风格”。
作者简介
费德里科·费里尼(1920-1993)
知名导演。生于意大利北部的里米尼小城。年轻时做过记者、编辑、电影编剧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担任导演工作,先后拍摄《大路》《甜蜜的生活》《八部半》等二十余部影片。他执导的电影4次获得奥斯卡蕞佳外语片奖,他本人也在1993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此外,他还获得过戛纳电影节四十周年奖、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等。
费里尼以强烈的个人风格扩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成为欧洲艺术电影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他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并称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被誉为20世纪影响广泛的导演之一。
精彩书评
★年轻时在戏院看的《大路》令我感动。欣赏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电影,就不能错过《我记得》与《八部半》这两部代表作。
——侯孝贤(知名导演)
★费里尼这样的天才是历史上仅有的,希望意大利还能出现像他这样的大师。
——乔治·纳波利塔诺(意大利总统)
目录
我记得……
与罗西里尼相遇
开机
卡比利亚之夜
信手涂鸦
编故事
情迷朱丽叶
萨蒂里康
献给马戏团
电视
罗马
再见里米尼
电影是什么
结语
附录:费里尼电影创作表
精彩书摘
昨天晚上我梦见里米尼港湾,澎湃苍绿又骇人的大海,如大草原般滚动,海面上厚重的云块朝向陆地奔腾而去。
巨大的我从小小的、狭窄的港湾出发,想游到大海去。我告诉自己:“我如此巨大,但大海终究是大海,要是游不到呢?”然而我并未因此而苦恼,仍继续在小海湾中伸长了手臂划水。我不会溺毙,因为脚碰得到底。
这是一个膨胀的梦,或许是想让我重拾对大海的信心。一个自我保护的小小机制:诱惑人高估自己,或者低估那些可能会限制自己起跑的障碍。总之,我搞不清楚到底是应该抛弃起步时的小港湾情结,还是应该高估自己。
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并不十分乐意回里米尼。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障碍。我的家人还住在那里,我母亲,我妹妹。我是惧怕某些感情吗?主要是我觉得,回到那里是一种对记忆欣然但自虐的反复咀嚼,这是一种戏剧和文学的动作。当然,它自有魅力。昏昏欲睡且混乱的魅力。其实是我没法把里米尼视为一个客体,不如说,也只能说,它是记忆的世界。的确,当我人在里米尼时,总是被已经存档、安抚过的记忆幽灵袭击。
如果我留下来,这些纯真的幽灵说不定会默默向我提出令人困窘的无声的问题,而我不能用完全相反的意见或谎话来回答它。我必须从家乡找出缘由,不含任何欺骗。里米尼是什么?它是一个记忆的世界(虚构、掺假、被侵犯的记忆),而我利用它如此之久,以至于心里没有一丝尴尬。
但我不得不继续谈它,甚至有时自问:终有一天,当你遍体鳞伤、疲惫不堪、不再有竞争力,难道不想在这片港湾买一栋小房子吗?老城那一边的港湾,小时候,我在对岸看着它,看着船骨搭造起来。海湾靠这边的一半,让人联想到喧闹嘈杂的日子,与开奔驰轿车往海边去的德国人一点儿也不搭界。
其实,早期那里都是贫穷的德国人。突然间沙滩上随处可见斜躺的自行车和篮子,水中则满是小胖子与“大海象”(矮胖的大人)。我们小孩子戴着羊毛罩耳帽,由我父亲的伙计带到海边。那个时候,在老城那边的港湾,我只看到了枯枝,还听到一些声音。
前一阵子,通过朋友蒂达·本齐,我买了一栋房子,价格低廉。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固定点,或许可以回归纯朴生活。不过这不可能成真,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看过那房子一眼。其实,光想到一栋紧闭的房子,没有房客,在那儿空等,我就觉得不舒服。
当我决定卖掉房子时,蒂达跟我说:“那可是你的家乡!”好像在提醒我,不要再一次背叛它。
在此之前,蒂达曾说服我在马雷奇亚买了一小块地。那地方看起来很适合谋杀站街女郎。
我们去看地的那个傍晚,听到一阵军乐声。一个穿四角裤的男人正在吹降旗号。他是菲奥伦蒂尼,知道所有加里波底的事迹。此外,他还研究桑祖维斯葡萄酒。他的家里堆满了印刷品、军旗和破烂古董。那晚,始终穿着一条四角裤的菲奥伦蒂尼仿若泥偶的脸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他说:“我看到一张很和善的脸,可是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怎么会?”蒂达说,“是费里尼!”“天杀的……”菲奥伦蒂尼惊叹道。接下来他马上说:“我找到了一瓶桑祖维斯葡萄酒……得让你们尝尝。”他是个酒鬼,有点顽固,因为我没用手心暖杯而吼我。“来嘛,费里尼。”蒂达继续说,“来住这里嘛。”“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钓鲻鱼了。”菲奥伦蒂尼很有把握地说。马雷奇亚这一带因为多石,一片荒芜凄凉。但是蒂达建议我买下那块地。“你等着,小白痴,”蒂达说,“这里将有公路通过,地价会涨。”结果公路开到另一边去了,现在菲奥伦蒂尼向我出价五十万里拉,但地还是我的。
我第一次去马雷奇亚时,还是小孩。我们在学校当“海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逃学了。我跟在卡林尼后面。河边有一辆黑色的巴里拉汽车,里边坐满了警察。他们像青蛙那样,下到遍布卵石的河滩。有几朵云低垂着慢慢游荡,掉入树梢枯枝设下的圈套。我们走进一处杨树林,有一个人上吊了,他头戴鸭舌帽,身边守着两名警察。我当时没搞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只看到一只掉落的鞋和没穿鞋的脚上的男袜,还有两条满是补丁的裤管。
里米尼的家。那些我住过的家,我还记得很清楚;只有一个例外,我出生时的家,在夫玛卡利路。我七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坐马车漫游。那是在冬天,马车车篷紧闭,我们六个人挤在车内:我父母、三个小孩、一个女佣,在黑暗中堆叠。车窗也得关上,否则雨水会进来。我什么都看不见。阴暗里,只见到父母的脸。能坐在马车夫旁边真是极大的快乐,因为只有那儿可以呼吸。
那个星期天下午,马车转进一条我从没走过的大道,一排房子,一栋紧临着一栋。爸爸说:“你是在那儿出生的。”而马车一溜即过。
我真正记得的第一个家是利帕大楼。它还在,是大街上的一栋大楼。房东总是一身蓝:蓝衣服、蓝色圆顶帽,还有一大把白胡子,像供人朝拜、不可侵犯的神祇。我母亲一面把手擦干,一面说:“孩子们,不要动,利帕先生来了。”然后老先生就进来了。一天早上,我听到一阵咆哮,外带悠长的哀鸣。大楼中庭挤满了牛和其他牲口。或许有市集或大拍卖,我不知道。
想着里米尼,一个一笔成形的词(Rimini),一排小士兵,我无法把它客体化。里米尼是乱七八糟,是夹杂不清,是不寻常,是温柔,是宽阔的胸襟、空旷的海洋。在那儿,乡愁格外清澈,尤其是冬天的海、白色的浪花、狂飙的风,如我第一次所见。
另一个家,也就是我们住过的另一栋房子,靠近火车站。这个家让我察觉到“天意”的蛛丝马迹,那是一座屋前有花园的小别墅,屋后的大菜园跟一栋庞大的建筑相连—一个军营,一间教堂?那上面用白色字母圈写成半圆形:“里米尼剧场”。少了两个字母,掉了,不见了。由于我家的菜园比较低洼,所以矮墙后面那片立有建筑物的土地看起来特别高,像立在墙头。
一天早上,我想在菜园用芦苇搭一扇拱门,突然听见一阵嘈杂声。是剧场铁卷门发出的巨响,我从没注意过的铁卷门正在上升,最后露出一个巨大的黑洞。正中央,有一个穿风衣戴巴斯克帽的男人和一个打毛衣的女人。他俩有这么一段对话。男人:“凶手应该是从窗户进来的。”女人:“窗户是关着的。”男人:“强纳顿下士发现有撬开的痕迹。”
然后那个男人问待在菜园的我:“树上有无花果吗?”“我不知道。”
他们来自史塔拉契·赛伊纳提剧团,正在排一出恐怖剧。
在那个男人的帮助下,我进到黑洞里。我看见了舞台和头顶正上方挂在几根绳子上颤颤巍巍的火车头,夹在红、白、黄色的赛璐珞之间。
那是剧场。
之后,那男人继续窗子的话题。我不懂那是一种游戏还是什么。大概过了很久,我忽然听见母亲在叫我:“饭好了。”“他在这里。”戴巴克斯帽的男人回答了我母亲的呼唤,然后帮我重新跨过矮墙。
两天后,父母带我去看戏。母亲说,在演出期间我一动也不动。火车头从幽暗的布景中向前推进,那是深夜,它几乎就要碾过一名被绑在铁轨上的女子。待那名女子被救起,上方便猛然落下巨大、沉重又柔软的红布幔。
这样的激动持续了整晚。中场休息时,我去看了侧面的布景、剧场正厅后排的小沙发、天鹅绒布、铜管乐器、回廊,还有神秘的走道,我像只老鼠在里面窜来窜去。
这个靠近火车站的家,也是我交上第一个朋友的家。至于那个位于克雷蒙提尼路九号的家,则是初恋的地方。房东(奥古斯提诺·道奇,五金店老板)是路易吉诺的父亲。路易吉诺是我的高中同学,那个在《伊利亚特》剧中扮演赫克托尔的家伙(我们自己演的《伊利亚特》)。
对面大楼里住了一户南方人,姓索里安尼,有三个女孩,艾尔莎、碧扬奇娜和内拉。碧扬奇娜肤色微黑,从我的卧房就可以看到她。她第一次出现在玻璃窗后面时,好像——我不记得了——穿得很女人,胸脯美丽而丰满,已经像是做母亲的人了。
如今住在米兰的她说,我们并没有像我描述的那样(我描述的?)逃到波隆那①,最多只是骑自行车—我载着坐在横杆上的她—去了奥古斯都城门外。
那个时候,对我而言,阿姨是女人的代名词。当然,我也听说过住着某种女人的房子。靠近河边,克洛迪亚路上的朵拉之家,“河畔朵拉”。可是当大家谈到女人时,我脑海里只有那些在奶奶家做床垫的阿姨、用筛子筛麦子的干贝托拉的女人,所以我当时并不懂,之后我察觉到有些女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朵拉之家会租两辆马车,每十五天一次地在大街上展示新来的雏儿作为宣传。于是,我会看到涂脂抹粉的女人,戴着奇怪而神秘的面纱,用金烟嘴抽烟:朵拉之家新来的女人。
干贝托拉,罗马涅省的内地,小时候我夏天都会去那儿。我奶奶总在手里握着一根藤杖。她可以用它来使男人像卡通人物般跳起来。总而言之,她能让那些当天雇来要到田里工作的男人乖乖站好。早上,先是会响起一阵喧闹的吱吱喳喳,之后,那些粗鲁的男人像进了教堂似的,恭恭敬敬地来到她面前。接下来,奶奶分配咖啡牛奶并管理一切。她要尼克拉呼气,好知道他有没有喝酒。他便用手肘顶一顶旁边的人,腼腆地笑着,变成了小孩子。大黑巾罩着头和口鼻,一对眼睛晶亮如沥青,我的奶奶法兰洁丝卡像是“坐着的公牛”①的同伙。她对动物也有非凡的能力,猜得出它们的病痛、情绪、想法和花招:那匹马不知怎么回事,爱上那只母猫了。“再过三天‘嘉本’会来。”她无比自信地宣布,而且准确无误。“嘉本”是罗马涅特有的风,反复无常,变幻莫测,完全无法预测—对其他人而言如此,对她则不然。
奶奶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比她老一点儿,也比较壮,每天晚上都去小酒馆接她喝酒的丈夫,把他放在手推车上带回来。他叫恰帕洛斯,并不是希腊名字,意思是“捡骨头”。一天晚上,在受过大家的嘲笑后,男人双腿悬在妻子拖拽的手推车外,一副安心苦修的样子。就是那晚,在那顶破帽子下,我遇见了那个男人的目光。
农民之间经常争吵。有三个姐妹和一个男同性恋为了一份遗产争执了二十年之久。他们互丢粪便,偷对方的鸡,持续不断地移动土地交界的围篱。直到一天清晨,三姐妹显然经过了一夜的深思熟虑,决定到男同性恋家里,用拍地毯的藤拍把他痛打一顿。
我希望有一天能拍一部关于罗马涅农民的电影,一部没有左轮手枪的美国西部片,片名叫“去他的圣母马利亚”,是句骂人话,不过就发音而言,要比“罗生门”好听。
有个叫纳西的人老是说:“我能控制而且我想控制。”他双腿残废,因为他坐在树枝上锯树的时候坐错了位置。他是个牲口贩子。
这个纳西,像极了罗马涅古代滑稽戏的一种面具。由于断了腿,他的动作跟鱼鳃一样起起伏伏,像只青蛙。他一开始以歪七扭八的姿势行进时,就喊道:“我能控制而且我想控制。”有一次,他从老是穿着法西斯党服、长靴锃亮、胡尖抹过肥皂像大头针一样直挺的泰欧多拉尼的嘴里抽出香烟,说:“现在你不准抽烟,现在纳西抽烟。”
每当我想起干贝托拉,想起一位身高两米的修女,想起那些在火光中驼背的人、破旧桌子后面的瘸子,脑子里就闪过希罗尼穆斯·波希①。
干贝托拉也有吉卜赛人和向阿布鲁佐山区迁移的烧炭工人经过。晚上,在动物可怕的嘶叫声后,一个烟雾腾腾、衣衫褴褛的身影就出现了。先看到火花,然后是火苗。那是阉猪人,从大路上来,穿着千疮百孔的黑斗篷,戴一顶破帽子。猪群已提前感觉到他即将现身,惊恐得吭哧乱叫。阉猪人跟全镇的女人上床。有一次,他让一个可怜的白痴怀了孕。大家都说那是恶魔的孩子。我为罗西里尼写的电影短片《奇迹》,灵感就源于这里。还有那促使我实现《大路》的心底骚动,也源于此。
在乡下,从吉卜赛人那儿,我常常听到关于爱情迷药和巫术的事。我想到一个女人,安吉莉娜,曾到家里来做床垫(应该要有一整章献给这些行业:磨刀工人和他的破车、全身墨黑的烟囱清扫工和最令佣人害怕的人物)。安吉莉娜要在我奶奶家住三天,还包吃。有一天,她正在把一个个棉花球缝进床垫里,我瞥见她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匣子:一个小玻璃盒,里面装着一绺打了结的毛发。“那是什么?”我问她。“这些是我的头发,那些是我男朋友的胡子,是我趁他晚上睡觉时剪下来的。这样,去特里艾斯特工作的他就跟我紧紧绑在一起,不会分离。”
另外,马雷奇亚的小市场里,有一位老人可以使鸡和羊生病或痊愈。
俱乐部附近有一个铁路工人的老婆会“恍惚出神”。她这样治病也能赚不少钱。有一天,我也排入要去接受诊治的老先生和老太太的队伍中,最后我站到一间小客厅的门口,房间里简直是家徒四壁。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脸上喷洒了水珠的老太太,弓着脊背,身体僵硬,跟一个我看不见的人说:“克拉—多那—累—特罗—佩—特(那个女人比你强),你得让她去。”说完话后,老太太哭了起来。后来走出一个惊慌的大男人,他不愿被人看见。他站在阶梯上,头上戴着帽子,不肯离开。或许他是想找到勇气,再回去寻求不同的神谕。
大家也常谈到那些住着幽灵的鬼屋。“卡尔雷塔”是我朋友马里奥·蒙塔纳利的别墅。据说一百年前,别墅主人在灌醉表妹后把她掐死了。他们说,有些夜晚,可以听到酒窖里传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大家认为,那是被掐死的表妹戳破酒桶的橡皮盖往杀她的凶手嘴里灌酒,好让他不得安宁,永远溺毙在酒里。
罗马涅—海上冒险和天主教教堂的混合体。这儿有圣马力诺,一座阴郁而自命不凡的山丘。一种奇怪的狂妄自大和渎神心理,掺杂着对上帝的迷信与挑战。老百姓没有幽默感,也不设防,但是喜欢嘲弄和自我吹嘘。有一个人说:我可以吃下八米长的香肠、三只鸡和一根蜡烛—居然还有蜡烛,简直是马戏团表演。然后,他真这样做了。一吃完,他们马上用摩托车把他载走了。他脸色发紫,眼睛翻白,而大家面对这种残忍和死亡的威胁却放声大笑。
有一个家伙叫“由山上升起”。是升——我也不懂——而不是降:就仿佛一次假想的空中散步。还有“哦不”,四海漂泊的水手,偶尔会寄一张明信片给他在拉乌尔咖啡馆的朋友:“经过鹦鹉岛,想起你们大家。”
这一带有一种口音,极为甜美,或许来自大海。我记得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夏日午后,在一条阴影层层叠叠的小巷子里:“现在几点?”“应该恰好四点……”有人回答。而小女孩哼哼唧唧,好像是说一定比这晚:“哼,才没有恰好……”
同时,女人有东方式的肉欲冲动和态度。早在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位尚未皈依的女管家,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工作服,一张脸因为血脉偾张引起的疖子而红扑扑的。很难说她多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的女性特征像俗语所说的,一触即发。总之,这女人搂着我,摩搓着我,身上散发出马铃薯皮、蛤蜊汤和修女衬裙的味道。
我读的幼儿园是圣文森修道院建的,有大帽子修女的那所。有一天,正在排队准备一场宗教仪式时,她们让我负责握一支小蜡烛。一名戴眼镜的修女—很像电影演员哈罗德·劳埃德—指着蜡烛,以不容争辩的语气说:“不要让它熄灭,因为耶稣不喜欢。”那时刮着很大的风,幼小的我被那巨大的责任湮没。有风,而蜡烛不能熄灭。否则耶稣会怎么处置我?队伍开始行进,缓缓地,沉重地,随着手风琴的乐声碎步移动。一段小快步,然后静止;又前进,再次静止。领队在干什么?行进仪式中还得唱歌:“我们要主,他是我们的父……”夹在一群长袍修士、神父、修女之间,突然,一股绝对的忧郁、死亡和严肃的气氛迎头罩下。就是这队人吓到我了。最后,我哭了起来。
一二年级我念的是特阿提尼小学。我在班上都跟那个一同在马雷奇亚看到有人上吊的卡森尼一起玩。老师是个爱打学生的人,节庆的时候才变得特别友善。家长们带来一包一包的礼物,堆叠在讲台上,像主显节前夕那样。收完礼物后,在我们放假之前,他都要我们唱:“青春啊青春,春天多美~~~~丽。”他非常重视那四个“~”。
之后几年,我被送去法诺,在一所慈爱的神父们管理的寄宿学校读书,跟小金鲷的相遇就发生在那段时期,一如我在《八部半》中的描述。
回到里米尼,我就读的中学位于马拉特斯提安诺路,现在已改成市立图书馆和美术馆了。当时,我觉得这所中学是一座高耸入天的大楼,上楼和下楼都是一种探险。那些阶梯永无尽头。校长绰号“宙斯”,标准的自大狂。他有硕大无比,跟600型小汽车一样大的脚,用它残杀小孩。被他踢一脚能让你的脊椎骨断裂。他总是先假装不动,然后出其不意地用那只大脚把你像蟑螂一样踩得扁扁的。
中学那几年是属于荷马和“战斗”的时光。我们在学校读《伊利亚特》,并得牢记在心,我们每个人都以荷马书中的一个人物自居。我是尤利西斯,有点孤僻,老是望着远方;当年已经微胖的蒂达是埃阿斯;马里奥·蒙塔纳利是埃涅阿斯;路易吉诺·道奇是“驯马人赫克托尔”;斯塔克奇奥蒂是“飞毛腿阿喀琉斯”—他每一年级都要重读三遍,所以是班上年纪最大的。
下午时分,我们会找一个小广场重演特洛伊战争,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所谓“战斗”。我们带着用绳子绑好的书(那时大家习惯如此),然后挥舞着书互相攻击,展开一场书本和绳鞭的混战。
于是,《伊利亚特》在课堂上再度上演时,班上同学的脸已然与那些荷马笔下的英雄合而为一。这么一来,那些英雄人物的冒险事迹便成了我们自己的冒险事迹。所以,有一天,我们往下读着《伊利亚特》,读到了对埃阿斯的评论,荷马称其为“愚蠢的行尸走肉”。
“埃阿斯”蒂达便怀着对荷马的恨意开始抗议,仿佛诗人的这句话把他自创世纪以来的名声都毁了。
赫克托尔死亡的时刻到了,“赫克托尔”路易吉诺·道奇,历经了他伟大的一刻。可怜的路易吉诺!像条蛔虫似的在特洛伊城墙外被拖着走:
那张脸,
那张原先焕发如宙斯的脸,
如今血污斑斑,
在敌人的狂喊声中垂向祖国的土地。
路易吉诺死了,
目睹凶残景象,
母亲打散头发,揭去面纱,
一声哀号
冲上星空。
用户评价
(一) 最近无意中翻到一本《拍电影》,说实话,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本非常枯燥的技术手册,充斥着各种晦涩的术语和复杂的设备参数。但读着读着,我发现它远不止于此。作者似乎有着一种神奇的魔力,能够将原本可能令人望而却步的电影制作过程,拆解成了一连串充满趣味和启发性的步骤。它不是那种告诉你“怎么做”的书,而更像是“为什么这样做”的引导。比如,在谈到镜头语言的时候,它没有罗列各种景别和运动的定义,而是通过分析经典电影片段,生动地展现了不同镜头组合所能营造出的情绪和叙事张力,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剪辑室,与导演一同斟酌每一个画面的选择。那种对细节的考究,对情感的捕捉,以及对叙事节奏的把控,都让我感到豁然开朗。它鼓励我去思考,去感受,去尝试,而不是死记硬背。我甚至觉得,就算你没有任何拍电影的经验,也能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领略到电影的魅力,甚至激发出一些创作的冲动。这本书像是一位老友,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推你一把,告诉你:“你也可以!”
评分(二) 我必须承认,《拍电影》这本书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我对“幕后”的刻板印象。我一直以为拍电影是一群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和技术宅的“阳春白雪”,但这本书以一种极其接地气的方式,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它不是高谈阔论那些虚无缥缈的艺术理论,而是从最基础的“想法”如何变成“画面”开始,一步步深入。我尤其喜欢它对“故事”的探讨,如何构思一个引人入胜的剧本,如何塑造立体丰满的人物,以及如何利用镜头语言来“讲”故事,而不是仅仅“呈现”故事。它里面引用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得入木三分,让我瞬间明白,为什么有些电影能触动人心,而有些却索然无味。书中对“团队合作”的强调也让我印象深刻,原来一部电影的诞生,凝聚了那么多人的心血和智慧,从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到剪辑、配乐,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这种集体创作的理念,让我看到了电影的另一种美,一种协作的艺术。
评分(三) 我一直是个电影爱好者,但对于电影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却知之甚少。《拍电影》这本书,就像是一扇窗,让我得以窥探到电影制作的奇妙世界。它的叙述风格非常流畅,一点也不生硬。读起来感觉像是跟一位经验丰富的电影人聊天,听他娓娓道来那些关于光影、关于色彩、关于声音、关于表演的种种秘密。它没有过多的理论灌输,而是通过生动的例子和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明白了许多过去困惑不解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同样的场景,不同的镜头调度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为什么音乐能在短短几秒钟内,调动起观众最深层的情感?这本书不仅仅是在教你“怎么拍”,更是在引导你去“怎么看”。它提升了我作为观众的鉴赏能力,让我能更深入地理解电影的艺术价值,更能体会到创作者的匠心独运。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许多电影学院的入门读物,因为它真正触及了电影的灵魂。
评分(五) 很少有一本书能让我从头到尾都如此投入,并且在合上书本之后,仍然意犹未尽。《拍电影》就是这样一本让我沉迷其中的书。它没有试图将所有电影制作的知识都塞给读者,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具启发性的道路。它更侧重于“思维方式”和“创作理念”,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教会你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表达”。我尤其欣赏它对于“细节”的关注,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元素,在书中却被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了影响观众情感的关键。它告诉我,电影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宏大的场面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更在于那些隐藏在画面深处,不易察觉的匠心。这本书让我明白,拍电影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一种可以将生活中的观察和感悟,转化为影像语言的艺术。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电影制作背后那份纯粹的热爱和执着。
评分(四) 这是一本让我重新审视“电影”这门艺术的书。以往我对电影的理解,大多停留在“看”的层面,享受它带来的视觉盛宴和情感共鸣。而《拍电影》则把我带到了“创造”的维度,让我看到了那些光鲜亮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辛勤的付出和精巧的设计。它不仅仅是关于技术,更是关于“如何用视觉语言来表达思想和情感”。书中的某些章节,比如关于“情绪的营造”和“氛围的烘托”,让我茅塞顿开。它并非机械地告诉你灯光要怎么打,而是让你理解光影在塑造人物内心世界中所起到的微妙作用。对于那些渴望进入电影行业,或者只是对电影制作充满好奇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它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让你能清晰地认识到电影制作的完整流程,以及其中每一个环节的专业性和重要性。我从中获益良多,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
评分用神卷买的书,超值,赞一个!
评分费里尼的经典之作
评分618促销买的,人工智能是情怀是时尚是工具是装饰是乐趣
评分没有想的好
评分物美价廉,活动给力
评分没有想的好
评分印刷精美,质量不错不错,值得信赖
评分不错的书,推荐大家一起购买!!
评分刚入门不知道买什么书,从网上查到这个书好,所以学习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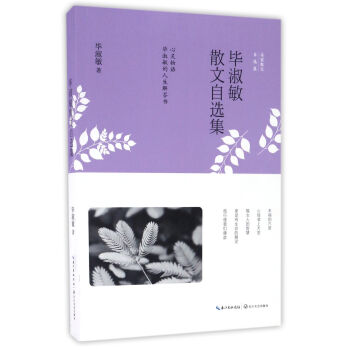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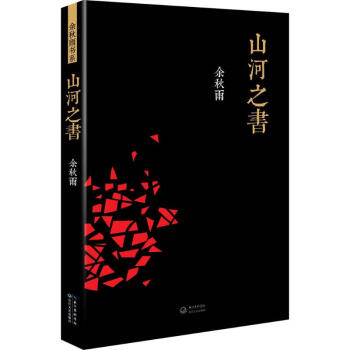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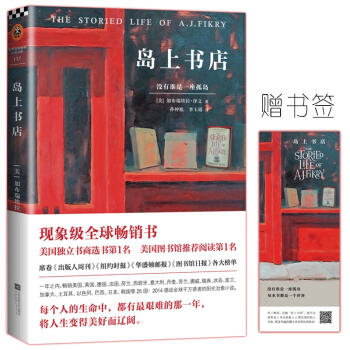
![中国神话传说 [Chinese Myths and Legend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181944/59cdbfbdNd9815e6a.jpg)

![中国少年儿童阅读文库·影响孩子一生的经典故事:100个智慧故事(彩图注音)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38760/rBEhVFJvCZ8IAAAAAAQCREvNhQgAAEtYAMcsEUABAJc604.jpg)
![世界儿童文学精选:小公主(拼音美绘本)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70637/558280ceN3dfcdb0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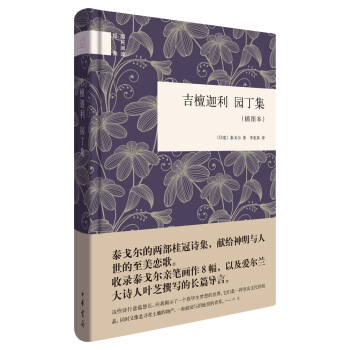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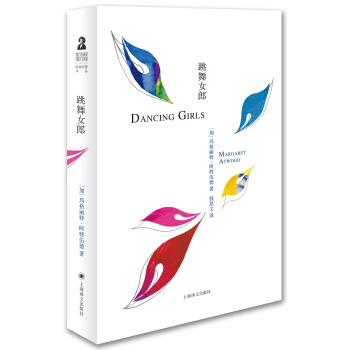
![秘密花园 [7-14岁] [The Secret Garde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72347/56b0188eN0874aa9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