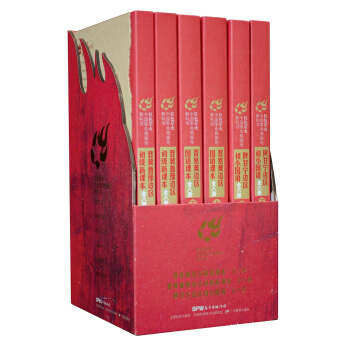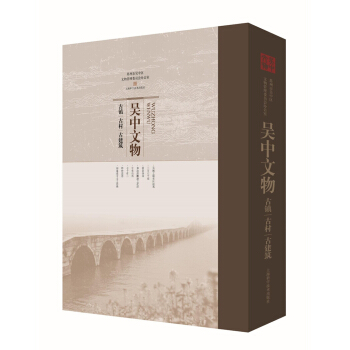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满文翻译领域之力作,足以填补清史、民族史、宗教史之空白。
内容简介
《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第1次对涉及雍和宫的满文历史档案、文献作了系统的翻译梳理,这批满文档案,涉及僧俗各类事务,将其翻译整理,既对研究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有较高学术价值,亦对目前我国之宗教事务管理及对雍和宫保护维修、佛事活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雍和宫档案译稿是该领域翻译研究的杰作和精品,其信、达、雅之妙不同凡响,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等不可限量。雍和宫作为北京地区的重要标志之一,在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一书对于弘扬北京文化,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北京的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赵令志,1964年7月生于内蒙古赤峰市。1987年7月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部,读中国民族史硕士研究生。2007年,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美兰,中国第1历史档案馆编研处研究员,曾翻译满文档案《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与赵令志教授合著《准噶尔使者档之比较研究》。
内页插图
目录
1.内大臣海望传著拣员管理雍和宫事务等之上谕雍正九年十月十七日
2.和硕庄亲王传著雍和宫二等侍卫侉色教练内府佐领兵丁之上谕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二日
3.著雍和宫头等侍卫劳格补放郑各庄城守尉之上谕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4.和硕庄亲王奏闻修缮柏林寺所需银仍支领雍和宫银两应用事折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5.西宁办事大臣马尔泰等奏闻派员护送果莽寺敏珠尔呼图克图进京事折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6.大学士鄂尔泰等奏闻西宁办事大臣马尔泰派员护送果莽寺敏珠尔呼图克图进京事片雍正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7.大学士鄂尔泰等奏闻西藏送京喇嘛随班禅额尔德尼使者业已起程片
雍正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8.侍郎马尔泰等奏闻料理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自西宁起程前往京师折
雍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9.总管内务府奏请嵩祝寺番经厂佛像开光所需物件于何处开销事折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10.郎中黑德等来传饬营造司以将海望所建房屋一座辟作藏经馆事行文雍和宫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一日
11.总管内务府为雍和宫后佛楼新添小道童等钱粮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三日
12.和硕庄亲王奏闻议覆大行皇帝梓宫奉移雍和宫折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13.著将御前侍卫富努监禁百日释服之后再行请旨之上谕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14.郎中杨作新传大臣海望饬拣员照料雍和宫修缮工程文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15.管理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释服之日照例令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等于乾清宫念经事折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八日
16.管理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闻梓宫奉移雍和宫简派散秩大臣值守事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17.管理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圣上前往雍和宫不必早去事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18.宫殿监副侍李英差传支给雍和宫太监等口粮事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19.雍和宫值班内务府衙为调取苏州织造海保履历等事咨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20.雍和宫值班内务府衙为一并调取郎中海保等升补情形及其履历事咨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21.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宁寿宫皇贵妃前往雍和宫著照例备办车轿鞍马事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22.雍和宫值班内务府衙为回执入值内务府总管人员名单等情事咨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23.内务府为备办宁寿宫皇贵妃等前往雍和宫及皇太后皇后等回宫所需仪仗等事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24.领侍卫内大臣为奏事郎中张文彬等传谕圣上前往雍和宫并妥办应备事宜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25.雍和宫值班内务府衙为询查世祖圣祖如何施恩奶母两家等情事咨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26.领侍卫内大臣为知照圣上前往雍和宫事咨总管内务府文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27.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为宁寿宫皇贵妃等前往雍和宫著照例备办车轿鞍马事文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28.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为皇太后皇后等前往雍和宫著照例备办车轿鞍马事文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29.领侍卫内大臣为奏事郎中张文彬等传旨圣上前往雍和宫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30.总管内务府为皇后妃嫔前往田村仍照雍和宫例备办车轿鞍马事咨领侍卫内大臣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1.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为皇后妃嫔前往田村仍照雍和宫例备办车轿等事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2.总管内务府为王大臣饬办圣上前往雍和宫日赏沿途兵丁等饭食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3.总管内务府为派员替换备办圣上前往雍和宫日赏沿途兵丁等饭食官员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4.总管内务府为传王饬办赏神武门至雍和宫沿途兵丁饭食事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5.总管内务府为传王大臣等谕旨备办圣上前往雍和宫沿途兵丁等饭食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6.总管内务府为传大臣等遵旨饬办圣上前往雍和宫日赏沿途兵丁饭食搭建大棚事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7.总管内务府为传王大臣等差员饬办赏神武门至雍和宫沿途兵丁饭食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8.总管内务府为遣员照料圣上前往雍和宫日赏赐沿途兵丁做饭大棚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39.总管内务府为遣员替换备办圣上前往雍和宫日赏沿途兵丁做饭大棚官员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40.领侍卫内大臣为圣上前往田村及雍和宫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41.总管内务府为派员备办圣上前往雍和宫日赏沿途兵丁做饭大棚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42.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皇后妃嫔前往田村所需马匹照前往雍和宫例备办事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43.总管内务府为照新定尺寸搭建做饭大棚事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44.领侍卫内大臣为奏事郎中张文彬等传旨圣上前往雍和宫献供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45.值月镶红旗满洲蒙古都统为上谕给奉移梓宫官兵加薪等情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46.值班景运门前锋统领为知照圣上前往雍和宫沿途兵丁执牌用饭等情事呈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47.值班景运门前锋统领为知照裁减圣上前往雍和宫沿途官兵人数事呈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48.銮仪卫为知照圣上前往雍和宫备轿校尉人数事呈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49.总管内务府为传王大臣等备办神武门至雍和宫沿途兵丁饭食粮米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50.总管内务府为传王大臣等晓饬严肃纪律事致管理做饭大棚事务官员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51.总管内务府为传王大臣等晓谕严肃纪律事致管理做饭大棚事务官员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52.总管内务府为奉宸苑人手紧缺召回调出备办兵丁饭食人员事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53.管理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参奏老格偷窃雍和宫供奉金盏事折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54.以和硕庄亲王等员丢失雍和宫金盏著严加议处之上谕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55.内阁抄出以镶白旗人员看护雍和宫等差务之上谕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56.赏赐乾清宫念经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等喇嘛缎匹银两单
雍正十三年九月
57.总管内务府为重申雍和宫大行皇帝供献等项事宜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58.领侍卫内大臣为奏事郎中张文彬等传旨前往雍和宫供献事咨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59.步军统领衙门为分拨凉棚用饭兵丁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60.吏部为开单议叙雍和宫工程效力人员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61.领侍卫内大臣为奏事郎中张文彬等传旨圣上前往雍和宫供献事咨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62.总管内务府为急速增员办理雍和宫田务事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四日
63.领侍卫内大臣为知照圣上前往雍和宫供献并瞻礼佛楼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五日
64.署理户部尚书事务内大臣海望口奏以雍和宫头等侍卫常保等补放圆明园总管等事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65.正黄旗满洲为转行上谕给奉移梓宫官兵加薪等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日
66.关防处为调整雍和宫等处官差人员事呈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67.署理户部尚书事务内大臣海望奉旨以雍和宫头等侍卫常保等补放圆明园总管事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68.领侍卫内大臣为圣上前往雍和宫供献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69.总管内务府为员外郎济保仍于雍和宫钱粮事务上行走事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70.总管内务府为另遣他员查办雍和宫事务事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71.领侍卫内大臣为知照圣上前往雍和宫供献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72.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备办皇太后皇后等前往雍和宫所需车轿等事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73.领侍卫内大臣为圣上前往雍和宫供献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74.领侍卫内大臣为圣上前往雍和宫供献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75.内阁抄出总理事务庄亲王奏议大行皇帝诞辰之日仍着丧服行礼等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76.总管内务府为济保仍于雍和宫查办事务上行走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77.领侍卫内大臣为圣上前往雍和宫供献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78.总管内务府奏请赏给皇宫与雍和宫间行走引导等员双薪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79.吏部为开单议叙办理丧仪效力人员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80.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备办皇太后皇后前往雍和宫所需车轿等事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81.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备办宁寿宫内主子等前往雍和宫所需车轿等事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82.入值散秩大臣永谦等为奏事郎中张文彬传旨圣上前往雍和宫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83.入值散秩大臣玛哈达为圣上前往雍和宫照例备办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84.总管内务府为遣员替补参领赫达色入值巡察事致都虞司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85.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等差传备办皇太后皇后前往雍和宫所需车轿事文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86.雍和宫坐班内务府衙为遣员替补员外郎萨兰泰事咨呈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87.内阁抄出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等奏闻遵旨议处和硕诚亲王等守灵失职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88.领侍卫内大臣为奏事郎中张文彬等传旨圣上前往雍和宫供献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
89.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为给柏林寺等处笔墨银仍于雍和宫支给等事之堂谕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90.雍和宫坐班内务府衙为调员入值雍和宫管理扫雪等事咨呈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91.宗人府为知照内阁抄出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等遵旨议处和硕诚亲王等守灵失职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92.和硕庄亲王等奏请照例支给万寿寺等处香供银两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93.正黄旗为回覆知照和硕庄亲王允禄参奏老格偷窃雍和宫供奉金盏折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94.礼部为知照上大行皇帝尊号之日皇帝仪礼等情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95.总管内务府参奏顺贞门门禁正黄旗内府护军统领伊福旷班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96.吏部为核实雍和宫工程议叙人员职名文稿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97.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等差传每日上诣田村仍照前往雍和宫例备办太监等所需马匹等事文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98.元旦前往雍和宫行礼之上谕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99.总管内务府奏闻察议顺贞门门禁正黄旗内务府护军统领伊福旷班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00.领侍卫内大臣为圣上前往雍和宫祭祀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101.领侍卫内大臣等为知照议处乾清门行走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等失职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
102.总管内务府奏请采办雍和宫供奉所用羊只事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103.总管内务府为传和硕和亲王等派员饬办雍和宫欠项银两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104.总管内务府为传和硕和亲王等派员饬办雍和宫欠项银两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105.总管内务府为传和硕和亲王等派员饬办雍和宫欠项银两事致各该处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
106.总管内务府奏请御前侍卫富努违制监禁百日期满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107.和亲王传旨以侍郎刘保暂行帮办雍和宫内务府总管事务之堂谕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108.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明日圣上行礼火神庙仍照前往雍和宫例备办马匹事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109.宫殿监侍领侍苏培盛差传备办随驾前往雍和宫太监等所用马匹事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110.总管内务府为大臣刘保等传明日于雍和宫备蒙古医士一名事致上驷院札付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111.总管内务府奏闻以丢失雍和宫供奉金盏案内失职大臣丁皂保等降级补用事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12.总管内务府为知照丢失雍和宫供奉金盏案内失职大臣丁皂保等降级补用事咨吏部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13.坐班雍和宫内务府为传和硕和亲王等饬已届年底严加警戒事咨内务府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14.管理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请圣上于正月初二日前往雍和宫行礼事片
雍正十三年
115.管理总管内务府事务讷亲等奏请清理雍和宫所存什物数目事折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116.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闻核查雍和宫各类人员事折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117.管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讷亲等奏请清理雍和宫所存物件交付各处事折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118.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闻安置雍和宫各类人员事折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119.管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讷亲等奏请雍和宫所属打牲乌拉朱轩达所得珍珠交广储司银库折
乾隆元年三月初八日
120.管理内务府总管事务讷亲等奏请雍和宫所属打牲乌拉朱轩达所得珍珠交广储司银库折
乾隆元年三月初八日
121.总管内务府奏览雍和宫所属打牲乌拉朱轩达所得珍珠事折
乾隆元年三月十六日
122.总管内务府奏请按品补用雍和宫归入上三旗佐领侉塞等员事折
乾隆元年四月初四日
123.总管内务府奏为对品补用雍和宫归入上三旗佐领侉塞等员事折
乾隆元年四月初四日
124.总管内务府为知照将雍和宫内管领五十等以六品内副管领对品补用事咨吏部文
乾隆元年四月初八日
125.总管内务府奏请安置雍和宫侍卫官员护军校等事片
乾隆元年四月十六日
126.总管内务府奏请雍和宫庄园头人等已遵旨赏给和亲王事折
乾隆元年四月十六日
127.总管内务府奏请雍和宫庄园头人等已遵旨赏给和亲王事折
乾隆元年四月十六日
128.总管内务府奏请对品补用雍和宫归入上三旗护军校玛希图等事片
乾隆元年四月十八日
129.总管内务府为知照将雍和宫归入上三旗护军校玛希图以主事对品补用事咨吏部文
乾隆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130.总管内务府奏请将雍和宫归入上三旗羊群头目班第以催总对品补用事片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131.总管内务府奏请将雍和宫归入上三旗羊群头目班第以催总对品补用事片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132.总管内务府为将雍和宫归入上三旗羊群头目班第以催总对品补用事咨吏部文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133.礼部为知会皇上万寿节谒雍和宫行礼之仪注事咨总管内务府文
乾隆元年八月十一日
134.总管内务府奏请将雍和宫归入上三旗六品内管领王保对品补用事片
乾隆元年八月三十日
135.总管内务府奏请雍和宫归入上三旗六品内管领王保以内副管领对品补用事片
乾隆元年八月三十日
136.赏赐皓月清风亭子念经之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等喇嘛缎匹银两单
乾隆元年八月
137.总管内务府为知照对品补用雍和宫归入上三旗内管领王保事咨吏部文
乾隆元年九月初五日
138.总管内务府奏闻宁寿宫内廷等位前往雍和宫拣员引导事片
乾隆元年十月初八日
139.总管内务府奏为宁寿宫内廷等位前往雍和宫拣员引导事片
乾隆元年十月初八日
精彩书摘
1、内大臣海望传著拣员管理雍和宫事务等之上谕
雍正九年十月十七日
十七日,内大臣、户部左侍郎兼内务府总管海望传旨:前交显亲王、衍璜、马尔赛等办理雍和宫事务。今马尔赛既已赶赴军前,著派常明、永福办理雍和宫奏事等事务。再,现正用兵,著将应裁撤之雍和宫周围堆拨裁去,免旗兵守卫,将内务府佐领下护军、披甲人等编班值守。钦此。
奉常[明]大人饬,将此交付都虞司,著以本官职衔、永[福]护军统领职衔缮写行文,本日即将无印公文行至雍和宫,晓谕办理雍和宫事务人员,明早前来见我等,不得迟延。
(都虞司笔帖式六格抄去)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1-7)
2、和硕庄亲王传著雍和宫二等侍卫侉色教练内府佐领兵丁之上谕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二日
十二月初二日,和硕庄亲王传旨:著派雍和宫二等侍卫侉色同七十等,共同管理训练内务府佐领下两千兵丁。钦此。
(都虞司笔帖式郝善抄去)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1-9)
3、著雍和宫头等侍卫劳格补放郑各庄城守尉之上谕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谕:郑各庄城守尉达素之缺,著以雍和宫门头等侍卫兼参领劳格补授。钦此。
将此交付于兵部主事晗笃。
(佛顺缮,唐古里核)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20-87)
4、和硕庄亲王奏闻修缮柏林寺所需银仍支领雍和宫银两应用事折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汉文】初七日,和硕庄亲王臣谨奏:为奏闻事。
臣遵旨将柏林寺应行粘补之处,派员估计需用木植、砖瓦、灰斤工价等项,共需银三千四百余两,遵旨仍支领雍和宫银两应用。其监修官员,臣拣选内务府官一员,同郎中苏和讷兼管修理。臣亦不时查看。工竣之日,将用过钱粮数目详查,另行奏闻。为此谨奏请旨。等因缮折。交与奏事郎中张文彬等转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满文】奉王谕,著选派内务府员外郎商林,会同苏和讷监修。
(都虞司笔帖式富成抄去)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1-22)
5、西宁办事大臣马尔泰等奏闻派员护送果莽寺敏珠尔呼图克图进京事折
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臣马尔泰、臣达鼐、臣三达里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准理藩院咨开:二月初十日奉上谕,现京城内精通佛经之大喇嘛稀少。闻西宁果莽寺之敏珠尔呼图克图所学甚好。著咨行马尔泰、达鼐等,晓谕伊等办给牲畜口粮,委派妥员,护送来京。钦此。钦遵,等因咨行前来。
臣马尔泰、达鼐即差笔帖式,迎接敏珠尔呼图克图,转降谕旨。据敏珠尔呼图克图告称,从前果莽寺破败,蒙圣主睿鉴,为弘扬教法、逸安众生,得重新修葺,赐名广福寺,此后教法大兴。雍正五年,小僧充达赖喇嘛之使,前往京师,屡次朝觐天颜,蒙施厚恩,甚为垂怜,节次蒙恩,似须弥山般无穷广大。此恩如何能报,唯尊奉佛法,竣成《甘珠尔》、《丹珠尔》经,供奉讽诵。小僧尝亲自赴藏,召集众喇嘛讽诵,恭祝圣主万寿、教法弘扬、众生安逸,冀以朝觐天颜。今圣主降旨,宣召进京,小僧闻知即不胜欣悦感激,即欲遵旨前往,然不能不将寺中事务托付稳妥之人。故今回寺,俟诸事办竣,自三月二十日由西宁起程。等语。
臣等即令地方官员,办给敏珠尔呼图克图及随行念经拉穆扎巴等僧徒三十人所需驮乘牲畜、沿途盘费银两。派随臣等办事之兵部员外郎五十七,妥为照料送京。令于三月二十一日自西宁起程。沿边差遣,所用钱粮数目除报该部销算外,为此恭谨奏闻。
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九日。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1-26)
……
前言/序言
译者前言
乾隆九年(1744年)谕令将雍和宫改为寺院后,雍和宫随即发展成为清朝内地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和宗教活动与管理中心,在联系清朝中央政府和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清政府将雍和宫作为与蒙藏等地区宗教上层联络的纽带,故其对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间思想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雍和宫仍属藏传佛教名刹,为北京地区寺院建筑保存最完整,驻锡喇嘛最多,佛事活动完备、宗教文化独特的佛教活动场所,仍为内地及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之核心,对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雍和宫旧址原为清代驼馆,康熙四十年(1701年)在此为皇子修建两座府邸,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康熙皇帝将西侧府邸赐给四子胤禛,将东侧府邸赐给八子允禩。胤禛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五月入住。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胤禛府邸按亲王府规制扩建成为“雍亲王府”。胤禛继皇位后,于雍正三年(1725年)降旨将雍亲王府升为行宫,赐名“雍和宫”,乃乾隆出生之潜龙邸。目前,关于改宫为庙之动因,坊间素有乾隆帝认为潜龙邸雍和宫乃神爽凭依之地,理应清净纯洁,不宜由秉性乖张之和亲王弘昼继承,复成藩王列邸之说,实乃对清代皇子分府制度与清廷兴黄教以安蒙藏之政策,缺乏了解。
与明朝藩王实行采邑制度不同,清代皇子婚后分府,赐予府邸、牛录、庄园、人丁,但所赐府邸、庄园等,仍属于隶属内务府之皇产,各皇子仅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此乃清廷经常收回王府,改赐他人,王府屡次易主之所在。虽然弘昼亦出生于雍和宫,但并无继承雍和宫之权,其成婚后亦已另分府邸,因而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将雍和宫赏给和亲王弘昼居住时,乾隆认为雍和宫“系皇考肇迹之区,若令列邸分藩居此发祥之地,不特邻于亵越,并恐无福衹承”,且雍正帝已升祔太庙,此外尚有宫中奉先殿、景山寿皇殿、圆明园安佑宫等奉祭之所,更不宜将此行宫辟为专祀雍正帝神御之所,因而将雍和宫改造为皇室供奉三宝之家庙,最为妥协。
清朝兴黄教以安蒙藏之政策,滥觞于入关之前。入关后,顺治、康熙、雍正皇帝进一步推行此政策,“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收效甚巨。然不足者,京城并无藏传佛教大寺,对清廷推衍黄教多有不便。诚如乾隆帝所谕:“推究佛学之广博精深,归于喇嘛之勤奋。西昭乃自古以来传播佛学,创立黄教之地。其于佛学理论、习经以及戒律等,甚属严谨,为各地佛学之典范。朕乃弘扬黄教利益众生之施主,褒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并勤于尊崇佛教、弘扬黄教之处,遍及唐古特全区及至于北京、多伦诺尔、呼和浩特、席热图昆仑、喀尔喀哲布尊丹巴之库伦、西宁等地。其中北京地域宽广,更应按照西昭之例,创立学院,教习喇嘛,以弘扬黄教。惟所有寺庙之喇嘛,本土人居多,除遵守戒律诵经外,辨经、坐禅、传授佛学高深理论者无多”,改变这种寺院及高僧分布不均的局面,使北京亦成为尊崇、弘扬黄教之中心,建立规格较高的黄教寺院,抑或为乾隆帝深思熟虑之事。故在否定将雍和宫赐给弘昼之议后,降旨“朕念雍和宫乃甚属吉祥伟大之所,今在闲置,依照宫殿之坐落、样式,稍加修缮,辟为大杜冈,作为供佛及喇嘛会集之场所。由西昭召来熟悉辨经制度之三四十位大德高僧住寺教习众喇嘛外,蒙古人等历来虔诚信佛,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所属各旗,选送勤于习经、聪颖、年岁二十以上喇嘛一二人,若仍不及额数,亦可于现在各寺庙闲散班第内选其聪慧者,充额喇嘛五百人,供给钱粮,免其官差,按照昭地学院之例管教。其学业优秀者,褒奖补放他寺达喇嘛、副达喇嘛,考试并给予嘎布楚、兰占巴等学位。懒散者昭示众人,作为懒惰例。若各扎萨克地方,愿送其他习经之人亦可居寺学习。寺内众喇嘛俱勤于习经,若各地皆效仿行事,实乃有益于佛教及众生。”这道关于改庙的上谕,在阐明其对佛学的认识和立场的同时,对雍和宫改庙之缘起到寺庙建制、师资和僧徒来源以及寺庙的财政支持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指示,其考虑诚可谓无所不及。
将雍和宫辟为黄教大寺之事,受到蒙藏僧俗各界赞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郡王颇罗鼐等上表庆贺,各地蒙古王公遵旨陆续选派本旗符合条件之喇嘛前往雍和宫习经。乾隆皇帝指示达赖喇嘛自西藏哲蚌寺、扎什伦布寺等选派显、密、医、杂四扎仓上师,并从三大寺挑选十八名格西级经师,送往雍和宫。达赖喇嘛等遵旨办理,在雍和宫改建且尚未开光之前,既“由哲蚌、甘丹、温都孙等大庙喇嘛内,拣选熟谙经文,能守净道”、堪膺“教授经艺之喇嘛二十二名,其僧徒喇嘛五十二名,通共七十四名”送往京城,可谓超额选送。嗣后,复从西藏、青海各寺邀请呼图克图进京驻于雍和宫,故该寺改建伊始,即成为蒙古地区培养黄教经师之中心,皇家举行诸多佛事活动之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开始实施的确定活佛转世呼毕勒罕的金瓶掣签制度,将雍和宫作为“金瓶掣签”地之一,使雍和宫进一步成为清代蒙古和京师地区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心,其在蒙古及京师藏传佛寺院中的地位愈加突出。自雍和宫改庙至清末,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十三世达赖喇嘛及章嘉呼图克图等来京,均曾于雍和宫驻锡梵修、讲经传法、授戒收徒。乾隆皇帝以及之后的历代皇帝每年也都依例三次“盛装隆从,威严如仪”地到雍和宫拈香礼佛。喇嘛活佛以及清朝皇帝在雍和宫举行的诸多佛事活动,达到了清廷“以政御民,以教御心”的目的,加强了蒙藏地区上层宗教集团对清政府的向心力。
清朝对汉人推行儒家思想,并通过开科取士、修《四库全书》和提倡理学等手段,使北京成为儒家文化的发展中心,清朝皇帝亦以集“治统”与“道统”于一身自诩,因而北京无疑成为儒家文化发展的掌控中心。而在蒙藏地区推行黄教,以理藩院管理喇嘛印信、度牒,并在雍和宫设金奔巴瓶,以金瓶掣签方式掌控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使北京亦成为控制藏传佛教之中心之一,如此,北京作为驾驭全国的首都的功能便更为突出。清帝既是理学的倡导者,又系黄教之大施主,此乃与历代皇帝有别之处。迄今,关于北京是清代儒家文化中心及清帝倡导理学之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北京也是藏传佛教管理中心及清帝在藏传佛教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因而,本书之出版,抑或对后项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清政府对雍和宫的僧俗事务非常重视,分别设官管理。在长期的宗教活动和行政管理中形成了大量的档案文献,既有皇帝的谕旨、也有内务府、理藩院等部门官员的奏折,以及相关衙署往来的文件,目前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雍和宫档案即达数千件。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既是清代雍和宫历史的见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和体现了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弥足珍贵。2002年,雍和宫管理处委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清代雍和宫的相关档案,共同陆续出版24册《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收录满汉蒙等文字档案3100余件。所收档案种类庞杂,主要为上谕、字寄、奏折、奏片、咨文、呈文、札付、传文、记注、仪注及档案附录的粘单、报单、清单、附件等,可以全面反映雍和宫改庙、建置、管理、财务、教育、礼佛、诵经、金瓶掣签等各方面情况,实属研究清代民族与宗教的罕见史料。因雍和宫属皇家寺院,隶属内务府,与蒙藏地区文移往来,皆通过理藩院,按清代之定制,凡关涉理藩院、内务府、宗人府、八旗、民族、军事、边疆、陵寝等事务者,必须以清语折奏,因而清代雍和宫的档案,绝大多数是满文档案。目前,学界能准确翻译利用满文档案者,仍寥寥无几,故《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出版后,利用者有限,没有达到预期效果。2012年,雍和宫管理处与我联系,欲翻译其中的满文档案,冀以进一步发掘这批档案的价值。
这批满文档案,涉及僧俗各类事务,将其翻译整理,既对研究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有较高学术价值,亦对目前我国之宗教事务管理及对雍和宫保护维修、佛事活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学术研究方面,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档案,值得注意:
1、寺院管理:雍和宫管理可分为行政事务管理和宗教事务管理两部分。在行政管理上,雍和宫为皇家藏传佛教寺院,直属清廷管辖,由皇帝简派一名亲王或郡王担任“领雍和宫事务大臣”,管理雍和宫事务。而实际具体事务,系由理藩院、内务府兼管办理。遇领雍和宫事务大臣缺出,则由理藩院尚书、侍郎联衔开列名单,请旨简派。在领雍和宫事务大臣下,设总理雍和宫东书院后佛楼事务大臣,简称“总理雍和宫大臣”,员无定额,一般自王公及各部院、内务府总管大臣内拣派。寺内设文案房、经坛房、造办房,分别管理文移往来、僧人诵经、造办佛像诸事,由该处郎中、员外郎、内管领、笔帖式、拜唐阿等执事司职。本书所译之满文档案,多数为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有关于雍和宫建置维修、购置地亩、财务收支、诵经需用、道场服务、物品保管、官员任免、造办佛尊、堆拔执更等方面的满文档案,几近其半。从这些档案中,可以了解清代对寺院之管理制度,尤其在财务管理方面堪称完备,对所记各类需用物品之详细,折合银两之精算,令人叹为观止。对我们现今管理僧俗事务机构,颇有可鉴之处。
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清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喇嘛度牒制度。驻京喇嘛,“大者曰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曰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其次曰扎萨克喇嘛,其次曰达喇嘛、曰副达喇嘛,其次曰苏拉喇嘛,其次曰德木齐、曰格斯贵,其徒曰格隆、曰班第”,其中“扎萨克喇嘛给予印信,其余格隆、班第等给予禁条、度牒,不给印信”,并发给相应口分钱粮。上述僧职中扎萨克喇嘛共有四缺,其中一缺专属雍和宫。理藩院下设喇嘛印务处,具体负责管理喇嘛事务。各寺院喇嘛皆有定额,在内地黄教寺院,以雍和宫额设喇嘛最多,为504缺,约占驻京喇嘛总数2217定额之四分之一,足见雍和宫之特别。与其他寺院不同,在雍和宫扎萨克喇嘛之上,又设“管理雍和宫总堪布喇嘛”之职,简称雍和宫总堪布,地位颇高,一般聘请驻京或藏地呼图克图担任。本书内有一些自西藏等地聘请呼图克图、达喇嘛至京城传经,担任总堪布、堪布之职,管理雍和宫等寺院的档案,系研究寺院管理的罕见资料。
2、培养人才:为蒙古地区培养藏传佛教人才,乃雍和宫之重要任务之一,此从乾隆帝改庙之谕令内即可知晓。清朝历代皇帝虽将蒙古视为藩篱,王公作为亲戚,但对蒙古诸部因藏传佛教而与藏区交往过密,皆心存顾虑,对蒙古各部奏请自藏区聘请高僧弘法传教之事,基本予以否决,往往谕令驻京呼图克图前往。乾隆皇帝为了满足蒙古各部宗教信仰之需要,使蒙古诸部心系北京,倾心内向,于雍和宫改庙伊始,即于此创立显宗、密宗、杂明、医明四大扎仓,自西藏聘请精通教法之高僧主持各扎仓,乃以此四大经学院,为蒙古地区培养喇嘛。当时学僧定额80名,其中今内蒙古地区60名,即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每盟各10名;外蒙古20名,给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赛因诺颜部各5名。所译满文档案内,有许多谕令蒙古各部送学经喇嘛至雍和宫各仓学习、学成归部后续选送喇嘛、此类学经喇嘛每月诵经及应给口分钱粮等方面的档案,乃研究雍和宫经学教育之珍贵档案。
此举使雍和宫成为北京乃至内地藏传佛教寺院中,学经组织最为完备的寺院,为蒙古地区培养了大批黄教人才,成为内地重要的黄教学府和培养蒙古地区黄教人才的中心,并客观上阻滞了蒙古喇嘛赴藏地学经和藏区喇嘛至蒙古地区传教的情况,使蒙古各部敬佛学经的视野,定格于雍和宫。如此在蒙古地区弘扬黄教,达到了乾隆帝“建筑一座庙,胜养十万兵”之目的。另外,在乾隆初期与准噶尔汗国和平通使期间,噶尔丹策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喇嘛达尔扎均请自西藏聘请高僧,到准噶尔汗国传教,以振兴该地黄教,乾隆帝拒否所请,作为转圜,同意其与蒙古诸部一样,可选送10或20名幼年喇嘛到北京学经,并负责一切费用,此乃乾隆帝将准噶尔等同诸外藩蒙古之意,为准噶尔汗以无出痘幼年喇嘛可送而否决。
3、佛事活动:作为皇家寺院,雍和宫担负着为皇家诵经及举办各类佛事活动的任务。清廷在宫中设置“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处”,简称“中正殿念经处”,具体安排皇家诵经等活动。雍和宫主要佛事活动可分为诵经和节庆两部分。其中诵经有内课、本课、随营、外课之分,尤以内课、本课为主。
内课系指雍和宫作为皇家寺院,在清宫、御园或其他寺院为皇室进行的祈福诵经,具体由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处安排。据(乾隆)《大清会典》内《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定例四十一条》规定,雍和宫喇嘛每天都要为皇室诵经,所诵经典主要包括《吉祥天母经》、《无量寿佛经》、《大晏护法经》、《喇嘛递供献经》、《威胜天王经》、《时轮王佛经》、《救度佛母经》、《药师经》、《四大护法经》、《救护经》、《龙王水经》、《大游戏经》、《尊胜佛母经》、《财宝天王经》、《金刚经》、《乐师经》、《吉祥经》、《斗母经》、《长寿佛坛城经》、《大怖畏坛城经》、《毗卢佛坛城经》、《清净经》、《宗匣经》等,地点除雍和宫外,或在中正殿、宝华殿、慈宁宫、阐福寺、弘仁寺、嵩祝寺、永安寺、延寿寺、恩佑寺、正觉寺、圆明园清净地、景山关德殿、北海真谛门等处。本书所译此类档案内,均附录需用物品清单,记录诵经需用各类物品,弥足珍贵。
本课系雍和宫内之成规诵经,由四扎仓喇嘛分诵。主要为每日早课和农历初一、十五日和初十及月末最后两日的诵经法会。每日早课乃寺内喇嘛之必修课,主要诵《皈依经》、《兜率天赞》、《绿度母经》、《白度母经》、《大白伞盖经》、《五大行愿品》、《心经》、《诸护法献供经》等。初一、十五日的诵经法会主要念诵《大威德金刚经》、《勇保护法经》、《地狱主经》等。初十日法会主要念诵《长寿经》等,月末法会念《大日如来经》、《荐亡经》等。
随营系喇嘛在军营中的经差,乃清代喇嘛随营制度。凡遇皇帝亲征、行围狩猎、阅兵安扎御营或出征安扎八旗行营,于安营前由随营扎萨克喇嘛率达喇嘛4名,在营地四周念《曼陀罗净坛咒》,安营时由喇嘛诵经净地面,安营完毕再诵经散祟,其后方开营驻兵。若皇帝驻跸,其随军之雍和宫堪布或察罕达尔汗呼图克图率达喇嘛在皇帝黄帷和寝帷内外念“散祟咒”毕,皇帝方与文武大臣一起入营。迄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此制度废止。
外课指应邀至宫外为私人诵经,因内城居住满蒙旗人、王公大臣较多,故此类外课需求较大。
雍和宫节庆佛事活动主要包括迎新年法会、祈愿法会、跳步扎、佛吉祥日法会、大威德金刚坛城法会、关公磨刀日法会及火供仪式、天降节、燃灯节、腊八舍粥等。这些活动目前雍和宫仍在举行。
4、金瓶掣签:乾隆末年,随清军入藏,廓尔喀事平定,乾隆帝即着手整顿、改革西藏僧俗各项事务,其中在大昭寺、雍和宫设置金奔巴瓶,掣签转世活佛之制,乃诸项改制之一,并将其缮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鉴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上谕军机大臣及在京呼图克图商议改革认定活佛转世之成规。旋于八月二十九日颁上谕,除在拉萨大昭寺设金奔巴瓶,签定藏区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外,“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钵巴瓶,如蒙古地方出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年月日姓名缮写签上,一体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陋习,永行禁止”,确定了金奔巴瓶掣签制度,并晓谕蒙藏地区一体遵行。自此,雍和宫作为签定活佛转世之场所,奠定了其在藏传佛教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发表了一些关于拉萨大昭寺金瓶掣签的研究成果,但尚未见研究蒙古地区活佛于雍和宫掣签确定呼毕勒罕的论著,或囿于此类文献,多为满文文献之故。《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内,收录了60件关于在雍和宫金瓶掣签的档案,其中主要是乾隆帝为在雍和宫推行金瓶掣签,彻查喀尔喀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舞弊事件的档案。乾隆五十七年降谕实行金瓶掣签确认呼毕勒罕定制后,五十八年二月,理藩院具奏访得喀尔喀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希擅自寻找灵童,赴藏向达赖喇嘛、拉穆吹忠求得咙单,指称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系呼毕勒罕之事,系未遵照新规,仍按旧例认定活佛转世之事件。此奏引起乾隆帝重视,立即谕令理藩院、驻藏办事大臣彻查此事。最后,重新按新规寻访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于雍和宫掣签认定,成为于雍和宫掣定之首位呼毕勒罕。乾隆帝对此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旨在加强清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借机规范了藏区活佛转世于大昭寺掣签、蒙古地区活佛转世于雍和宫掣签制度,防止僧俗势力结合,抑制蒙藏贵族夺取宗教权力,消弱达赖喇嘛、班禅等对蒙古地区活佛转世的控制,因而赛因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事件,在清代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除此事件的档案外,亦有一些关于在雍和宫签定蒙古地区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的档案,最晚为光绪末年者,皆为研究清代蒙古地区呼图克图转世的珍贵史料。
自赛因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事件后,陆续有青海塔尔寺、佑宁寺、拉茂德钦寺、广惠寺、东科尔寺,内蒙古锡勒图召、五当召、班第达召、小召、大乘转轮寺、巴音和硕庙,外蒙古扎雅寺、哈尔哈库伦,甘肃拉卜楞寺,辽宁阜新瑞迎寺,北京察汗喇嘛庙等寺的阿嘉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敏珠儿呼图克图、咱雅班智达呼图克图、锡哷图呼图克图、内托济音呼图克图、洞阔尔呼图克图、萨木察呼图克图等活佛之呼毕勒罕,多于雍和宫金瓶掣签确认。直至民国年间,雍和宫仍在举行金瓶掣签。
5、宣扬黄教: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建为“绀宇梵宫,轮奂长新”的皇家寺院,亦有对外宣扬清朝“阐扬黄教,安逸众生”之意。年班蒙古王公进京,均到雍和宫礼佛。若遇雍和宫之礼佛活动,皆请其参加。尤其每年末于雍和宫举行的跳步扎,蒙古王公皆以亲临为幸。甚至在乾隆朝前期,蒙古准噶尔汗国使臣屡次前来北京与清朝商谈划定边界、请求赴藏熬茶、协商双边贸易等事宜。其中乾隆十年(1745)二月,乾隆皇帝偕准噶尔使臣哈柳前往雍和宫观看布扎。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准噶尔使臣于雍和宫朝见并观看布扎。乾隆十三年(1747)四月,准噶尔使臣于雍和宫朝见并观看诵经。这些活动看似微不足道,其意义则非常深远,他不但向蒙古宾客宣扬了乾隆皇帝本人尊崇佛学,尊重蒙古和藏区风俗习惯的一贯立场,而且对虔诚信佛的蒙古准噶尔汗国之民众,通过他们自己的使臣之口径,客观地了解清朝的宗教与民族政策起了积极作用。雍和宫作为建筑宏伟、扎仓齐全、佛事频繁、活佛齐聚、喇嘛众多的名刹,诚可谓对外宣传清朝弘扬黄教之窗口,在蒙藏地区信众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吸引大量蒙藏地区的达官贵人和普通信众前来朝拜,加强了北京与蒙藏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对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以上几条外,有关雍和宫的建筑维修、香灯地亩购置与经营、内务府壮丁为皇室应差、各类官员考核拣放及伊犁、金川等地平定后,自雍和宫派活佛或高僧到彼处主持黄教寺院等类档案,对不同学者而言,抑或价值更高。惟望此书出版,能嘉惠学林,对研究清代藏传佛教史、民族史、宫廷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有所裨益。在翻译时,我们将佛经、佛尊、礼佛用品类的藏语、蒙古语词汇,交由雍和宫法师嘉木样·图布丹、嘉祥罗杰指正,两位高僧均做精准翻译,为本书增色颇多,在此对两位高僧之帮助深表谢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李德成研究员审校此稿,提出诸多修改意见,虽为老乡、同学,仍宜于此谨致谢忱。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档案内容庞杂,涉及清代民族、宗教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以我等之学识水平,难免有翻译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用户评价
这套书的阅读体验简直是一次心灵的探险。作者的叙事节奏拿捏得炉火纯青,时而如山涧清泉般娓娓道来,将那些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时而又如惊涛拍岸般,将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展现得波澜壮阔,令人心潮澎湃。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敏感或多方解读的历史事件时所采取的审慎态度和严谨的论证过程,避免了过度的主观臆断,力求呈现一个更接近真相的面貌。不同于市面上一些肤浅的历史普及读物,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即便是对历史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也能从中汲取到新的养分和不一样的视角。纸张的质感和排版的设计也为整体的阅读享受增添了不少分数,捧在手里就是一种享受。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承载的史实信息量,更在于它所传达出的那种对历史的敬畏与深沉的思考。作者没有将历史简单地脸谱化,而是致力于展现复杂的人性及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抉择与无奈。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书中描述的那些决策者们在面对巨大压力时内心的挣扎。文字的精准度极高,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使得整体的文风既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这种平衡拿捏得恰到好处,让历史不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可以与之对话的鲜活存在。对于任何对清代宫廷文化或社会结构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套书都是一份不容错过的饕餮盛宴。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种厚重的历史著作有些望而却步,担心内容过于晦涩难懂,会变成一场枯燥的“学术马拉松”。然而,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固有印象。作者仿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魔术师,他巧妙地将那些冷峻的史料转化成了富有生命力的故事。书中的某些章节,我已经反复阅读了好几遍,每一次都能品味出新的层次感。比如关于礼仪制度演变的那一段,作者用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了不同时期宫廷生活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与松动,这种洞察力实在令人赞叹。全书结构清晰,逻辑严密,即便是像我这样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也能轻松跟上作者的思路,并且被深深吸引。这绝对是近年来我阅读过的最有价值的历史类书籍之一。
评分我对于那些能够将繁杂的史料梳理得井井有条,并最终形成一套完整、自洽的分析体系的著作,总是抱持着极高的敬意。这套书无疑就是这样的典范。它的体量虽然可观,但阅读起来却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仿佛在不断解开层层叠叠的谜团。作者的考证工作做得极其细致扎实,每一个论点都有据可查,这为全书奠定了坚实的信誉基础。特别是对于一些涉及权力制衡和内部派系斗争的描述,处理得极其圆融且富有洞察力,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力和批判性思维。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已经超越了一般历史读物的范畴,它更像是一部深刻剖析了特定时代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度研究报告,阅读完毕后,我的知识储备和理解深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评分最近读完了一套非常引人入胜的历史读物,它让我对清代宫廷的运作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本书的文字功底扎实,作者对史料的驾驭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它不仅仅是在罗列史实,更像是在为我们搭建一个可触摸、可感知的历史场景。书中对于一些关键历史节点的分析鞭辟入里,特别是对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的挖掘,最终串联起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让人不得不拍案叫绝。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描述人物性格时的那种细腻入微,既不失客观,又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挣扎。读完后,感觉自己仿佛跟随书中的人物一同经历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装帧设计也相当考究,每一页都能感受到出版方的用心,阅读体验极佳,绝对是值得珍藏的佳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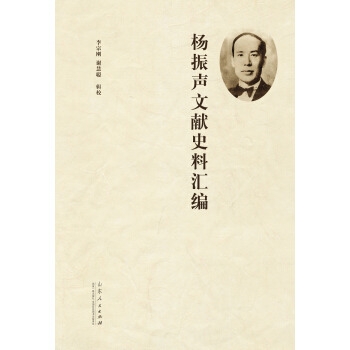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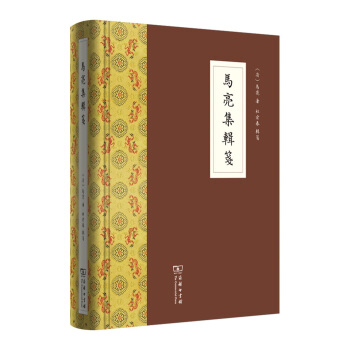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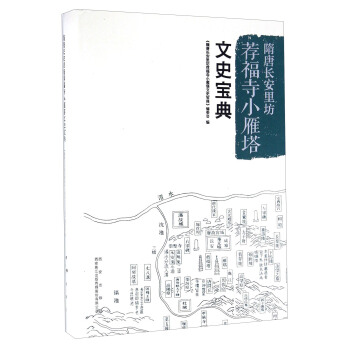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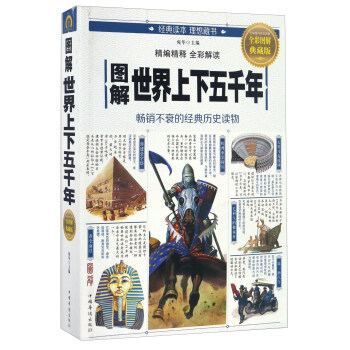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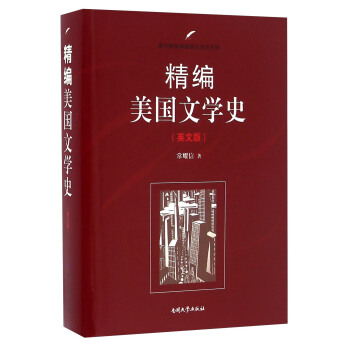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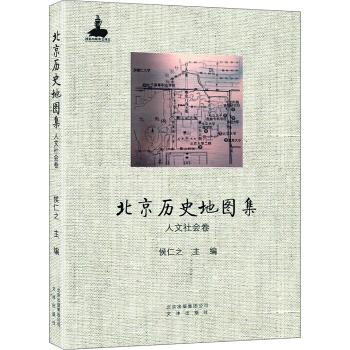

![丝绸之路1 丝绸之路历史沿革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28352/57cd4a2fNb7c36c5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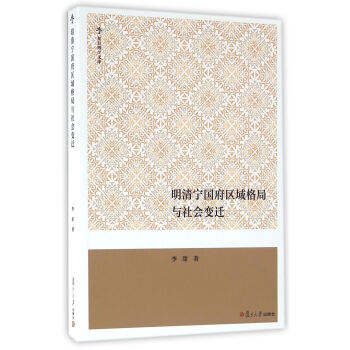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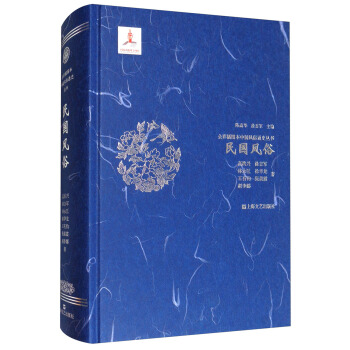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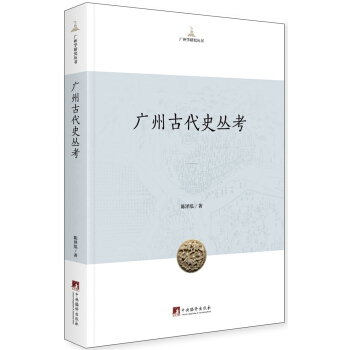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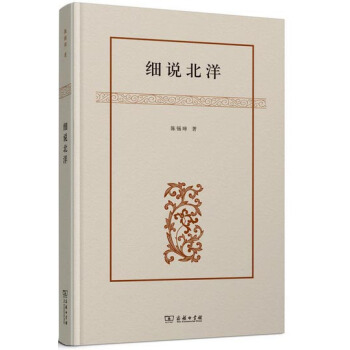
![亚历山大二世:最后的伟大沙皇(精装本) [ALEXANDR II:The Last Great Tsa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54415/58cf968bN0f3fa72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