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坊间已有不少西方政治思想史类著述,不过本书对政治思想史的叙述却并非亦步亦趋地跟随政治思想家的地理与历史脚步,而是以政制为主轴把希腊城邦时代以来至现代性国家建立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划分为——城邦与邦民、帝国与个人、共和与法制、俗权与信仰、城市与人文、权力与权利——凡六编十七章,其历史分期只是与西方历史时间大致吻合,思想史的时间与“客观的”历史时间本不完全同步。如此编排并不全是为了对历史悠长、人物繁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而是因为政制之为一种客观精神本就应该作为思想——至少是政治思想的一种潜在形式——来把握。以政制与政治理论之互释研读西方政治思想史,也不会再出现如此吊诡的思想史事件:对西方政治思想影响至深,且常常被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们浓墨重彩的斯巴达、共和罗马与中世纪城市,却无法在政治思想通史类著述中占据独立的篇章。
作者简介
张辰龙,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年、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博士后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目录
目 录
第一编 城邦与邦民——(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城邦政制及政治理论的创建
第一章 希腊城邦与雅典民主
第一节 希腊城邦
第二节 民主雅典
第三节 斯巴达政制
第二章 苏格拉底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端
第一节 苏格拉底之前
第二节 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
第三节 民主危机与苏格拉底的审判
第四节 苏格拉底的审判与雅典民主的检讨
第三章 哲人王与理念城邦:柏拉图对政制与正义的哲学建构
第一节 理念论:洞喻的哲学寓意
第二节 哲学王与城邦理念:洞喻的政治寓意
第三节 重回洞穴:三次叙拉古之行与哲人王实践
第四节 从哲人王到建邦者
第四章 政治的界定与政制类型:亚里士多德与政治理论的创立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辩驳
第二节 政制类型
第三节 优良政制:混合与良法之治
第四节 多样性、政治与政治理论
第二编 帝国与个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5世纪)希腊化时期的反政治思想及其在罗马帝国的流转
第五章 城邦的衰朽与世界性帝国的建立
第一节 城邦的衰朽与城邦的背离
第二节 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城邦与城邦联盟
第三节 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境况
第六章 从反政治到非政治:希腊化时期的各哲学流派
第一节 反政治抑或非政治的:希腊化时期政治思想的特质
第二节 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犬儒主义的流变
第三节 伊壁鸠鲁学派的美德功利与契约正义
第四节 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与世界主义
第三编 共和与法制——(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及其理论解读
第七章 罗马的政制与法制
第一节 城邦架构的帝国实体
第二节 共和政制
第三节 共和的律与法
第八章 混合与共和:波利比阿与西塞罗对罗马共和制的解读
第一节 波利比阿论混合制的优势
第二节 西塞罗对共和之界定
第四编 俗权与信仰——(公元1世纪至公元16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超越政治观
第九章 基督教与俗权的历史遭遇
第一节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
第二节 中世纪基督教教会与日耳曼诸王国
第三节 肉身的沉重与宗教改革
第十章 天国与尘世:基督教初期“政治无能论”
第一节 俗权的界限:《新约》中的政治思想
第二节 奥古斯丁界分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第十一章 教权与政权:神学辩证
第一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调和与综合
第二节 马丁?路德的单剑论
第五编 城市与人文——(12世纪至16世纪)中世纪城市及其政治人文主义
第十二章 自由城市与城市共和
第一节 自由城市
第二节 城市共和:佛罗伦萨与威尼斯
第十三章 政治人文主义:帕多瓦的马西略与马基雅维里
第一节 市民人文主义与共和主义
第二节 政教分离与人民立法者:帕多瓦的马西略
第三节 权力政治与共和政治:马基雅维里纠结于君主与共和之间
第六编 权力与权利——(16世纪至19世纪)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权力与权利的辩证
第十四章 现代性国家的形成
第一节 现代性国家形成过程中三种主要向力与三种理论旨趣
第二节 演化抑或创新?现代政制的构建之争
第十五章 绝对主义与主权的建构
第一节 布丹论主权及其限制
第二节 格老秀斯区分对内主权与对外主权
第三节 霍布斯的政治信约与绝对主权
第四节 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与伦理国家
第十六章 权力分立与有限政府
第一节 洛克的社会契约与有限政府
第二节 孟德斯鸠论权力分立与政治自由
第三节 复合共和制:詹姆斯?麦迪逊的大国保障自由方案
第十七章 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张力
第一节 哈林顿论共和与自由
第二节 卢梭的社会契约与人民主权
第三节 贡斯当论主权的限度与辨析两种自由
第四节 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忧思
第五节 密尔论自由、功利与代议
精彩书摘
第一编 城邦与邦民——(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城邦政制及政治理论的创建
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发轫于古希腊,与其城邦这一特殊政治体及这种政治共同体中政治生活紧密相关。
不过,城邦时代的古典文明并不是希腊这个区域最早的文明。之前发生在这个地区的文明被现代考古和史学界称作爱琴文明(Acgean civilization),又可细分为米诺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和迈锡尼文明(Mycenean civilization)。繁盛于克里特岛的米诺文明(鼎盛于公元前2200~公元前1450年)与同时代的近东政治制度相似,是一种中央集权式的宫廷政治。【注文:虽然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但在米诺文明的中心克诺索斯的考古发现,没有任何民众政府适合其遗迹,其复杂的宫殿结构只能表明它一个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中心。】其居民使用的语言并不属于印欧语系,其线型文字A至今无人识别,米诺斯文明几乎可以肯定是非希腊的。在希腊半岛形成的迈锡尼文明(鼎盛于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虽然是希腊人所创,但深受米诺斯文明影响,为后者所形塑,这些荷马称之为亚该亚人的希腊人同样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和再分配经济,与希腊古典时期的城邦文明存在根本性差异。
早期爱琴文明和后来的城邦文明之间存在着数个世纪的断裂。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文明彻底毁灭(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特洛伊战争或许是其最后的辉煌,如果《荷马史诗》记载的是史实),【注文:古希腊人,如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等,相信迈锡尼文明是另一支希腊人多利安人的入侵摧毁的。而现代考古和史学界则认为迈锡尼的毁灭有着其他众多的原因,因为迈锡尼文明的崩溃与赫梯帝国(the Hittite Empire)的瓦解,以及埃及新王国的衰落大约同时发生。】原来兴盛迈锡尼文明的土地上只留下一片废墟,人口锐减,其居民四处流散,其中一股跑到了塞浦路斯岛和阿卡迪亚(Arcadia),更多的人则途经雅典远走小亚细亚,形成古希腊人四支的最重要一支——爱奥尼亚人。被后世誉为希腊人《圣经》的《荷马史诗》就是最早流传于这个地区,乱世之后的文艺复兴也最早蕴生于此地。【注文:《荷马史诗》就产生于这个地区,其使用的语言主要是爱奥尼亚方言。最早的哲学也诞生于此地,如著名的米利都(Miletus)三哲(Thales, Anaximander, Anaximense)。】迈锡尼文明毁灭之后,是长达三四百年的“黑暗时期(公元前12世纪末至公元前8世纪前半叶)”【注文:对于“黑暗时代”的说法并不是没有反对意见,认为把这个时期定为“黑暗时代”过分强调了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城邦文明的特殊性与独创性,是“冷战”思维的结果;二是“黑暗时代”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么黑暗,虽然确实存在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等现象,但考古发现这段时间并不是没有发展。因此,有些人根据《荷马史诗》把这个时期命名为“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期间希腊人甚至丧失了书写能力。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段时间既无文字记录也很少有考古学上的物质遗存。由此造成的不仅是这种晚期青铜文明与后来的城邦文明时间上的隔断,同时也造成文化传承上的巨大断裂,后世希腊人对之前文明的社会组织、物质文化和书写系统等几乎没任何理性认知,留在记忆中的只是梦幻般的人神共存的传说。虽然迈锡尼人所使用线型文字B的某些政治词语流传到了城邦时期,【注文:线型文字B在20世纪50年代已为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解读,这种音节文字虽然是从线型文字A发展而来的,但其所记录的语言确实是一种古希腊语。只是到了古风时代希腊人借助腓尼基(Phonecia)字母再次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希腊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始于公元前776年,即有记载的第一次奥林匹亚赛会开始之年,而之前的历史只是史前史。】但语词所意涵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概念所指称的制度安排更是同名异指。【注文:到荷马时代,泥板上描述迈锡尼时代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头衔、级别、职能等词汇和涉及土地制度的词汇几乎全部被淘汰。由于制度被摧毁,残存的个别词汇也不再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如在线型文字B(Linear B)泥板中,Qasireu(Basileus)这个词语指的是村社一级的地方长官,到了荷马和赫西俄德那里却具有了王的意思,有时也表示“贵族”。但Basileus所意指的“王制”和泥板书上王制(Wanax)已大相径庭,改变的不仅仅是“王”的称谓,而是性质:Basileus在职权上受到诸多限制,再也不拥有迈锡尼时代的那种王权了,即使像阿伽门农这位“王中之王(anax)”每逢大事也得召开议事会听取他人的意见;又如demos,在泥板(词形为damo)中指的是村社,自荷马开始既指村社,又表示居住在村社中的人——“人民、民众”。词义的变化不仅是义项的简单增加,而是反映了制度安排的根本变迁:由原来被统治的单位成为邦民得以享有权力的主体。】
伴随迈锡尼文明毁灭的是中央集权制彻底消失在希腊历史的长河之中,从此再也不见踪影。公元前8世纪以降的希腊世界不是迈锡尼的产物,而是黑暗时代的结果,与迈锡尼文明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继承关系。城邦,这种迥异于之前和同时代其他政治实体的特殊构造,近乎“无中生有”地萌芽于“黑暗时代(Dark Age)”后期【注文:《荷马史诗》的故事情节虽然远袭迈锡尼世界,名义上的背景是迈锡尼末期,但线型文字B泥板所透露的迈锡尼社会与荷马描写的完全不同,倒是和“黑暗时代”后期的考古遗存大范围的重合。因而,普遍推测《史诗》实际反映的是作者自己的时代——荷马时代,一个与迈锡尼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存在着本质不同的时代,而《史诗》所描写的制度安排倒是和后世的城邦制度之间有着比较清晰的发展线索。】,发展于“古风时代(Archaic Period)”【注文:古风时代(大约公元前750年至前500年)意思是“守旧的时代”,这一称谓源于艺术史。】,在古典时代达到其鼎盛。古典希腊史其实也就是有关城邦的历史,因为正是城邦创造出了独特的希腊文明,是所谓“希腊奇迹”的基础。
前言/序言
前言:以政制为思想的政治思想史
政治思想史首先遇到是一个不言而喻又莫衷一是的问题,何谓“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s)”?尽管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政治思想史的写作还是以经典作家的经典著述为文本勾勒其主要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或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有的干脆就是思想家的思想传记,如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不过,大多数著述虽然是以经典作家的政治理论为主要内容,但也以相当的篇幅交代了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这也是汉语学界书写《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方式,只不过有的背景叙述过于宽泛,有的相对集中于政治理论之相关。对于这种主流写作方式,剑桥语境学派表示了不满,如斯金纳就认为应该集中探讨产生这些主要理论家之作品的社会和知识环境,政治思想史应该是意识形态史而不应全是经典著作史,应该是真正的政治思想史而非政治理论史或政治哲学史。通俗地说,经典著作家的理论过于抽象和高远,远超同时代的人,和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点“隔”,必须用当时的主流政治意见(如流行的小册子等)打通其与政治生活的关联,如此不仅能更全面地把握当时的政治思想,也能更好地理解经典文本,使这些经典理论对当时的政治行为更具解释力。这不是一般性的背景介绍,因为这种叙述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工作。【注文:因此,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著述接近于“政治观念史(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参见Bhikhu C. Parekh & Robert N. Berki,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A Critique of Q. Skinner�餾 Method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3(2):163-184.】可惜,到目前为止,语境学派只写出了一些断代史,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理文献本来就稀少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也有人进一步推论,政治思想应该是政治家或政治人物的相关思想,而不应是思想家们高深的政治理论。问题是,大部分政治人物并没有留下著述,而且政治人物的政治言行不说历史叙述本身是否可靠,除非进行过度的阐释,否则难以写成思想史。
于是,我们就发现一个相当吊诡的思想史事件:对西方政治思想影响至深,而且也常常被近现代政治思想家们浓墨重彩的斯巴达与共和罗马,【注文:关于斯巴达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影响可参见Elizabeth Rawson,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 Clarendon Press, 1969;关于共和罗马的影响可参见Fergus Millar, The Roman Republic in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2.】却很少在政治思想通史类著述中占据独立的篇幅。【注文:或许孤陋寡闻,我们只知道吉达尔(Raymond G. Gettell)在《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中给罗马留下了独立的篇章;萨拜因的经典教科书《政治学说史》貌似也给予了独立的章节,其实是归入了希腊化范式,而且把共和时期的西塞罗与帝制时期的罗马法学家并论在了一起,除了顺带提了一笔波里比阿和西庇阿集团外,对存在长达近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几乎没有什么介绍;与萨拜因类似的,还有声称重视思想与制度关系的邓宁(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的《政治理论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而波洛克(Sir Frederick Pollock)的《政治科学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s)》则干脆把西塞罗缀在希腊人后面;就是《剑桥希腊与罗马政治思想史》也是把希腊化、西塞罗和罗马帝制时期合在了一起,与古典希腊并列。晚近,科尔曼两卷本的《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在讲述西塞罗时简单介绍了罗马的共和政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著述倒是大多单列了“罗马政治思想”,如高一涵《欧洲政治思想史》、张翰书《西洋政治思想史》和孟云桥《西洋政治思想史》,甚至蒲薛凤在其《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中都为罗马留了一个独立的小篇幅。】对于斯巴达,大多只是在阐释柏拉图的“理想国”时简单地勾勒几笔,而罗马这一对政治理论更具影响的精神存在不是被并入希腊化时期就是与早期基督教,甚至中世纪合论,【注文:如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以及N. Jayapalan,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tlantic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2001.】更有甚者竟当共和罗马不曾存在,至少在篇章目录中根本不见踪影。【注文:且不论汉语学界,就是英语学界有关政治哲学史的著述也有根本不提共和罗马的,如《牛津政治哲学史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以及Subrata Mukherjee & Sushila Ramaswamy的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PHI Learning Pvt. Ltd, 2011),或许觉得共和罗马难以找到够得上哲人的作家。当然,大多数著述也论及西塞罗,甚至波里比阿。且不说他们的相关著述留给我们的只是残篇断简,就算是完好无缺,其对罗马共和政制之思想意涵的揭示,恐怕也难以企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等对希腊政制的理论阐释(这也是有些思想史著述不愿给他们独立篇幅的主要原因),更不匹配已成为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思想巨大资源库的罗马共和政制。】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自然是共和时期的罗马没有太多符合其标准的政治思想家,当然也没有多少经典性政治理论著述。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重要,但毕竟不是思想,而只能作为思想的背景,既然思想史的主题不存在或不重要,其背景即使再重要也只能轻描淡写了。就如邓宁,虽然坚持政治理论史要与政治史始终保持关联,也知道罗马的实际制度对后世思想界的影响比其政治理论要大得多。不过,因为其政治理论文献之微少而不足大论,虽然勉强用一定的篇幅叙述了罗马政制的演进以及西塞罗和波里比阿,但显然不能与希腊并论,甚至其整体都不能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单个思想家并肩,不得不合论共和罗马、帝制罗马和希腊化,尽管邓宁也曾说过“要从制度的直接阐释中抽取理论观念”【注文:W. A. Dunning,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Ancient and Medieval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p. xviii-xix, xxv, 106-107.】。
制度当然不直接就是思想,【注文:所谓康有为语“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现为汉语学界广泛引证,但搜索《康有为全集》十二卷未见此语,只在其《实理公法全书》之“凡例”中见到“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于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仅就此段论述而言,虽然义理(理论或思想)与制度紧密相关,但仍然是分立的,并非思想包含制度和义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但也无人否认制度是一种精神存在,即黑格尔所说的“客观精神”。而所谓客观精神则必定是人之思想(精神)的外化或客观化,【注文:这是所说的外化客观化并不是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三”——书写成文字进入纸张等等,而是指制度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作用的规则、习俗等之所以成为制度,是因为它们存在于你我他之间,而不仅是单独的你或我知道(主体性),即使你和我都不知道,但因为我们生活群体绝大多数都知道并遵守着,它们就客观地存在着,就是客观的,而且外在于我们单个的每一个人。当然,这只是最通俗的解释。】具体说就是统治阶层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化或客观化。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统治阶层政治思想之客观化的政治制度安排,【注文:之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制度所反映的并不完全纯粹是统治阶层的思想,必然有被统治阶层的意愿掺杂其中(无论多少),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一定是实际协议(虽然共和罗马的政治安排确实很多是来自这种实际的协议),大多可能统治阶层本身感受到来自被统治者的压力。所以,统治阶层的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可以反证被统治阶层的思想,因为被统治阶层往往留不下其思想的文字记录。当然,制度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复杂过程,有传统等诸多因素参与其中。】或许比所谓代表着统治阶层的思想家更能反映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黑格尔才指出,法并不是“冷冰冰的文字”,必须“把法作为思想来把握”,而法和伦理(国家、政府和国家制度)及其现实世界只有通过思想才能被领会,只有“通过思想才取得合理形式,即取得普遍性和规定性”【注文: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7、15页。稍微了解黑格尔的当然知道,黑格尔所说的“伦理”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伦理并不是一回事。其实,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精神哲学》而不是其《历史哲学》对于思想史研究应该很有启发。】。按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精神哲学,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本来就也应该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形式。比如,民主雅典留下了大量政治理论文献,但却没有一篇是正面表述当时民主意识形态或民主理论的【注文:唯一对民主的正面阐释,是柏拉图在其《普罗泰戈拉》中借智者普罗泰戈拉之口讲述的一个神话故事,即宙斯在所有邦民中间平等地分配“政治技能”——羞耻感(aidos)和正义感(dike)。】,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色诺芬和“老寡头”等都是反民主的,至少对当时雅典的激进民主都持批判态度。因此,我们了解当时民主意识形态或民主理论的最佳渠道就是当时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实践,如“抽签”“陶片放逐”以及民众法庭的审判等,这些制度及其运作本身才真正揭示了当时大多数雅典人对政治持有的观点。
其实,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日耳曼法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基尔克(Otto von Gierke,1841~1921年)在与理论上处于上风的罗马法学派交锋过程中,就竭力从德意志中世纪存在的各种合作团体的规章制度中挖掘其理论意涵,以团体人格说挑战了罗马法学派的法人拟制说,而其对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性团体之政治价值的揭示也深刻地影响了菲吉斯(Neville Figgis,1866~1919年)有关多元主义国家概念的论述。不难理解,梅特兰(F. W. Maitland)何以很有意味地把基尔克《德国合作团体法(The German law of Associations)》第三卷译之为《中世纪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s)》。实际上,目前研究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学者也大多采用这种经由各种制度来阐释政治思想的方式。不过,这与其说是出于理论的自觉,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中世纪世俗世界本来没有留下什么经典文本供其研读。
揭示政制本身的理论意涵,有时也会为我们带来经典作家没有传递给我们的理论收获。当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以共和罗马创建者之一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辨别共和与民主这两种理念时,其理论资源显然不是来自对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等经典著作的研读,而是源自他对斯巴达、迦太基、荷兰,尤其是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等在政治制度安排之不同的理论阐释。【注文: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14篇、第39篇和第63篇等。其实,《联邦党人文集》本身就是对制度进行理论解读的经典例证,只不过其方法别人学不来,因为三个作者之一的麦迪逊本身就是《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他当然知道自己在草拟这些宪法规条时自己的政治理念。】其实,稍微注意一下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在公民大会安排上的区别,也会发现雅典人和罗马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差异。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对联邦制的理论论证,也有不少得自希腊化时期亚该亚联盟在制度上给予的理论启示。【注文: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18篇等。】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政制本身作为政治思想的一种形式或者一种潜伏形式,那么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精神实体或思想史实——斯巴达与共和罗马,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出现完全遗漏这一吊诡现象,尽管古典时期的斯巴达人自己在政治理论上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
当然,作为一部政治思想史,我们不可能只揭示制度的理论意涵而抛弃经典作家的经典著述。一方面,制度虽然不是“冷冰冰的文字”,但毕竟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仍然需要一个将其“激活”的过程,否则它们就无法进入我们的“主观”,无法在思想上对其进行理解与把握。而经典作家们的政治理论为我们提供的各种观念或概念就是制度的“激活码”,就是我们观察和理解这些制度的眼睛,否则我们只能“看(look)”而无法“看到(see)”;另一方面,没有相关的制度知识,我们也难以真正理解经典作家的政治论述。举个简单例子,柏拉图为其第二好的城邦设计的人数是5040人,不能多也不能少。在其著述中,我们只知道这个数字来自他那神奇的政治算术,但作为在现代国家生活的我们却很难理解这么点人口如何构成一个“国家”。如果了解一些希腊城邦世界的基本情况,那么自然就知道这个神奇的数字只不过是希腊城邦世界的城邦大小的正常尺度,即多数城邦人口的一个大致平均数而已。当然,要想真正理解这个数字的政治价值,还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大多数希腊人对城邦所持有的各种观念。所以,黑格尔才认为,即使柏拉图的“空虚理想”“本质上也无非是对希腊伦理的本性的解释”【注文: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页。】。其实,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为其对现实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关键是如何解读。大众化的二流小册子貌似贴近生活,或许正因为其太过贴近反而影响我们的视野。因此,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政制与政治理论的互释过程。
不过,我们对西政治思想史的叙述却是以政制为主轴而非亦步亦趋地跟随政治思想家的脚步,因为如此安排不仅不会再为把共和罗马安置在何处而困扰,而且也会减少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历史分期的苦恼。【注文:除非像施特劳斯那样把政治思想家按历史时间进行简单的排列,历史分期在历史撰述中必不可少,以便于我们记忆、理解、把握漫长的过去(虽然人为地切割了原本连绵不断的时间之流)。不过,由于思想史的时间与“客观的”历史时间并不同步,用黑格尔的话说“思想总是落后于时代”,而且思想的发展也并非流线式而是发散性的,再加上每个撰述者自己主观性,可以说坊间流行的几部《西方政治思想史》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分期。除萨拜因和麦克里兰等少数几部外,大多数《西方政治思想史》分期过于琐碎而不利于读者把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脉络。】按照这一理路,并基本遵守历史时间,我们把西方政治思想史安排在六个主题之下:
一、城邦与邦民
叙述从公元前8世纪城邦出现之后至公元前4世纪古典时代结束期间古希腊城邦政制,以及西方政治理论的初创。我们会用较大的篇幅阐释希腊人城邦理念、雅典民主、斯巴达政制以及为何把polite译为“邦民”而不是通常的“公民”。
二、帝国与个人
与以往的成见相反,我们并不认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是与政治无关而只关涉个人幸福的伦理思想。希腊化时期各哲学流派的政治旨趣与其说是对帝国政治的应对,不如说表现出的首先是对城邦衰败的反映——反城邦或反政治倾向,其内含的与政治无关的“非政治”理论旨趣只是到了城邦彻底崩坏与帝国秩序稳定确立之后才开始凸显,并流转于罗马帝国。
三、共和与法制
在我们的思想史叙事中,共和罗马自然要独立成编。共和罗马这一城邦架构下的帝国实体,让后世政法思想家们殚精竭虑的正是其复杂的政制安排与精细的法律规则,远非波利比阿的混合制所能涵盖。与罗马法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不同,至少共和罗马的公法体系之发达远超其私法,我们力图用“治权(imperium)”这一罗马人特有的政治观念贯穿关于其政制与法制的阐述。
四、俗权与信仰
对基督教的神学政治观的讲述,我们不再人为地裁断成三截——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和近代宗教改革,而是从其诞生一直延续到马丁?路德宣判上帝的身体(教会)之死,因为期间基督教的政治观无论如何变化,但在政治之于信仰的无能上却一脉相承。
五、城市与人文
与共和罗马的遭遇类似,有关中世纪城市这一封建制度和教会体制之外出现的异体,人们不是归入中世纪晚期就是近代早期,几乎无人使其独立成篇。然而,我们如果从12世纪自由城市的出现算起到16世纪以后绝对主义国家的产生,这种独特政治体的存续时间无论如何都不算短命,而所谓“过渡性”只不过是现代人的“后见之明”。尽管它们与身旁的封建和宗教势力纠缠不休,但对其异质性无论是城市自身还是封建主与教会却有着相当的认同。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些城市人根本不知道“国家(state)”为何物,而正是国家的出场才终结了自由城市的存在。
六、权力与权利
我们并没有像前几编那样,详述现代性国家建立过程中各国政制及其变迁,而是化繁为简,把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建构过程的各种力量总结为三个主要方向。如此粗简地概括肯定有不小的问题,但如何在简短的篇幅内厘清西方各主要国家在现代性国家建构过程中各自发展不一的政制特性,的确是一个不小的理论挑战。当然,更关键的是,经由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的张扬,近代现代的政治思想家们大多在一定意义上都成了实际上或理论上的立法家或建国者了,他们比以往的政治思想家们表现出了更多的“能动性”或“主动性”,传统以及现存体制不再仅仅是他们的思想源泉,更是他们建构自己新政制的材料。期间,他们在政治理论上的中心论题就是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国王的权力与权利、国家的主权、地方性权力、权力的制约与限制以及人民主权、团体的权利、个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与个人自由之权利保障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叙述脉络虽然早于成型,但所谓“以政制为思想”阐释方式却是交稿前的匆忙总结,虽然并非全是为自己如此安排寻找借口,但作为方法却也没有完全一以贯之,尤其某些政制的理论意涵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此稿为客串之作,西方政治思想史只是我授课的职业,既非我原来的学业也非我的研究本业。其中一部分是授课内容,但大部分是备课时的边角料。虽然其框架形成已有十来年,但内容每年备课时都略有补充,因交稿时间紧迫与家事繁多,也未能来得及详细整理,因此语言风格的不一致和叙述的不系统在所难免。
用户评价
这部作品给予我的震撼,在于它对于“思想”本身的高度自觉。我原本以为,政治思想史就是梳理“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然后分析其影响。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断被重塑、被误读、被批判,而又在新的语境下焕发生机的过程。作者在探讨某个思想家的理论时,常常会拉出长长的历史链条,追溯其思想的源头,又展望其可能的未来走向。比如,在分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时,他并没有停留在“权力至上”的简单解读,而是深入探讨了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意大利城邦政治现实,以及他为何会提出那样一套“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更重要的是,作者展现了后世如何解读和运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从君权神授的衰落到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思想的“生命史”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我最感到惊艳的是,作者在处理“自由”这个概念时,展现了其在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那里的丰富内涵。从古典自由到现代自由,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每一次概念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的重新思考。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政治思想并非凝固不变的教条,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对话,一场关于如何组织社会、如何实现人类福祉的持续探索。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它打破了我对“政治”的刻板印象,让我看到政治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它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联系。我本来以为政治思想就是关于政府、法律、权力这些“硬核”的东西,但读了这本书,我才发现,它关乎人性、关乎伦理、关乎历史的走向,甚至关乎我们对“好生活”的想象。作者在介绍中世纪经院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时,那种将神学、哲学与政治理念巧妙结合的分析,让我看到了思想的交叉与融合。而当他谈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以及它如何挑战传统的政治秩序,重新确立人的价值时,我感受到了思想解放的力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不同思想家对“正义”的理解时,展现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多样性。从柏拉图的“各司其职”到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再到罗尔斯的“公平原则”,每一次对正义的重新定义,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和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本书让我觉得,理解政治思想,就是理解人类社会不断探索自身如何更好地组织、如何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生活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更是一本关于我们自己、关于我们所处世界的书。
评分这本书我断断续续读了好几个月,真是一场思想的盛宴。一开始我被书名吸引,以为会是一本梳理西方政治思想演进的教科书,但读下去才发现,它远不止于此。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等等的名字和他们的理论,而是极其细腻地勾勒出了这些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碰撞、融合、演变,甚至是被曲解和重塑的。读到斯宾诺莎关于国家与自由的论述时,我仿佛能看到当时荷兰共和国的社会氛围,那种对理性与宽容的追求;而当读到休谟对经验与怀疑主义的探讨时,又忍不住思考,我们当下许多政治决策的依据是否真的牢不可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思想史中的争议和矛盾,他很坦诚地展示了不同思想家之间的激烈辩论,以及这些辩论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实践。比如,关于自然状态的设想,从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到洛克的“自然权利”,再到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每一次重塑都带来了对人性、社会契约和政府合法性的全新理解。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政治思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具体的历史土壤,回应着当时的社会挑战与哲学关切。每一次翻开,都像是在与跨越千年的智者对话,他们的问题,我们今日依然在追问。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可以说是相当颠覆。我本来以为会是那种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的学术著作,看完会积累一堆概念和人名,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作者的叙事方式非常独特,他更像是一位引人入胜的导游,带着读者穿梭于不同的思想“遗迹”之间。他不是简单地告诉你“孔子说了什么”,而是会让你理解为什么孔子会在那个时代提出那些关于礼乐、仁政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如何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格局。而且,书中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穿插讲述,也让那些抽象的政治哲学变得生动起来。比如,在谈论启蒙思想时,作者会巧妙地引入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状况,让你明白,那些关于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的口号,是如何在民众心中生根发芽,最终引爆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我尤其喜欢作者在分析不同思想家的论证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辩证的眼光,他不会轻易地褒贬,而是会深入到思想的逻辑脉络中,让你自己去体会其中的精妙与局限。读完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连接,我才真正理解了“绝对命令”为何不仅仅是关于个人道德,更是对政治秩序构建的深层启示。这本书让我觉得,理解政治思想,就如同在解读一张错综复杂但又充满魅力的古代地图,每一个符号、每一条线索,都指向着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
评分坦白说,刚开始拿起这本书时,我带着一种“学习任务”的心态,想着把它当做一本工具书来查阅。但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完全被吸引住了,常常会因为某个观点而停下来,反复咀嚼,甚至引发一连串的思考。作者在讲解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时,那种对细节的把握,让我仿佛置身于雅典的广场,听着苏格拉底与人辩论,感受着公民大会的氛围。他没有用干巴巴的理论去描述,而是通过生动的细节,让你体会到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它不仅仅是统治,更是生活本身。我特别喜欢他对一些“非主流”政治思想家的关注,比如那些被历史洪流冲刷得不太显眼的思想火花。在谈到中世纪的政治思想时,作者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教会与世俗权力之间的斗争,而是挖掘了一些关于公法、契约的早期萌芽,这些都让我对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读到现代政治思想部分,作者对于民主理论的探讨,从早期代表制到直接民主,再到对民粹主义的警惕,让我看到了民主形态的演变以及它所面临的永恒挑战。这本书让我明白,政治思想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过去的伟大思想家,更在于理解那些思想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以及我们未来可能面对的可能性。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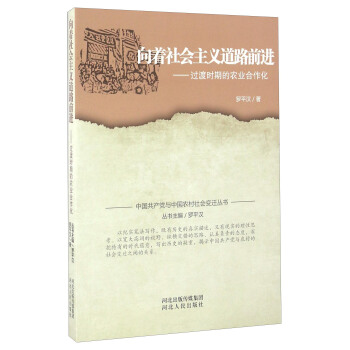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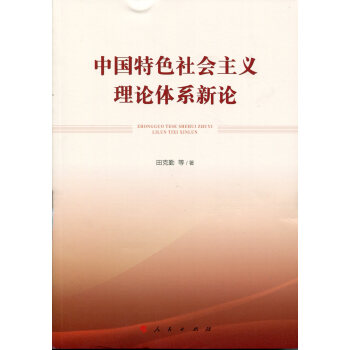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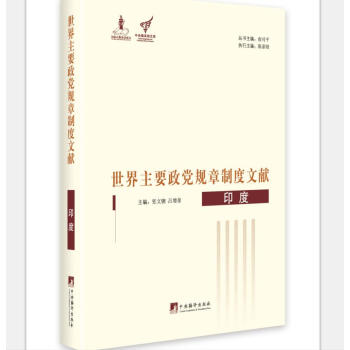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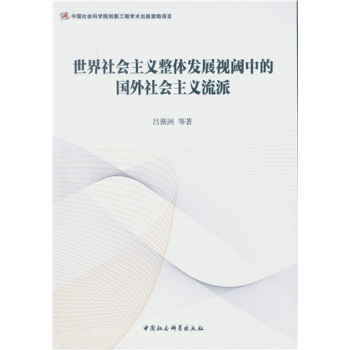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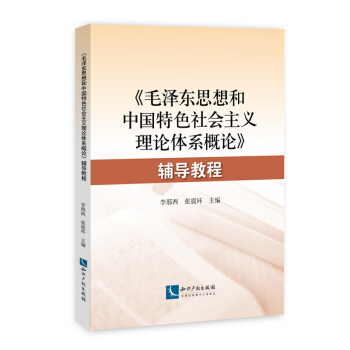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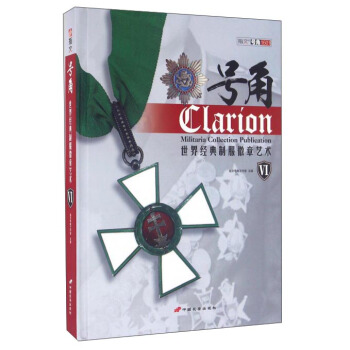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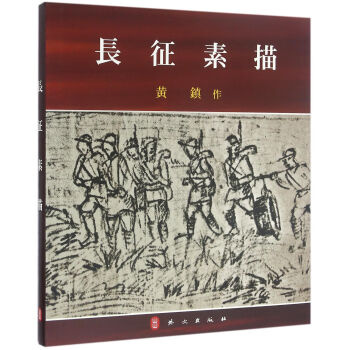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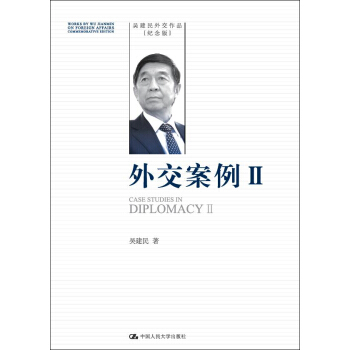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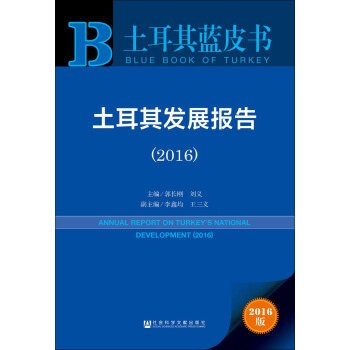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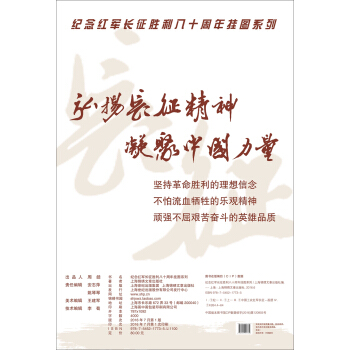
![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二辑) [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96977/58186e55N1c89b963.jpg)
![移民论/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二辑)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Futu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96979/58186e55Nfc2b6e4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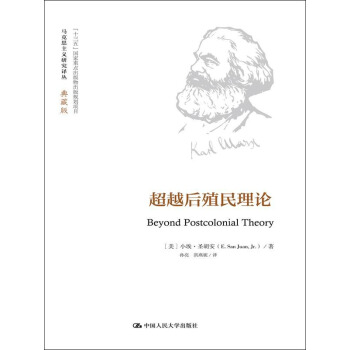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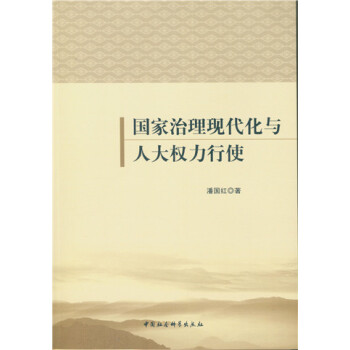


![联合国维和词汇手册/武警学院维和警察培训教材 [United Nation Peacekeeping Vocabulary Handbook]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11739/584fbd62Nea7f8d0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