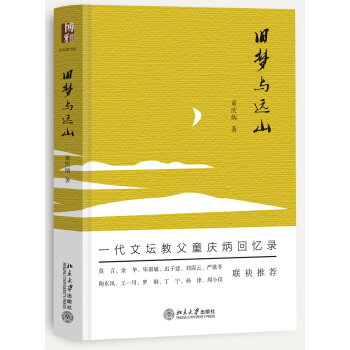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一代文坛教父童庆炳先生回忆录。
莫言、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震云、严歌苓、陶东风、王一川、罗钢、丁宁、孙津、周小仪等知名作家、学者联袂推荐。
关于饥馑的童年,求学游历之路以及数十年教育生涯中的历历往事。
文字朴拙,洗尽铅华,温暖动人。
十余幅珍贵照片首次公布。
海报:
内容简介
一代文坛教父童庆炳先生回忆录。
莫言、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震云、严歌苓、 陶东风、王一川、罗钢、丁宁、孙津、周小仪等知名作家、学者联袂推荐。
《旧梦与远山》是童庆炳先生一部随笔选集,十余幅珍贵照片首次公布,深情记录他对童年、故土和情亲历历往事的缅怀,以及青年时代外出求学游历、教书育人的诸多回忆,文字朴拙洗尽铅华,温暖动人,十分珍贵。
作者简介
童庆炳(1936.12.27—2015.6.14),福建连城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全国模范教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编委,《文艺理论研究》编委。曾任韩国高丽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大学等20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
专著:《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文学审美特征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童庆炳谈文心雕龙》《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等二十余部;
合著:《中国古代诗学的心理学透视》《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马克思与现代美学》《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价值观的演变》等多部;
编著:《文学理论教程》《文艺心理学教程》《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等二十余部;
另创作有长篇小说《生活之帆》(与曾恬合著)、《淡紫色的霞光》、随笔集《苦日子 甜日子》、学术随笔《风雨相随——在文学山川间跋涉》等多部。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那时我经常逃课,逃童老师的课亦多。十几年的光阴转眼过去,回头一想,遗憾良多,逃童老师的课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遗憾。童老师在课堂下是蔼然长者,端重慈祥;在课堂上却是青春生动,神采飞扬。他讲课时的样子经常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莫言
虽然现在我回忆不起童庆炳老师每节课所讲的具体内容,但我想课上所受的启迪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注入了我们这些学生的作品之中。就像一个人成长必须摄取多种营养,你既吃山珍海味,也吃五谷杂粮、瓜果梨桃。童老师的课,对我们而言就是这其中的一种。缺了它你不至于失衡,但汲取了它的营养你会变得更为丰富。
——迟子建
记得毕业后有一次去看望童庆炳老师,坐在他北师大的家里,当时师母健在,高高兴兴地沏茶端水果,师母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童老师总是微笑的样子,师母说话声音高低起伏,童老师说话声音从来都是平静的。
——余华
听他的课,在汲取知识的同时,常泛起情不自禁的感动。他把枯燥的文艺理论讲得流光溢彩,闪烁着温润高贵的人性光芒。他以深刻的学养为经纬,在严谨的学术框架中,将各种生动的例子随手拈来,如同精致的小品,点缀在精工细作的博古架上,浑然一体,处处生辉。
——毕淑敏
目录
1 远 山
4 饥饿的味道
13 祖母、小溪和山路
18 柴路弯弯
24 母 亲
40 祖母的手
44 月 季
49 故乡的水
52 父亲的字据
56 雉 鸡
61 消失的樟树
65 少年柴夫
68 摊藤草
70 故乡的沦陷
83 回忆母校连城一中
87 在龙岩师范的日子
95 第一笔稿费
100 高考1955
103 恰同学少年
114 五十年代的人情
119 我当厂长的三个月
125 四合院
132 苦日子,甜日子
139 那天,我就是中国
145 妮 基
155 在地拉那“偷书”
160 四谒列宁墓
167 韩国人的精神
173 深夜风铃
177 众声喧哗的书斋
181 潮白河放龟
186 上课的感觉
192 一部教材与四个编辑
196 北师大图书馆
200 五十年后的重逢
208 教师的生命投入
213 人生七十
222 哭曾恬
232 黄药眠先生的最后一课
237 回忆启功先生
243 季羡林先生
247 追忆郭预衡先生
251 王蒙印象
259 毕淑敏,一只勤劳的蜜蜂
264 赖丹留给我的“文学诱惑”
268 钟敬文教授的手杖
273 编后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
精彩书摘
母 亲
母亲去世好几年了。但在我的笔下,关于她还是一片空白。几次想动笔写点什么,觉得往事茫渺,一直没有找到叙述的“切入点”,就这样拖了下来。上星期被拉去给本科新生作题为“如何过好大学生活”的报告,讲话一开始就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大学生活,很自然地就想起母亲送我上北京时那不可遏制的送别眼泪,那每年给我做的两双布鞋,一种甜蜜而又酸楚的别样的感觉在心中涌动,眼前变幻着母亲青年时壮年时老年时的面容,想象她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纳布鞋底时用力拉苎麻绳的情景,于是关于母亲的种种记忆如同屏幕上的影像那样在眼前跳动起来……
两个女人加半个男人
客家的一个传统就是妇女特别勤劳。在一些描述南方客家风俗的作品中,往往把男人写成懒汉,他们成天待在家里看孩子什么的,妇女则下地干活儿,十分辛劳,似乎“内外颠倒”了。这种描写完全是漫画化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我的家乡在福建西部一个不算小的村庄里。小时候我们头上戴的斗笠每每写着“雁门童氏”四个字,我当时不解其意。长大后读了家谱,才知道我们的三十四代以前的老祖宗是从山西雁门迁移来的,因为是“客家”,为了不忘老本,父亲总是在一些器物上写上“雁门童氏”。客家人无论男女都很勤劳。男人同样下地干活儿,而且一些关键的技术活儿,如赶牛犁地、莳田、插秧、脱粒等,还是以男子为主。只是那种“男耕女织”的传统分工不甚明显。当然客家妇女什么都能干,确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不过在我们家情形有些特殊。我父亲身为农民却不安心务农。他读过两年私塾,识字,写得一笔好字,村子里过年时候各家门前贴的对联,有不少出自他的手;他还会用毛笔画竹子和蝴蝶,虽然所画的范式就那几种,可倒也栩栩如生。于是就有一些亲朋好友来求他的字或画,可能就因为这点“优越感”,觉得只是种地太没出息,就尝试着做点生意。在我的记忆中,他贩卖过布匹和木柴,还从政府那里贷过款,进深山建造纸厂,用手工生产毛边纸,可能还折腾过别的什么,不过结果都一样:失败。这样一来,家庭的担子就完全落在两个女人加“半个”男人身上,两个女人是祖母和母亲,“半个”男人就是半大不小的我。
从我懂事时候起,祖母已经年迈,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田地里的活儿则差不多要靠正当壮年的母亲了。母亲一天的生活是很紧张的。在我们家,天还没大亮,母亲就起来挑水做饭。我们起床后舀水洗脸,发现两个硕大的水缸已盛满清凉透亮的水。她总是把一天的米饭都蒸在一个大的饭桶里,饭桶的盖儿一揭开,冲出一股白气,白气慢慢散去,才露出上面蒸的豆酱、酸菜什么的,下面才是带着扑鼻的清香的白米饭或红米饭。全家数口一天三餐的饭食都在这里面了。
母亲在田地里干活儿时永远用一个背带背着我的还要吃奶的弟弟或妹妹。一边耘着田,拔着草,一边哼着歌,哄着背上的孩子。有时候也把年少的我带到田地里去,听她的调遣,或拔兔草,或放水,或在田头哄弟弟或妹妹。我最愿意跟她到菜地去。因为菜地通常总是间种黄瓜和甘蔗,母亲会摘一条黄瓜给我,她用她粗糙的手擦一擦,说,吃去吧!或者折一根还不太熟的甘蔗给我,说,咬去吧!这可是我童年时期的一种特殊“享受”,也是母亲赐给我不多的爱中令我感到甘甜的部分,所以至今回忆起来,就会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甜蜜感涌上心头,能让我幸福地发半天愣。
母亲在我们家乡绝对是一位口头“文学家”,她虽然不识字,但总是能够把各种乡间琐闻通过她那抑扬顿挫的嗓音和巧妙的叙述变成有趣的笑谈。无论是在田间还是在路上她的伙伴总是喜欢拉着她听她讲点什么。这样一来,就总是耽误一些田间的劳作,往往天快黑了,家家屋顶上都冒出了袅袅的炊烟,她还得在田里赶活儿。这时候祖母就会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向着小溪对面的田野拉长声高声地喊起来:“新人!转来吧!新人!转来吧!”这喊声总要重复多遍。“新人”是我祖母对我母亲的称呼。因为我们家乡的“新娘”叫“新人”,在母亲过门后祖母第一次如此叫她,从此也就不再改了,那原因一方面是她们婆媳关系好,一方面是我母亲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名字,在户口本上她的名字叫“沈老妹”(“老妹”是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位“妹妹”的意思,只有几个舅舅以“老妹”称呼她)。“转来”是我们家乡话,意思是“回来!”祖母的喊声中隐含些微焦急,但更多的是关切、抚慰、担心、爱护!因此那喊声就像出色的女高音那样亲切、动人而又绵长,甚至刚从田间劳作回来的乡亲,都会驻足仰头微笑着欣赏我祖母的喊叫,并开玩笑说:“好听!好听!像唱歌一样。”更调皮的一些后生,就会模仿祖母的喊声也帮着喊起来:“新人!转来!新人!转来!哈哈哈哈!”这时候,村前村后就会此起彼伏地响起这喊声,像多声部合唱。这可以说是我们家门口天天的“一道风景线”,那韵味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
家里穷,婆媳俩就把我们家宽阔的祠堂变成临时的客店,在逢集时搭几铺位,让四乡那些来不及赶回家的客人暂住一晚,收一些住宿费。更经常的是婆媳俩做米面的包子,让我在中午放学回家时端到集市上去卖。她们知道我不好意思干这个活儿,就想出一些办法给我做“思想工作”:“咱也不是偷,不是抢,靠的是劳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不就是这样的劝告:“你父亲不像一个男人,不理家,你可不能跟他学,你还小,当不了一个男人,也得当半个吧!”当然,我乖乖地当了“半个男人”。
后来我外出读书,对她们俩来说,可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你想想,连支撑家庭的“半个男人”也跑了。
送 别
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十九岁的我,要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事先完全没有准备。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北京不但在她的想象中而且在我的想象中简直就像天边一样遥远。
1955年,福建还不通火车。从我们家乡的连城县出发,要坐五天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有火车的江西省的鹰潭。山高路险,行程艰难。“宁化青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毛泽东的诗句所描写的路,正是我上北京必经之途。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上一趟北京,比我们现在去一趟西欧、北美还要遥远得多。记得我在龙岩读中等师范时,有一位老师长途跋涉去北京开了一次会,就像出了一次国似的,回来后在全校作了一个报告,专门讲在北京的见闻。至今我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讲冬天北京街道两旁的树干,都涂了像人一样高的白灰,远远望去,像站着一排排整齐的穿着白衣的护士。
我上北京读书的消息,经乡亲们的渲染,变得“十分重大”,使我们家的“两个女人”更是手足失措,心绪不宁,不知为我准备什么好,更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盘桓在她们心间折磨她们,可理智上又觉得儿孙“进京”读书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是不能轻易哭的。离别的痛苦只能忍着。所以我离开家时,祖母始终是平静的,起码表面上是如此。
我上路那天,母亲要送我到离我们村子十五里的朋口镇去搭汽车。她着意打扮了一番,穿一身新的士林蓝布衫,脸上也搽了白粉,嘴唇也好像用红纸染过,脑后的圆圆的头发结上还一左一右插了两朵鲜红的花,让人觉得喜气洋洋。那十五里路如何走过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已很模糊了。唯有在汽车开动前母亲的“空前绝后”的哭和流不完止不住的眼泪至今仍历历如在目前。她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语无伦次地说着:北京“寒人”(冷),要多着衫。实在有困难要写信给家里讲,我会给你寄布鞋。我知道你惦记祖母,不要惦记,有我呢。也不要惦记弟弟妹妹,有我呢。读书是好事,要发奋,光宗耀祖。毕业时写信来,让你爸写“捷报”,在祖宗祠堂贴红榜,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说着说着,她突然流下了泪,而且那泪像家门口的小溪那样滔滔汩汩,堵不住,擦不完,完全“失控”,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她的哭就如同蓄积已久的感情的闸门被启开,非一泻到底不可了……后来她不再擦她的眼泪,任其在脸上自然流淌,她一边哭着一边嘴里还唠叨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我觉得自己无能,在这个时候竟说不出一句恰当的、有力量的话来劝慰母亲,只是傻傻地待着,还轻声说:“妈,你别哭了!人家看咱们呢!”谢天谢地,汽车终于开动了,她似乎意识到离别终成事实,举起了手,我从车窗探出头,看见她的泪脸,这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她不由自主地向前跑了几步,但汽车快了起来,她向后退去,在第一个拐弯处,她的脸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了,但我仍清楚地看见她头上的那两朵红花在晨风中轻轻抖动……
布 鞋
我从小穿的就是母亲做的布鞋。但每年一双也足够了。因为南方天气热,我们那里的习惯,早晨一起床,穿的是木屐。早饭后一出门,或干活儿,或赶路,或上学,都是赤脚的。要是上山砍柴则穿草鞋。只有在冬天或生病的时候才穿布鞋,而且是光着脚穿的。只有地主老爷或乡绅什么的才穿着长长的白袜子加布鞋。可以说我们那时的客家人差不多都是赤着脚念完小学和中学的。母亲为我每年做一双布鞋,在中学读书时,是绰绰有余的,是不会穿烂的。
1955年来北京上大学,母亲给我做了两双布鞋,我以为这足够我一年穿的了。哪里想到来北京在校门口看到的一幕是:农民穿着袜子和布鞋在地里耕地。我们几个从福建来的学生为此大惊小怪,觉得这在我们家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那里都是水田,一脚下去就没膝深,你穿着鞋袜如何下田?当然大学同学们平时进出都一律穿布鞋或胶鞋,个别有钱的穿皮鞋。开始我只是觉得不习惯,觉得穿着鞋脚上束得慌,不如赤脚自在随便舒服。起初半个月,只好“入乡随俗”,勉强穿布鞋去上课、上街等。过了些日子,我们三个福建来的同学基于共同的感受,就议论着要“革命”,要把北京人这“坏习惯”改一改。我们约好在同一天在校园里当“赤脚仙子”。哦,赤脚走在水泥地上,巴嗒,巴嗒,凉凉的,硬硬的,平平的,自由自在,那种舒坦的感觉,简直美极了。虽然我们三人的举动引来学校师生的异样眼光和窃窃私语,但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城里人的“偏见”罢了,他们看看也就习惯了,况且“学生守则”里并没有一条规定:学校里不许赤脚。就这样我们大概“自由”了半个月。有一次,校党委书记给全校师生做报告,在谈到学校当前不良风气时,突然不点名地批评了最近校园里有少数学生打“赤脚”的问题。党委书记严厉地说:堂堂大学,竟然有学生赤着脚在校园里大摇大摆,像什么样子,太不文明了吧。我们第一次听说赤脚“不文明”的理论。我们“赤脚”的自由生活方式不堪一击,一下子就被“剥夺”了。
于是母亲做的布鞋成为我生活的必需。似乎母亲是有预见性的,要不她为什么要往我的行李里塞两双布鞋呢?可布鞋毕竟是布做的,并不结实。当北京的杨树掉叶子的时候,第一双布鞋穿底了。等到冬天的第一场初雪降落大地让我这个南方人对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欢呼雀跃的时候,我发现第二双布鞋也穿底了。我那时每月只有三元人民币的助学金,只够买笔记本、墨水和牙膏什么的,根本没有钱买对当时的我来说昂贵的鞋。我天天想着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她会给我寄布鞋来。又害怕地想:她不会忘记吧?如果她记得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呢?什么时候可以寄来呢?从家乡寄出路上要经过多少日子才能到北京呢?路上不会给我弄丢吧?在等待母亲的布鞋的日子里,我能做的事是,将破报纸叠起来,垫到布鞋的前后底两个不断扩大的洞上维持着。可纸比起布的结实来又差了许多,所以每天我都要避开同学的眼光,偷偷地往布鞋里垫一回报纸。而且每天都在“检讨”自己:某次打篮球是可以赤脚的,某次长跑也是可以赤脚的,为什么自己当时就没有想到布鞋也要节省着穿呢?弄到今天如此狼狈不堪,这不是自作自受吗?北京的冬天刚刚开始,我就嫌它太漫长了……
我一生有过许多的等待,大学学习期间等待母亲的布鞋是最难熬的等待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母亲做布鞋的全部复杂的“工艺流程”,可在那些日子连做梦也是母亲和祖母在灯下纳鞋底的情景了。那时我想起来了,母亲为全家所做的布鞋,除鞋面用的黑布是从商店里买来的之外,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由她和祖母用最原始的办法“搜集”的,连纳鞋底的细苎绳的原料也是自家种的,这在我们村子里,可能是“只此一家”了。
苎,或者叫苎麻,对许多读者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却倍感亲切。因为母亲和祖母在自己的家门口的一块很大的青石块上,垫起了厚厚的土,在那上面种了苎麻。苎麻是一种多年生的植物,叶子又圆又绿,每片都有巴掌那么大,茎灰白色,仅手指粗细,可长得有一人高。每当苎麻成熟要收割的那天,家里就像过节一样,十分热闹。先是摘那些嫩绿的苎叶,将它碾碎了和米面掺揉在一起,既可以直接作面饼,也可以作有馅的包子皮,所以割苎麻意味着家里要改善一次伙食。那苎叶做的面饼或包子,吃起来有一股特殊的清香,这在别家是享用不到的。所以苎麻叶饼蒸熟以后,母亲就遣我们兄弟姐妹东家送,西家送,让亲朋们也尝个新鲜。苎麻的皮从苎茎上剥下来,要花不少工夫,这都是母亲和祖母的活儿。而已经剥干净的苎麻杆儿,白白的,圆圆的,松松的,直直的,再加上一些竹签,就成为我们兄弟姐妹手中的玩具了。我们自由地把它截成长短不同的“小木段”,可以搭成小屋,可以做成鸟笼,还可以做成一切你想象得出来的东西,整整数天我们都可以沉浸在由苎麻杆儿构成的游戏里。母亲和祖母为处理那些结实无比的苎麻皮,则要辛苦好几天,从泡到刮到晒到捻,最后像变魔术一般变成了可以纳鞋底的细细的软软的却坚韧无比的苎麻绳。至于糊袼褙、描鞋底样、剪鞋面、纳鞋底等,也是琐碎、麻烦、吃力,费尽心血,这些我都在等待母亲的布鞋的漫长过程中一一想过了无数遍。这个时候,我才深深感到母亲的爱尽在这不言的琐碎麻烦吃力中。
在春节前几天,我终于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两双新的布鞋,在每只布鞋里,母亲都放了一张红色的剪纸,那图案是两只眼睛都朝一面的伸长脖子啼叫的公鸡。我知道母亲在我们家乡可以说是一位剪纸艺术家,这肯定是母亲的作品,以“公鸡啼叫”的形象对我寄予某种希望。我从小穿的就是母亲做的布鞋,但从未如此认真地、细心地、诗意地欣赏过她做的鞋。我抚摸着那两双又硬又软的新布鞋,觉得每一个针眼里都灌满了母亲的爱意与希望,心里那种暖融融甜滋滋的感觉至今不忘。在这一瞬间,母亲的面庞、身影又在我眼前生动地重现,我突然感到我虽然离开母亲数千里,可仍然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我想起了母亲那天送我时哭泣的场面,痛责自己当时所说的那句愚蠢的话。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你热衷的事情都会转瞬即逝,不过是过眼烟云,唯有母亲的爱是真实而永恒的。
照 片
母亲来过北京两次。一次在1963年,一次在1981年。她是属于故乡的,所以每次都没有住满计划好的天数,就催着我给她买回福建的火车票。第二次来北京时,她的背驼了,牙掉了。看见她衰老的样子,我感叹不已。原说好起码要在北京住一年的,但只住了一个多月就受不了啦。她不会说普通话,而她的客家话除了我之外,家里人都听不懂,她与邻居们就更难有什么交往了。我整天在学校忙,只有晚上回家才能跟她说一会儿话。她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哪里受得了这种孤独和寂寞?况且故乡有八九个孙子、孙女让她牵肠挂肚呢!在家乡时那些孙子、孙女整天簇拥着她,无论是哭是笑是闹是吵是悲是喜是苦是甜,都是生活,都是有滋有味的生活。归乡之情油然而生。尽管北京的故宫、北海、颐和园等古老宫殿、园林等令她感到新鲜,北京歌剧院的宏伟使她赞叹,长安街的宽阔让她目眩……但此刻对她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故乡。她对我说:“我整日这样吃喝,却没有人给我说话,这不是让我坐禁闭吗?”我拗不过她,只得随她的心意办。
在决定返回故乡前,我问她还有什么心愿?她说:“什么也没有。就是我想要一个会画的人照我的样子给我画一张像。”她的话一出口,我立刻就理解了。她想到死后她的“位置”问题。照我们故乡的风俗,在每年除夕那天,第一件重大的事情是要把历代祖宗的画像挂在厅堂里,上贡,烧香,磕头,以示对祖宗的敬意,祈求祖宗的保佑。到祖父祖母这一代,画像上没有留出位置,就单独把画像装在镜框里,摆在列祖列宗画像的下面。母亲也想给后代留个纪念。这是常情,岂有拒绝的理由。不过我给她的建议是去照一张相,然后放大。她很愉快地就同意了。于是我就让我爱人带她去照相。
在礼士路那间照相馆,她们遇到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照相师。他可以让最紧张的顾客也能从容而放松。几天后,我爱人把放大的近两尺见方的大照片取回来了,照片好极了,用光很有层次,构图恰到好处,母亲的脸绽开了微微的笑,像那含苞的花,看起来比现实的她年轻多了,而驼背更照不出来。我跟我爱人想母亲定会满意。
母亲戴上眼镜,看着,开始还露出满脸的笑容,突然她收起了笑容,问我们:“我怎么是一只耳朵的呢?我的那只耳朵哪里去了?”她的话吓了我一跳,连忙凑过去看,看完大笑起来,说:“妈,这是艺术性的处理,照相师照这张相片时有一个角度,你懂透视的方法吧?喏,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我也只有一只耳朵……”母亲说:“什么‘豆豉’不‘豆豉’的,我不懂!反正我要两只耳朵!”我叹着气:“是透视,不是什么‘豆豉’,你真会打岔。喏,‘透视’是这么回事……”母亲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只说:“少了一只耳朵,不好!不好!我不要!我的那些孙子们,孙子的孙子们,要是问:我的这位奶奶为什么少一只耳朵?那不是太丢人了吗?”母亲既然把问题上升到“丢人”的高度,那就必须重照。我爱人带她去找照相师,照相师哈哈大笑,我爱人解释说我母亲不懂透视原理,看不习惯,无论如何要重照一张,要钱可以重付。照相师态度极好,根本不要我们的钱就给重照了一张,并对我母亲说:老太太,放心吧,这一回是有两只耳朵的。这次终于照出了母亲完全满意的标准像。我们给照片配上了一个镜框,她临离开北京时说,这回从北京带转去的东西中,最让她满意的就是这张照片了。
此后,我在讲美学理论过程中,为了说明“艺术接受”是以接受主体的“预成图式”为依据的,说明“所见出于所知”的理论,有时就把母亲照相的故事加进讲课内容中。我的意思是:因为母亲缺少“透视”这种知识作为她的“预成图式”,所以她不能接受那没有两只耳朵的照片。每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笑,同学们也会心地笑。但是有一次,当我又要举这个例子时,我突然觉得也许母亲对那张照片有她的独特的艺术要求是对的。她诚然不懂什么“透视原理”,但她有她的艺术感觉。她甚至称得起是一位民间剪纸艺术家,她的那些剪纸创作在我们家乡是出了名的。我想起了我上大学期间,她寄布鞋给我时在鞋里放的剪纸:公鸡的侧面,竟然集中了两只眼睛,把本应是长另一面的那只眼睛也调到同一个平面上来了,这里有变形,有立体构图,可以说有属于“现代”的东西。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去嘲笑她呢?实际上对于事物的美是不能孤立起来考察的,一个事物美不美取决于它处在何种环境中,与周围环境构成何种关系,同时还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欣赏它的是哪个主体。母亲深知那张照片将有一天要挂在那些祖宗的画像下面,同时又是供后代子孙景仰的,因此她的艺术无意识要求达到“天平式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和谐、端正、庄重、肃穆的美,才能跟列祖列宗的画像融为一体。
坏 狗
1988年夏天,我回家看望父母。刚跨进大门,一只毛茸茸又肥又壮的凶猛的大狗就朝我这个“陌生人”汪汪大叫起来。这是母亲养的狗。据弟妹侄子侄女们的说法,这只狗跟我们家养过的数不清的忠于职守的好狗比较起来,是一只“坏狗”。它“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老到邻居家偷东西吃,今天叼人家院子里凉着的一块咸肉,明天咬死人家草坪上的一只小鸡,告状的人填塞门户,给家里找来无穷的麻烦,惹来数不清的是非。弟弟妹妹多次建议把这只狗处理掉,免得再生出麻烦是非来,但母亲就是不同意,说:狗是我养的,有麻烦找我,谁要是敢动它一根毛,我跟谁拼命。弟弟妹妹只好忍气吞声,表面不再说三道四,但在母亲不在时,就毫不客气地用脚踢狗,嘴里还骂着“吃货”“死狗”这类字眼。全家老少真是“同仇敌忾”,对这只终日给家里惹是生非的“坏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母亲的情面不敢下手。
我在家的那些日子,那只被弟妹们斥之为“坏狗”的狗,对它的保护人母亲的亲热、亲情和依恋则十分动人。见主人摇尾舔脚这些且不说,单说母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一群孙子孙女通过黑黑的窄窄的坑坑洼洼的石砌长街,到离家可能也有一里多地的电影院去,她的狗就总是冲在前面,为她探路和开道,为她排除可能会出现的“险情”。看电影时,狗静静躺在她的脚边,要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还替她暖脚。电影散场,人多拥挤,狗为他们开道,并紧紧护卫着母亲,不让她被人踩着或挤着,母亲顺手拉着它的长尾巴,闭着眼也能平安摸回家。狗对母亲那种尽职尽责的样子,真是令人感动。有一次,母亲用手轻轻地捋着狗的毛,对我们说:全家人谁这样照顾过我?!我们听了之后,不用说与母亲争论,甚至连笑都不敢笑。
1990年,父亲病危,我又一次被召回老家。我是黎明时分到家的,我以为还会遇到那只狗,还会听见它那汪汪的叫声,还会看见它那毛茸茸的样子,出人意料的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根本没有什么狗。我张嘴就问:那只“坏狗”呢?怎么不出来欢迎我?弟弟连忙给我使眼色,意思是让我别问。幸亏母亲的耳聋加重了,又没有戴上耳机,没有听清我的话,才没有引起麻烦。
这次在家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母亲闭口不提那只狗。狗的“下场”是弟妹们在母亲外出时七嘴八舌告诉我的。那只狗因为总去邻居家偷东西吃,为非作歹已非一时,邻居们损失惨重,对母亲所钟爱的这只“贼狗”早就恨之入骨,早就想除掉村子里的一害,只是考虑到母亲的呵护而不敢下手。有一天,村子里几个青年人聚在一起,想打牙祭,可又囊中羞涩,有一位胆子大的,就提出一个建议,趁我母亲去邻村走亲戚之机偷偷宰了“贼狗”。他们“论证”了半天,认为这既是为民除害之举,必然会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同时又解决了打牙祭资金不足的问题,真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我的两个弟弟知道之后,采取了不支持不阻拦不参加的“三不政策”,这就更壮了那伙儿年轻人的胆子。他们把狗引到一个小屋里,七八条扁担的力量结束了母亲的“爱狗”、人们眼中的“贼狗”的一生。这些青年七手八脚把狗剥了皮。狗肉在我们家乡是上等的肉食,他们看见这条被扒了皮的鲜嫩的狗肉,欢喜地手舞足蹈起来。
正当他们为自己的“胜利”欢呼的时候,母亲似乎是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那间小屋的门口。那局面是可想而知的。母亲的愤怒、哭骂和要跟他们拼命的劲头儿,把他们吓傻了。母亲给这几个青年上的纲是“谋财害命”,她认为,狗和天下的生灵一样,都是“命”。“命”这个客家话的单词要是用普通话来说,就是“生命”,世界上哪里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可贵呢!在母亲扬言要到县法院控告他们之后,这几个力大无比的小伙子竟屈辱地一齐跪在母亲的跟前,请求母亲的饶恕。那天家里也乱了套,我那两个在这件事情上实行“三不政策”的弟弟,也遭到母亲空前的叱骂。只有一个去跟她报信的侄子,才勉强过关,没有遭受批评。母亲甚至还摔了屋里的一些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
狗死不能复生。按母亲的意愿,狗的“遗体”被抬到家门口的溪灞边的砂石上,挖了一个深过一米多深坑,在溪水的呜咽声中,母亲的爱狗被隆重地“殡葬”在这里。母亲病倒了,但仍然坚持守在狗的墓地旁,晚上她被劝回家休息,由那位通风报信的侄子替她守望。如此三天三夜。
从此母亲不再养作为生灵的狗,直到她自己去世。
(1998年5月)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旧梦与远山》,这个名字本身就像一首低吟浅唱的歌,带着一种悠长的韵味,让我心生向往。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但光是名字,就足以在我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幅画面。我能想象,“旧梦”代表着过去,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却已随风而逝的时光,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片段,或许是青涩的爱恋,或许是年少的憧憬,或许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它们像褪色的老照片,泛黄而模糊,却又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力量。而“远山”,则象征着未来,那片遥不可及的风景,那种对更广阔世界的渴望,亦或是对内心深处平静的追寻。它是一种召唤,一种激励,一种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将“旧梦”与“远山”并列,仿佛是在描绘人生的旅程,我们在过往的痕迹中徘徊,又被远方的召唤所吸引。这本书的名字,给我一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而是更侧重于情感的细腻描绘,以及人生哲思的深度挖掘。我期待着,它能带领我走进一个充满回忆与希望的世界,让我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也给我勇气去追寻心中的那片“远山”。
评分“旧梦与远山”,这两个词语组合在一起,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充满了宁静而悠远的气息。我脑海里浮现的,不是具体的情节,而是一种氛围,一种情绪。我可以想象,“旧梦”可能代表着那些已经成为过去,却依旧鲜活的回忆,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那些逝去的年华。它们或许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又或许带着一丝甜美的怀念,它们是构成我们生命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远山”则给人一种广阔、辽远、不可捉摸的感觉,它可能是我们内心深处对未知的探索,对梦想的追逐,抑或是对某种精神境界的向往。这本书的名字,给我一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快节奏、强情节的小说,而更像是一本能够静下心来品读的作品,它会引导读者去感受,去体会,去思考。它可能描绘的是一个人在时间的洪流中,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对话,如何在回忆的慰藉和对远方的憧憬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好奇,作者会以怎样的方式,将这“旧梦”的缠绵与“远山”的辽阔融为一体,又会在这两者之间,编织出怎样动人的故事。
评分仅仅是《旧梦与远山》这个书名,就足以激起我内心深处的涟漪。它不像那种一眼就能看透的直白,而是含蓄而富有张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探究其背后的故事。我能感受到,“旧梦”二字,承载着过往的重量,或许是那些深埋心底的遗憾,或许是那些曾经炽热的情感,又或许是那段被时光温柔过滤的青春。它们像陈年的酒,越是沉淀,越是醇厚,在不经意间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又或是令人心头微痛的气息。而“远山”,则是一种无尽的向往,一种对未知境地的期盼,一种对心灵归宿的追寻。它可能是一片遥不可及的风景,也可能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理想,更可能是一种内心的平静与圆满。将这两者并列,便勾勒出了一条时间的轨迹,从过去的回响,走向未来的召唤。我猜测,这本书里一定有关于成长,关于失去,关于追寻的深刻探讨。它或许会用一种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方式,描绘出主人公在面对过去与未来时的挣扎与选择,在回忆的温存与对远方的渴望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
评分一本关于时间的书,虽然我没读过,但光是这个名字就让我想了好多。旧梦,总带着一丝褪色的温柔,好像隔着一层薄雾,依稀能看到年轻时的影子,那些不经意间的欢笑,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它们沉淀下来,化作了悠长的回忆。而远山,则是一种辽阔,一种不可及,一种对未来的期许,或许是未曾踏足的风景,或许是内心深处渴望的宁静。将这两个词并列,仿佛在描绘一条时间的河流,它从过往的旧梦中流淌而来,最终奔向那遥远的、未知的山峦。我猜,这本书大概会触及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些被时间冲刷过,又被岁月沉淀下的情感。我能想象,翻开它,就像推开了一扇尘封的门,里面有风,有光,有细碎的声响,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又似乎是书中人共同的经历。这样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故事感,一种引人入胜的魔力,让人忍不住想去探寻,在这“旧梦”与“远山”之间,究竟埋藏着怎样的故事,怎样的情愫,怎样的哲思。它勾起了我对往昔的回味,也激起了我对未来的遐想,似乎预示着一场关于成长,关于追寻,关于生命意义的深刻探索。
评分这本《旧梦与远山》,光是书名就充满了诗意和意境,让人一看便心生向往。我总觉得,一个好的书名,就像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窗户,它暗示着即将展开的故事,也勾勒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情感。这里的“旧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那些曾经的青春,曾经的爱恋,曾经的遗憾。它们如同梦境一般,虽然不真切,却又真实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时不时地浮现,带来一丝酸楚,又夹杂着一丝温暖。而“远山”,则代表着一种距离,一种目标,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它可能是我们尚未到达的远方,可能是我们内心深处渴望实现的理想,也可能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平静与安宁的追寻。将“旧梦”与“远山”联系在一起,似乎暗示着一种关于生命旅程的思考:我们是否一直在旧梦的回响中,朝着远方的山峦前行?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们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也或许能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我期待着,它能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那些关于梦想、关于回忆、关于人生的感悟,让我们在阅读中找到共鸣,找到慰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远山”。
评分关注百姓生存的良心之作
评分美好的体验,正版的质量,强大的京东
评分很好的书,正版价格也划算,满意!读书可以使自己的知识得到积累,君子学以聚之。总之,爱好读书是好事。让我们都来读书吧。 其实读书有很多好处,就等有心人去慢慢发现.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你有属于自己的本领靠自己生存。 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充实,学习到不同的东西。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还能带给你许多重要的好处。 多读书,可以让你觉得有许多的写作灵感。可以让你在写作文的方法上用的更好。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往往可以运用一些书中的好词好句和生活哲理。让别人觉得你更富有文采,美感。 多读书,可以让你全身都有礼节。俗话说:“第一印象最重要。”从你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中,就可以让别人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多读书可以让人感觉你知书答礼,颇有风度。 多读书,可以让你多增加一些课外知识。培根先生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不错,多读书,增长了课外知识,可以让你感到浑身充满了一股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激励着你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从书中,你往往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使你不断地改正错误,摆正自己前进的方向。所以,书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多读书,可以让你变聪明,变得有智慧去战胜对手。书让你变得更聪明,你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困难。让你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你又向你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多读书,也能使你的心情便得快乐。读书也是一种休闲,一种娱乐的方式。读书可以调节身体的血管流动,使你身心健康。所以在书的海洋里遨游也是一种无限快乐的事情。用读书来为自己放松心情也是一种十分明智的。 读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知识和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为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好的、扎实的基础!读书养性,读书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温文尔雅,具有书卷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写文章就才思敏捷;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只要熟读深思,你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了;感受世界的不同。 不需要有生存的压力,必竞都是有父母的负担。 虽然现在读书的压力很大,但请务必相信你是幸福的。 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孩子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没办法享受的。 所以,你现在不需要总结,随着年龄的成长,你会明白的,还是有时间多学习一下。 古代的那些文人墨客,都有一个相同的爱好-------读书.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是每个人都做过的事情,有许多人爱书如宝,手不释卷,因为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读一些有关写作方面的书籍,能使我们改正作文中的一些不足,从而提高了我们的习作水平.读书的好处还有一点,就是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做准备.那么,读书有哪些好处呢?1读书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量.多读一些好书,能让我们了解许多科学知识.2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千里眼.俗话说的好;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多读一些书,能通古今,通四方,很多事都可以未卜先知.3读书可以让我们励志.读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可以激起我们的爱国热情.4读书能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
评分女儿很喜欢,,应该是正版
评分是一本8错的,希望大家与我一起阅读
评分正版好书,装帧好,质量棒,内容不错,价格实惠,发货快,送货服务好!
评分不错的一本书,写了作者从大山走出来,难忘故土
评分给别人买的
评分不错的一本书,分析到位,有一些参考价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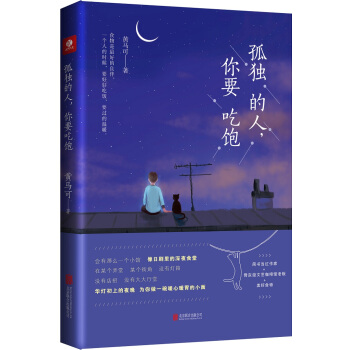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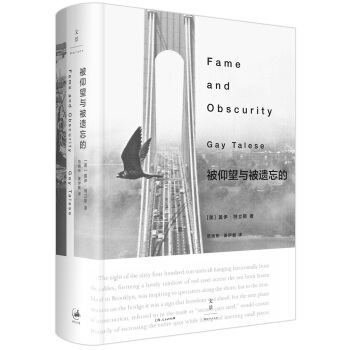



![小王子(平装) [3-6岁] [LE PETIT PRINCE THE LITTLE PRI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96892/bb9fcca6-68f9-48b0-a37a-5934c8f6e7aa.jpg)
![大个子老鼠小个子猫:三个笨学生(彩色注音版)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98671/03001f9d-c4fb-4be2-b5f8-55a57e99c153.jpg)
![笨狼的故事(2):笨狼旅行记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51867/rBEhVVG5nUEIAAAAAASQfI1FlooAAANBgINgcAABJCU432.jpg)
![新悦读之旅 小桔灯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88918/5497696dN4bb493ed.jpg)
![超有趣幼儿成语故事(儿童注音美绘本) [6-9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77272/577e16b5N5ee911ed.jpg)



![宝葫芦的秘密(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56253/577f4057N8e9a64f6.jpg)

![伊格魔法全集(套装共7册) [7-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38786/5409693bNe847c492.jpg)
![想象你是一颗飞翔的种子 [Acor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76725/554b1860N883ff65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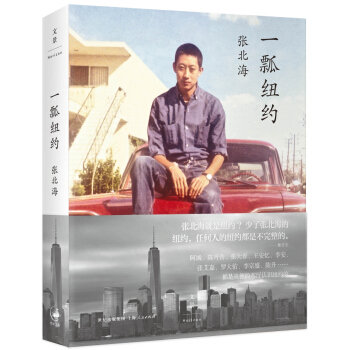
![汤姆·索亚历险记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06037/5576a504N52981c6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