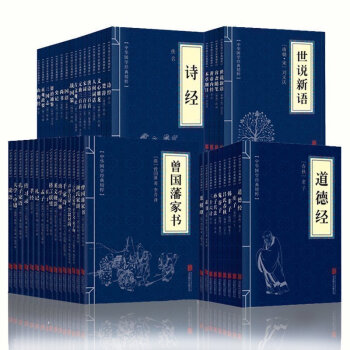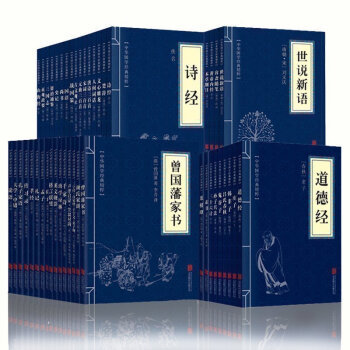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国学大师,历任北大、北师大、中大、浙大、西南联大教授,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书写者。七十年来《习坎庸言》就像传说中的《葵花宝典》,而今首度公开面世。
内容简介
《习坎庸言 鸭池十讲》是由“习坎庸言”和“鸭池十讲”两部分组成。《习坎庸言》是罗庸先生在西南联大习坎斋(取《易》之“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之意)自己寓所作的学术讲座讲稿,主题包孕广博,分为勉学、识仁、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等内外学术16篇,由学生李觐高根据笔记整理。《鸭池十讲》是罗庸先生在昆明期间另一系统的演讲。收其讲演稿十篇。因昆明的滇池在元代名鸭池,“以记地故,因题此名”。十篇文章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谈儒,论诗,谈士,娓娓道来,足见其学识之博,见解之深,更可窥其于国忧家难之即,对民族精神之阐释。作者简介
罗庸(1900—1950),字庸中,号习坎,蒙古族,生于北京。著名国学家。原籍江苏江都,清初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1926年参与创办华北大学。1927年应邀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同年秋,应鲁迅之邀,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2年起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后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碚。生前出版的著作极少,只有《鸭池十讲》和《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等。精彩书评
★众所周知,先生的道德文章属于儒家正宗,其中还融有释老之学,如果生当唐世,近乎谓“三教论衡”。——吴晓铃
★在一般人眼中,罗庸只有薄薄一册《鸭池十讲》,作为名教授,未免有点寒碜。但这与罗庸的文学教育观念有关:“文学本来是极活泼的东西,其所寄托在文字,而本身却散在生活的各方面。假如上堂就有国文,下堂就没国文,那就失去了国文的目的。”罗庸因此而提倡“打成一片的国文教学法”,即将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合而为一。如此将全副精力集中在教学中的教授,即便著述无多,依旧值得敬重。
——陈平原
★先生的人品和学识可并顾炎武和黄宗羲。
——齐燕铭
★罗先生这本书非常好读,我以为可以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并列,是那种常读常新的书,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罗庸对于中国文化深入了解,也是非常亲近的感情,这一点他很像钱穆,他的这些文章可以说篇篇动人,虽然半个世纪前的演讲,但今天读来还让人心有所动。——著名学者孟繁华
★罗庸先生的《鸭池十讲》,讲到为士之道。在罗先生眼中,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们以在野之身,积极做文化运动,孔夫子便是一例。战国时,士大夫学商人模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最好的时期是两汉四百年,特别是东汉,“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随后,董卓入卫,奸雄当道几百年,“处士一变而为党锢,再变而为文学侍从,三变而为世族的门客。读书人的生活,从居乡教授到运筹决策,再到做劝进表,加九锡文,最后到应诏咏妓,南朝士人的身份降到无可再降”。直至两宋,理学家们于讲学之余,尚能注意到乡村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公约之类。而到了明清两代,士子们与胥吏政治相因缘,“出则黩货弄权,处则鱼肉乡里”,士大夫的意义,似甚少有人顾及。
——南方周末
目录
习坎庸言缘起/
规约/
内篇一勉学/
内篇二识仁/
内篇三六艺/
内篇四诸史/
内篇五九流/
内篇六理学/
内篇七经世/
内篇八文章/
外篇一种族/
外篇二文化/
外篇三质文/
外篇四礼乐/
外篇五乡党/
外篇六学校/
外篇七儒侠/
外篇八风俗/
后记/
鸭池十讲
前记/
一我与《论语》/
二儒家的根本精神/
三论为己之学/
四感与思/
五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六诗人/
七思无邪/
八诗的境界/
九少陵诗论/
十欣遇/
精彩书摘
习坎庸言内篇三六艺
昔人治经,往往拘于门户,致有今古之争、汉宋之争。五四而后,复有对经学发生怀疑,倡为废经之论。而亦有视经为史料,以纯科学态度研究之者,遂与今古之争、汉宋之争并立,成为经学中之四派焉。今就所知稍加论列如次。
先论六经定名。六经或称六艺(刘歆《七略》有六艺略),孔子时无此称也,《论语》中亦无以六经教弟子之记载,然细按之,则夫子固尝以礼乐教弟子矣。颜回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是孔子以礼教也。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子击罄于卫,是孔子以乐教也。《论语》论诗之处尤多,而书则少,论及尧日一篇,是否孔子所说,疑未能定。孔子作春秋之事,《论语》无明文,称易之处则有: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其下文曰。不占而已矣。未能剧指此曰孔子尝以易教也。《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由、子夏。孔子之教弟子者,如此而已。
《庄子·天道篇》:孔子……翻十二经以说。或曰十二经即六经六纬,实则庄子之所谓十二经者,未易知其果何指也。(十二或为六字之讹)礼记经解,絜静精微易教也,恭敬庄俭礼教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良易乐教也,疏迩知远书教也,展辞比事春秋教也。此易、诗、书、礼、乐、春秋次第即为汉志所本,后之《隋书·经籍志》,逮清《四库全书》,莫不放此。《周礼·地官·保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又大司徒之职,以师三物教万民……一曰六艺,六艺次第同此)。自汉人以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孔门艺,因别称礼乐射御书数为古之六艺焉。《周礼》本为晚出之书,然亦保有不少古代原料,此六艺或即古之六艺(《论语》论射御处甚多,书数为小学之事,故未论及),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之名当起于战国,此证以《论语》而可见者。《论语》凡孔子弟子所记多称子曰,多单句;凡称孔子曰者,则多再传弟子所记,文多成格套(如尊五美,屏四恶,君子有三畏等),《礼记》经解篇已有整齐之六艺理论,是知六经之说或已定于春秋战国之际也。
至汉而有今古文之分。今文靠口传,重大义;古文靠简册,重训诂(清人尤重训诂)。至宋而又有汉宋之争,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因之各经显晦亦随时代而不同。
古之六艺与孔门六艺不同者,六经无射御书数,古六艺无易诗书春秋,一古射御或当有经,由礼大射可以推知)。而礼乐居六艺之首,则其所同者也。吾人在古代文化方面着眼,从孔门教学态度着眼,则六经次第礼应居第一,乐第二,诗第三。诗为乐词(乐言其音调,诗指其篇章);书太史所掌,是书已包之于礼之中;春秋亦太史所掌;易,太卜纀所掌,均应包括于礼;诗亦应为国史所掌,《大雅·生民》《小雅·六月》即是史诗。史诗乃诗的正宗,诗人即史家。卫宏诗序:国史明乎得失之故,云云可证。此章实齐所以有六经皆史之说也。由是论之,诗应居书前,春秋应列书后,易为卜筮之书,实如禅宗之教外别传。以此意排六经次第,则当为礼、乐、诗、书、春秋、易。然经解何以置易于六经之首?盖战国之末,秦汉之初,六经逐渐成系统化、哲学化,故置易于首,其余五经遂与易成为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此盖儒家与阴阳家合流之结果也。有一旁证焉,即由荀孟之别亦可得窥六经之次第。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此语不见于孟荀列传,见赵岐《孟子题辞》,观附注),是以法先王,盖长于诗书,未必长于礼乐也。荀子隆礼乐而杀诗书,故法后王。《劝学篇》“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云云,故继之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视礼乐在前,以六经为经世致用之学;孟子以诗书在前,视六经为义理训诂之学。盖荀子深得孔门立教之意,为儒家正宗;孟子实为儒家别派。(汉时荀孟并称,隋唐之后,贬荀尊孟,至宋而极。是以读六经者,只见其训诂名物而不知经世致用也。然由荀子至于韩非李斯,儒家一变而为法家,孔门以六艺设教之意,经数度变迁,原始精神盖不可复观矣。
今依新次分论之:
一、礼。《说文》:礼,复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古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国之大事也。今所见者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仪礼为礼经,今存十七篇,汉人称之为士礼(所谓推士礼以至于天下),实属记录节文之书。如《聘礼》《燕礼》所记,盖一礼节单子而已。就今所见之十七篇而论,知仪礼来源甚古。仪礼形式多仿自周人,至春秋仍通行,然士丧祀,祝有夏祝、商祝、周祝,夏祝商祝即夏商仪礼之残留,可知其源甚古也(惟夏祝商祝于丧礼中执事殊少)。《士昏礼》《士丧礼》篇后皆有义,此即礼记,约为老儒解短经,弟子笔记,本与礼经有别也。
今之社会学家读仪礼,目亲迎礼之为掠夺婚姻;新史学家读仪礼,目之为变性的遗留者。细按仪礼概非无故,《士昏礼》后之《昏义》,若与《礼记·昏义》相比,则知礼记曲解处多,然则墨守经传欺,抑从社会学者与新史学者之说欺,此孔门教学态度所宜先知,否则必生无所适从之苦。欲识孔门教学态度,必先识仁,仁者大用流行之谓(宋人曰天理流行),完全看重自己的生命,亦即全人类生命之谓,把人生看成活的,动的,向前进的,以人为主,以物为偿,不仅不随物转,且不容身外之物停留不进,因如此则有累有遗。此为孔门讲学主旨所在,足以对于历史上的遗产,可用者用之,其不可用者革之,可以存在者因之,其不应存在者去之,一切外物均须顺我的条理,我不能就它的范围(如茶杯本用以饮茶,若以饮酒即可目为酒杯),孔子于此认识极为透彻。故礼已由野蛮入与文明,孔子乃利用之使之更文明,且追而使人忘其野蛮之一面。人的地位高,一切皆我的注脚,一切皆为我所用也。仪礼原由野蛮而来,然至孔子面目已为之一新,盖孔子学有根源,故能贯之以道。不明乎此,扬甲抑乙,要为不通之论耳。(《五礼通考》为读礼必读之书)
戴记,仅有少数篇目真为礼记(如冠义、昏义皆有仪礼为经),其他各篇凡七十子后学所记均收入,实为儒家一大业书,由汉晋至唐,学者多注意昏义丧义,甚少理会乐记、学记、仲尼燕居各篇,犹存古意。宋人反是。此为讲学态度之转变。今欲分析礼记内容,则殊不易,韩非显学所称之八儒恐皆包有之。《王制》《月令投壶》《深衣》所记皆为礼学专篇,既非释经之传,亦不得称为儒学。大戴记多曾子语,若合二戴记以分析儒之派别,则讲《论语》可无笼统浮泛之病,然则此非本篇所论者矣(清人除朱彬《礼记训纂》,孙衣言《礼记集解》外,尚无佳疏,仍待重作)。
《周礼》本周官经(以别于《尚书》之周官)。冬官亡佚,汉人补入《考工记》。古文家尊《周礼》,今文家则斥为刘歆伪造。《周礼》中盖有丛杂不全的古史料甚多,曾经刘歆整理,然亦不可一概斥之为汉人伪造也(如周礼论诗六义之次第,曰风赋比兴雅颂,甚有根据,盖得古之遗意)。《考工记》为晚出之书甚易见(由地理考之似为晋人之书),记中以燕秦胡并举,是则战国时之说也。后人以《周礼》配《仪礼》《礼记》,称曰三礼,所包至广。盖儒者以礼为本,荀子隆礼,其意深远。欲治六经必先自治礼始,此大本大原也。(礼之用《礼乐篇》再详论之)
二、乐:乐无经,诗三百篇即《乐经》(《乐记》二十一篇,戴记合为一篇)。汉文得乐人宝公善说乐,然亦只记其铿锵鼓舞而已。是以《汉书·艺文志》曰:“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云云。大约古乐无谱,仅赖口耳相传而已。《尔雅》:“大版谓之业。”《左传》:“臣属肄业及亡。”后人乃误以案属乐谱,盖不然也。《汉志·诗赋略》著录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称之曰曲曰折,推想汉乐谱盖宇旁尽有曲折也(汉人乐谱已不可见,唐乐谱宇旁有曲折,《大藏经》《点山集》及道藏中有之,约略可以推见汉乐谱之大概,至歌态舞容,征之故记亦尚零星可见。然晋唐而后,学者聚讼,唯在吹律旋宫,乐学日益湮毁矣。(乐之用《礼乐篇》详之)
三、诗:诗即乐章。今人所聚讼者为诗系孔子手订抑系民谣问题。余意论诗有必须注意者二:读诗不能忘记音乐,一切解释均不能离开音乐,根据音乐解释,则可知二南何以编排在前,周颂何以在后。旧说以诗经按照年代编排,由音乐见地论之,此说甚谬。诗之内容代表周代文化面目,不必多牵涉孔子与先王之泽,而比较各地风诗之异同,则甚重要。就篇章字句而言,以音乐为之纲领;就诗的内容而言,以周文化作为纲领,由此读诗距诗意必不太远。《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理,可以群,可以怨,为读诗最重要见解,名物训诂抑其次也。
讲诗不必从毛,亦不必从三家,将古书中讲话之处连缀来讲,则必多所通解,如此则汉儒拘泥可以打破。盖三家与毛不同,宜汇通不宜墨守也。朱子从白文观诗之大义,其方法甚为可取,惟拘于三体三用之说,其极必言美剌,是朱说大病。近之说诗者,悉能打破旧说,惟多忘记诗乃代表周文化的面目,以是多浮浅不切之病。诗教不如是之卑也。(此节未尽之意《文章篇》详之)
四、书:今古之手可置勿论,仅就二十八篇言之,则书之面目已非固有,其中必多改动之处,如盘庚用语与用字是否为商代的即颇有问题也。书之内容颇为丛杂,如牧誓、大诰、酒诰仅为命令,顾命则多陈丧礼,与尚书之体不合。吕刑为中国最古法律条文,禹贡与礼王制性质为近,如此顾命并入仪礼,禹贡并入礼记,始与《尚书》记言之体相合。《洪范》一篇所托,或为阴阳家言,或为礼官之语,盖为后人连缀而成。而于行文之前加武王胜殷,杀纣,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的帽子而已。设将书中各篇归类整理之,则知《尚书》材料极不整齐,盖残缺亡佚者多矣。
……
前言/序言
出版前言民国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一个学者辈出的时代。特别是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西南联合大学,更是聚集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大师。一些学者或因其倜傥风流,或因其著作等身,或因其特殊的符号意义,至今仍为人所乐道;也有一些学者,虽然同样学富五车,却因英年早逝或惜墨如金,而几至无闻。罗庸先生即是后者之一员。
罗庸先生(1900—1950)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字膺中,号习坎,笔名有耘人、佗陵、修梅等,是清初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出生于北京。17岁进入北大文科国文门学习。后又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是同事。又先后任教于北大、女师大、北师大、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1932年回到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于1938年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罗庸先生即在此任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中文系主任,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课程。
时值抗战,物价飞涨,教授们大都生活困顿,教学之余,不得不各展所长,补贴家用。王力先生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闻一多会刻图章,每天忙个不休;潘光旦教务长曾张夹设笼捕鼠,由夫人做成菜。罗庸擅长诗词骈文,据说著名的西南联大校歌即出于他手;罗庸书法也佳,由冯友兰先生拟稿、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堪称双璧。但罗庸却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者。1942年春,一场大火把他的家当烧个精光,他不以为意,还把联大中文系的几位教师和研究生召集到一起,“共约讲习之会”,“旨在温故知新,克己复礼,以免独学无友”。讲课历时四个月,主题包孕广博,分为勉学、识仁、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等内外学术16篇,由学生李觐高根据笔记整理,是为《习坎庸言》。
罗庸先生在昆明期间另一系统的演讲后来也被整理成书,这就是《鸭池十讲》。收其讲演稿十篇。因昆明的滇池在元代名鸭池,“以记地故,因题此名”。十篇文章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谈儒,论诗,谈士,娓娓道来,足见其学识之博,见解之深,更可窥其于国忧家难之即,对民族精神之阐释。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归时,罗先生却决定留在昆明组建师范学院,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赴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碚。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中回忆说:当年在西南联大,“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罗庸讲课声音洪亮,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自身陶醉其中,学生更为之神往。有一次讲《楚辞》中的《九歌》,海报一出,连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也跑到城西来听讲。一间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窗外还站着人。罗先生一气讲了两三个小时,夜深才结束。一位听过罗庸讲课的学生回忆,罗先生讲杜诗,“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
《习坎庸言》记录者李觐高先生弥留之时,“神游抗战艰苦时期西南联大讲师时代,断断续续,长达数日”,醒后言及《习坎庸言》已为孤本,嘱其子“必予刊印,以续绝学”。李安国先生遵父嘱,“即予研读,先求断句,再究连贯”,终于成书。本社此次重新出版,对原书仍取“不加一字取舍”的原则,但广泛参阅古籍,对引文重新查证标点,以期更符合罗庸先生原意。罗先生一生超然物外,志趣高雅,潜心学问,温文儒雅,佛学、儒学造诣精深,至今已难觅能出其右者,却英年早逝,只有《习坎庸言》和《鸭池十讲》两本薄薄的专著。今将两书合为一书,以飨读者,可更全面地了解罗庸先生对文化学术之深悟,缅怀当年西南联大名师之风采,更希望于此对读者了解和领悟中国之文化及民族之精神有所裨益。
本书编者
2015年3月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文字语言呈现出一种混合的质感,它既有古典文学的典雅与韵味,在描摹意境和表达情感时,那种用词的精准和音律的美感令人叹服;但同时,在阐述观点时,它又保持着一种现代思想的清晰和锐利,逻辑推理毫不含糊,毫不拖泥带水。这种融合,使得全书读起来既有文采,又不失力度,避免了陷入纯粹的文字游戏,也摆脱了枯燥的学术腔调。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关于“自我认知”和“处世哲学”的议题时,作者的洞察力直达人心的幽微之处,常常让我产生一种“作者原来比我自己更懂我”的错觉。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共情能力,通过文字构建了一个安全而又充满挑战的对话空间,引导读者进行深层次的自我审视。总而言之,这绝非一本可以被快速消费的书,它更像是一份需要反复研读的“人生指南”,每一次重读,都会因为个人阅历的增长,而发现全新的层次和更深远的意涵,这种长久的价值,才是衡量一本好书的最高标准。
评分阅读体验上,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感受是“节奏的错落有致”。有些章节的论述如同急流,观点密集,逻辑链条环环相扣,读起来需要全神贯注,甚至需要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精炼的句子,生怕错过了一丝丝的推导过程。然而,紧接着的下一部分,笔锋又忽然转为舒缓,仿佛作者停下来,让你喘口气,去消化刚才的“高强度信息轰炸”。这种张弛有度的行文,极大地避免了长时间阅读带来的疲劳感。特别是涉及到一些跨学科的引用时,作者的处理方式非常高明,他不像某些学者那样堆砌术语,而是用一种近乎讲故事的方式,将复杂的理论融入到日常的案例分析中,使得即便是对某些专业领域了解不深的读者,也能大致领会其核心精神。这种对读者心流的体贴入微,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与可读性实现了绝佳的平衡。读罢一个章节,我常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不是被强行灌输的结果,而是跟随作者的思路,自己“走”到那个结论的体验,这种参与感非常宝贵。
评分我注意到书中对于“时间”这个概念的处理,展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视角。它似乎超越了线性的、钟表式的计量,而更倾向于将时间视为一种可塑的、充满韧性的存在。在论及“习坎”之困境时,作者并没有给出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反而强调了“在过程中驻留”的价值。他似乎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并非跨越障碍,而是学会与障碍共处,并在这种共处中积蓄力量。这种观点,与当下社会推崇的“快速迭代”和“立即见效”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尤为珍贵。书中对历史典故的引用也颇为考究,并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精心挑选,它们的功能是作为一个参照系,用古人的经验来映照当代的困惑,使得原本抽象的讨论变得有了历史的厚度和参照的深度。我感觉,这本书的核心魅力在于它敢于挑战那些被约定俗成的“成功学”叙事,转而赞颂那些在困境中默默坚持、不求速成的“庸”者之德。
评分初捧此书,未及细读,仅凭书名和封面设计,便觉一股古朴而深沉的气息扑面而来。那“习坎”二字,让人联想到《易经》中的艰难险阻,而“庸言”则暗示着日常的、平实的智慧。装帧的色调和字体选择,都透露出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承载。我期待在这字里行间,能找到面对现实困境时,那些看似寻常却蕴含至理的言说。这本书的厚度适中,拿在手中颇有分量,仿佛沉淀了岁月的智慧,而非浮于表面的喧嚣之作。我特别留意了作者的署名和引言部分,总感觉一位真正有学养的作者,其文字的起点,必然是对生命根本命题的追问。它不像市面上那些追求快速阅读和即时满足的读物,更像是一坛需要时间慢慢开启和品味的陈酿,让人忍不住想探究,究竟是怎样的“十讲”,才能构成这“鸭池”之地的深刻反思。这种对内容本身的强烈好奇心,驱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它构建的世界,去体会那种历经磨砺后沉淀下来的,不事雕琢的真知灼见。这本书的气场很强,让人不敢轻易亵渎,需要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去对待。
评分这书的开篇叙事手法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它没有直接切入宏大的哲学思辨,而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具象的场景作为引入——那片据说承载了作者多年沉思的“鸭池”。这种地域性的、带有个人情感印记的描述,一下子将读者从书本的抽象概念中拉回到了一个鲜活的、可以想象的物理空间。作者似乎在用一种近乎散文诗的笔调,描绘着池水的涟漪、岸边的草木,乃至那群鸭子日常的活动。这种看似闲笔的描写,实则暗藏着对自然规律的体察与敬畏,也为后续的“十讲”奠定了某种朴素而坚实的基调。我感觉作者是在用这种环境的描写来“定调”,告诉读者,真正的学问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最细微、最日常的观察中提炼出来的。这种叙事节奏的把握非常精妙,既不急躁,也不拖沓,让人在享受文字画面感的同时,也隐隐感觉到背后那股蓄势待发的思想张力。这种由景入理的过渡,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哲思表达的独特驾驭能力,绝非一般学院派的刻板论述可比。
评分很好,送货速度也很快。
评分一星是给京东的,与商品无关,现在一搞活动,准是大面积无货,活动一完,立马有货,装蒜的水平是越来越高。还有,你既然推出京东钱包,能不能给配送人员培训一下,配送人员都不知道钱包优惠券怎么用,告诉我到付不能用,其实是可以的,导致没有用上,给京东的差评。
评分大师作品,深入浅出,包装精美
评分书质量不错,还没看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还不错,代替大家小书同本,这个便宜。
评分传说。。。。。。。。
评分编辑太不负责任了,每页都有错儿,这书没法读。
评分很好的书,唯一遗憾就是纸张不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