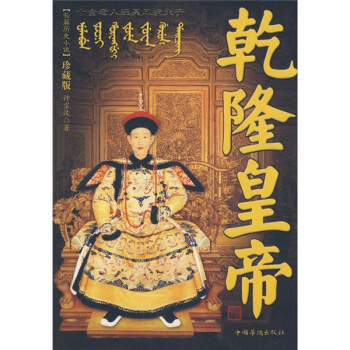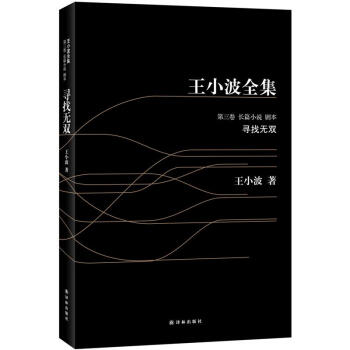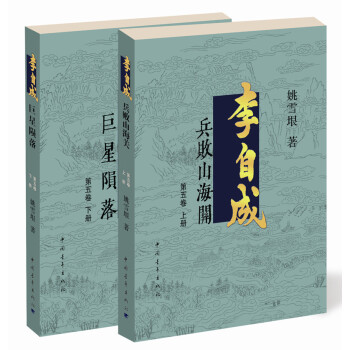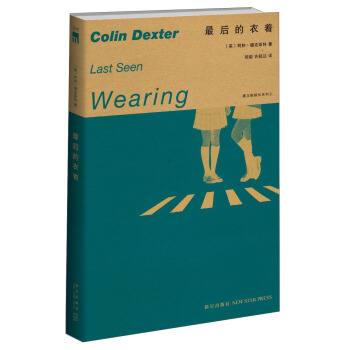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是了解安吉拉·卡特这位风格独树一帜的英国著名女作家最著名的代表作,也是她毕生致力于重述童话、奠定其奇异诡谲、瑰丽璀璨风格的巅峰之作。了解安吉拉·卡特,从阅读《染血之室》开始。内容简介
本书是卡特最为著名的一个短篇集,收录了包含题名故事在内的十个短篇。这是一个纯粹以民间传说和童话为素材的集子,是蓝胡子、美女与野兽、小红帽、白雪公主等故事主题的多重变奏与盛大交响曲。作者简介
安吉拉·卡特(AngelaCarter,1940—1992),英国著名女作家,作品风格独树一帜,混合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哥特式及黑暗系童话,想象奇异诡谲,语言瑰丽璀璨,充满戏仿的狂欢。她曾于1969年获毛姆奖,1983年担任布克奖评委,被《时代》周刊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爱》《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新夏娃的激情》《马戏团之夜》《明智的孩子》等,短篇小说集《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短篇小说合集《焚舟纪》等;收集编有《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严韵,台湾女诗人,译者,伦敦大学戏剧研究专业硕士。翻译过多部安吉拉·卡特的作品,如《明智的孩子》《焚舟纪》等。出版有诗集《日光夜景》。
精彩书评
《染血之室》是卡特的代表杰作,在这本书里,她高蹈、热烈的模式完美契合故事的需求。——萨缪尔·拉什迪
1980年,也就是《染血之室》出版一年后,卡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短篇小说并非是简约抽象的,它是洛可可式的。让我感觉一切尽在掌控。就像是在写一出室内乐,而不是创作交响乐。”她的语气中显示了自豪兴奋和一种精于此道的感觉。这部故事集将会吸引到更广泛的新读者。《染血之室》让她从民间故事中发现了崭新的领域,也探索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杂糅方式,正和她自己无法归类的天赋相得益彰。从今往后,她的作品将为世界所关注,而她,也将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
——海伦·辛普森(英国女作家)
以家喻户晓的童话做题材有个好处(同时也是坏处),那就是改写的意图和意义颇为方便解读。这或许很大一部分能解释何以《染血之室》是卡特众多作品中最受注目与欢迎的一本——不只读者容易“进入状况”,研究者更不愁找不到切入角度和分析重点。
——严韵
目录
导读(吴晓雷译)Ⅰ染血之室1
师先生的恋曲57
老虎新娘75
穿靴猫103
精灵王133
雪孩145
爱之宅的女主人149
狼人173
与狼为伴179
狼女艾丽斯195
前言/序言
“故事并不像短篇小说那样记录日常经验,”安吉拉·卡特,在她1974年首部短篇小说集《烟火》的后记中这样写道,“而是利用日常生活背后所隐匿的形象体系,来阐释日常经验。”这种截然的区分,用她后来的话说,就是“支离破碎的顿悟瞬间构成的20世纪小说”与她所青睐的艺术形式,故事,所具备的“华丽、非自然的”风格和象征主义的差别。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哥特传奇、残忍故事、传奇、恐怖故事、华丽叙事,这些直接描述潜意识画面的故事形式”一直吸引着她。所以,在第二部短篇集《染血之室》中,她不仅持续了这种哥特风格,还融入了西欧传统童话故事中的情节。她发现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别具特色的全新的融合方式,可以让她的声音为更多的读者听到。《染血之室》常常——却是错误地——被人描述成了一组加入了颠覆性女权主义情节的传统童话故事。但其实,这些是全新的故事,而非故事的重述。卡特曾明确地表示:“我并不是要写几个不同的‘版本’出来,或是,像本书的美国版中说的那么可怕,是什么‘成人版的’童话故事,而是要把这些传统故事中蕴藏的现代内容提炼出来,用作新故事的开端。”这些故事也并非如此相似,可以一言蔽之,无论是篇幅的长短,还是叙述的语气,故事与故事都大相径庭。就拿书名这篇故事来说,跟书中其他任何一篇相比都长了两倍不止,而跟最短的一篇比,整整有近三十倍那么长。再比如说,这篇故事娓娓道来、逐渐加强的哥特风格,和《穿靴猫》突飞猛进式的性闹剧,或是《狼人》那种简洁残酷的风格,都迥然不同。也正是这种差异,给予了这部短篇故事集一种令人难忘的复杂性——正因其假以短篇小说集的这样一种形式,才可以婉转曲折、变幻多样地从十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处理小说的主题。
《染血之室》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用其晶莹剔透的切面,或反射,或散射,绘出一幅幅——女异性恋者——欲与性的画像。而女异性恋者这一叙述角度,在当时,也就是1979年,仍属罕见。请记住,这一年佩内洛浦·菲兹杰拉德的《离岸》获得了布克奖;佩内洛浦·莱福里的《时间的宝藏》赢得了国家图书奖;两年后,安尼塔·布鲁克内的处女作《人之初》诞生;53岁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刚刚当选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时年39岁的安吉拉·卡特,写下了七本书,然而至今为止,这些书只获得了少数的赞许。
卡特后来受到的批评认为她不再像以往那样敢于挑战禁忌(“她永远也想象不出灰姑娘和仙女教母同床共枕的画面。”譬如帕特里希亚·敦克,就曾作此言)。但这种评价似乎有失公允。她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平息。过去十年,在高校中被广泛研读的《染血之室》,明显激起了一大批学生的愤慨和敌意,他们看到自己儿时的睡前故事被改头换面,如今已是满目的性与暴力,不禁怒不可遏了。不过,正如卡特所言:“我只是将这些传统故事中的现代因素挪为今用;而这些现代因素就是残暴而性感。”她的想象力中确有一种残忍肉欲的品质,浸淫了哥特的主题,在她年轻的时候尤甚。(后来,在她出版了《马戏团之夜》之后,她说:“知道吗,有时,我回过头去看自己写的东西,也会被自己想象中的暴力吓到。那都是在我有家有室之前了。”)
她把传统的童话故事拿来,用它们创作新的故事。童话故事,被实用地描述成了旧时的科幻小说。卡特当然是这样看待这些故事的,并用它们来尝试事物的多样性。她对大部分带有乌托邦视角和思辨色彩的科幻小说都欣赏有加——“读过很多这类作家的作品之后,我会觉得他们是在表达一些思想,而这基本上也就是我在努力做的。”同时,就像那些叛逆作家常发现的那样,在处理有争议性的话题时,曲笔和富于想象的隐喻就变得十分有用了。倒不是因为卡特介意不然会引发反感,而是不管她介意与否,利用历经时间考验的童话故事这种形式,那些原本不会成为她读者的人,也开始阅读她的作品了。而她采取幻想和童话的形式,也另有激进的用意;在给好友罗伯特·库夫的信中,她写道:“我确实相信,虚幻作品,作为现实之外的另一种人类经验形式,是有自我意识的(也就是说,它绝不仅是单纯的事件记录),也是有助于改变现实本身的。”
这样说的话,她的作品似乎听起来有些过于程式化了;不过,尽管一方面,她是在用幻想来表达思想,但另一方面,这些童话、传说所提供的画面和意象,也点燃了她的想象——雪地上的斑斑血迹和鸦羽,布满浮尘的镜上洒落的月光,五朔节时的墓地。《染血之室》中的这些故事,和这些深刻而清晰的想象之悦交相呼应。此外,她所创造的这个不同寻常的世界,还是一个令人惊诧的栩栩如生的具象世界,最细微的感受也丝毫不落,就像在《老虎新娘》一篇中,不忘描述热蜡从蜡烛上滴下,滚落在少女裸露的肩膀上。她热衷于描述奢华的饰物,用丰富的语言来表现丰富的场面。对话在她笔下倒没那么得心应手,她曾多年避而不用,还开玩笑说,拿动物当主角的好处就是不用让它们开口说话。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则被她称为“低级的模仿”,也不合她的心意。这倒不是说,她不善于观察,没有什么比她仿如人类学调查般观察入微的新闻风格更犀利的了,只是她的天赋最终没用于“低级模仿”而已。(看看《缝被子的人》,虽未被收录,却是这一类的典型,有趣,但大概是她最不成功的作品。)
卡特是一个视觉想象力非凡,又爱进行抽象思维的思想者。她之所以喜欢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正如她在《烟花》后记中所述),是因为,“形象和理性可以如此相融,这是歧义丛生的长篇叙事所难以企及的”。她发觉,“尽管纷呈的表象一直让我着迷,我却并没有流连于此,而是更乐于从中概括抽象”。所以,无怪乎她钟爱波德莱尔和19世纪的象征派诗人,也对20世纪法国超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作品青睐有加。《染血之室》中充满了大量的形象、象征和能指。然而,颇为有趣的是,这本故事集真正的童话教父,两位法国人,却都生活在更为久远的年代。
第一位是夏尔·佩罗(1628—1703),他所编著的传统童话故事集《往日的故事或传奇》于1977年被卡特译成英文出版。卡特在序言中称赞了他“完美的技巧和他善意的嘲讽”,并说,“从这位善良、宽容、好心肠的法国人的作品中,孩子们可以学到颇具启发的利己心……此外,还可以得到许多乐趣”。
接下来的另一位法国人,就是马奎斯·德·萨德(1746—1814)。对萨德作品的阅读,以及对其长达十年的批判,给她早期的两部作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两部作品分别是《霍夫曼博士可怕的欲望机器》(1972)和《新夏娃的激情》(1977),而她那部狂热的萨德色情作品格言录《萨德的女人》,和《染血之室》同出版于1979年。当《萨德的女人》遭受指责时,她振振有词地宣称,“我真看不出来,把男人对女人最堂皇的幻想都发掘出来有什么不妥”。这本书既艰涩又挑衅,言辞激烈的序言副题为“为女性提供的色情文学”——而对于许多同时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将一直是饱受争议之作。
这本书中有一句洞若观火的箴言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染血之室》中的故事,那就是,逆来顺受本不是什么美德——而事实上,尤其是当这种品质出现在——女性身上的时候。“朱丝蒂娜标志了一种关于自我的女性自虐倾向的开始,女人在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地位,反抗之心被自怜自艾日益吞噬,”卡特如是写道,并把玛莉莲·梦露也算作萨德的这位女主角朱丝蒂娜的后裔之列。另一段话或许可以看作为《染血之室》所写的一段题词:
作为欲望的对象而存在,也就是被动的存在。
所谓被动的存在,其实就是在被动中死去,也就是,被杀死。
这就是童话故事关于完美女人的道德训诫。
《染血之室》里的故事源于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的本性并非一成不变,人是可以变的。这些故事中最为精彩的一些段落就是对变形的描述。想想《师先生的恋曲》结尾部分,野兽就被美女变成了人形——“当她的嘴唇碰触到那些肉钩般的利爪,爪子缩回肉囊,她这才看出他向来紧紧攥着拳,直到现在手指才终于能痛苦地、怯生生地逐渐伸直”;或是另一则孪生故事《老虎新娘》,这一回,是美女被野兽变了形——“他每舔一下便扯去一片皮肤,舔了又舔,人世生活的所有皮肤随之而去,剩下一层新生柔润的光亮兽毛。耳环变回水珠,流下我肩膀,我抖抖这身美丽毛皮,将水滴甩落。”这些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仅解放了生物形态的桎梏,还挣脱了历史与观念的樊篱。“在《染血之室》里,有一篇故事叫作《爱之宅的女主人》,”卡特曾说,“故事的一部分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小说的电影版。影片中……那个女人,一个很被动、十分沮丧的女人,她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鸟儿是只会唱老歌呢,还是说,它也能学会唱新歌呢?’我们有没有本事唱出新歌来?重要的是,要是我们真没这种本事,那最好还是停下来吧。”
《染血之室》,这篇标题小说中那个未命名的第一人称女主角起先看似是朱丝蒂娜式的处女祭品,身着白衣,等待献祭时刻的到来。但在叙事的过程中,她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最终逃脱了背负的命运,——作为一名女受虐者的生活——当然,这之前经历了种种诱惑的一一考验。这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法国,怀抱在海水中的圣米歇尔山上的一座城堡里。这一点,和萨德笔下食人的敏斯基,和他那座建有行刑室、藏着掳获的处女、湖水环绕的城堡颇为相似。
这篇故事也是佩罗故事集中《蓝胡子童话》的另一个版本。在蓝胡子的故事中,新婚妻子打开了丈夫城堡中的禁室,发现了所有被杀死的前妻的尸体。佩罗的道德寓意在于女性的好奇心会导致可怕的惩罚。尽管在当时的法国,女人死于生产实属寻常,而五分之四的鳏夫都会再娶。这里,血迹斑斑的房间或许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视作子宫的象征。而在卡特这篇20世纪的新版本中,威胁并非来自生产的风险,而在于两性恋情中的阴暗之处,虐恋和致命的激情。
除此之外,《染血之室》还以惊人的技艺重塑了19世纪后期的法国。卡特声称,若没有伊萨克·戴那森的范例,这部选集中的故事就不会是现在这副模样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故事都是19世纪小说的仿作,和她的一样。”这些小说(她在别处写道)的“结构高度程式化,分为开端、中间、结局,在意象的运用上也有很强的视觉连贯性”。显然,这一评价对《染血之室》这篇故事而言也恰如其分,同时,也和伊萨克·戴那森《七则哥特传说》中精心构造的故事一样,读来就像一篇训诫小说。
“我希望为这个故事营造出一种浓郁的世纪末气氛,”卡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和一种独特的风格……利用短篇小说强有力的措辞,让读者半推半就地进入这个邪恶、诱人、致命的世界中去。”这是,她继续说,“特意向柯莱特所致的敬意。”这个无名无姓的十七岁女主角穿着一身校服,下面是哔叽裙,上面是法兰绒短衫,像极了柯莱特的克劳戴恩系列小说中的那位女主角克劳戴恩,而在故事中那个无名丈夫的身上,也多少可以看得到柯莱特第一任丈夫,那位放荡轻浮的威利先生的身影。
引人注目的是,几乎卡特所有的作品中都充满了引文和典故——为《染血之室》作注可以花上你五年的时间——不过,这篇故事中的用典尤为丰富。可以称之为一座由各种符号、典故和线索精心建造的大厦。马奎斯(当然是指马奎斯·德·萨德),是位邪恶的唯美主义者,一个酒色之徒,戏仿角色,戴着单边眼镜,留着络腮胡子,好拿糖栗子和温室花朵作礼物,尤其喜欢从波德莱尔和萨德那里掉几句书袋。他在城堡的墙上挂着莫罗、恩索尔和高更所画的亡妇们,还听瓦格纳(只听《崔斯坦与伊索德》的序曲“爱之死”);抽着“粗如婴儿手臂”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牌香烟;书房里堆满了各色虐待情节的插图版色情书,而城堡主塔的小房间里全是些肢体残缺的死尸和记录在册的各式虐待刑具。
在这篇口味浓重的小说中,马奎斯散发着香料与皮革的味道,就像“俄罗斯皮革”香水,文中提到了不下六七遍,故事终了才发现原来这味道来自“剥下的皮和排泄物”。芳香的百合,有如“蛇头一般,带着丧葬的阴霾”,散发出“娇嫩的肉欲”,出现了九次,肥大的茎就像“肢解的手臂”。诸如“献祭”、“刺刑”、“受难”和“牺牲”这种词汇也如同主题一样,反复出现。不过,稍嫌突兀的是——对某些批评家来说,是有些太突兀了——在这个中篇故事的最后两页,她的调音师突然出现,把子弹送进了马奎斯的脑袋,解救了受害者——我们的女主角,让她免遭斩首的厄运。她的命运并非不可改变。如今,她发现自己的未来变得不同了,她逃脱了那个老故事,正在学习唱一支新歌。
接下来是三则猫的故事。如前文所述,头两篇是美女与野兽的变形。卡特乐此不疲地尽情描绘着皮毛、织物和白雪覆盖的景色。要是说她善于描摹表象,多少有些贬义,就像是在说她肤浅一样。但这样说绝不是这个意思,她对表象的描画,就像高文诗人那般擅长。“我确实事无巨细全都写了下来,以飨读者——希望他们像读寓言那样来阅读,”她这样说,不过,“我也努力让这些表象看起来有趣……这样一来,如果你不打算把这些读作一整套象征的话,也大可以不必这样读。”的确如此,你可以完全无视这些故事中的思想,而单单是色彩纷呈、生动鲜活、感性艳丽的语言,加之引经据典、俏皮的笑话、跨文化的指涉、时髦的警语,仍可以让人不忍掩卷。
第三则猫的故事,《穿靴猫》和之前的两篇全然不同。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故事,它会十分有趣,简直是妙趣横生,”卡特如是说。她最近的两篇小说,《马戏团之夜》和《聪明的孩子们》中那种粗俗挖苦的语气就源于此,而由哥特风格转向明确地表达善意,也始自于此。这篇故事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小镇贝尔加莫,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各种原型和笑料都被用于实现默剧效果,性也变得淫秽下流荒唐可笑,年轻的恋人办起事来,在地毯上翻云覆雨,因为床铺已经被年老昏愦的丈夫,胖大鲁先生的尸体“占据”了,因为他一脚绊在了猫的身上,从楼梯上跌下来摔断了脖子。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这只猫,巧舌善述,尤其擅长含沙射影,主要依靠修辞问句和感叹来推动故事。语言中混杂着拉丁式的铺陈和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直白:“我径自进行净身,秉持猫族无懈可击的卫生习惯舔舐屁眼,一条腿高高跷起像火腿。”
接下来的三篇故事,位处本书的中间,和其他故事略有不同。这几篇故事中,恋人们都是致命的,传统的浪漫模式足以置人死地,而性更是导致死亡。《精灵王》并非源自童话故事,而是来自德国的传说,讲的是一个邪恶的妖魔,在黑森林中游荡,引诱迷途之人走向死亡的故事。故事中对森林的描写如画家般精细,点缀着各种植物的名称,以及对角度、光线的描绘。如此众多观察入微的细节累积下来,赋予了作品一种针脚细密有如织锦般的质地——迥然不同于后文那种分明的黑白红色的对比。《雪孩》不过一页纸那么长,寥寥数百字,但从某些方面来看,不啻为全书最惊人的一篇,譬如故事中的乱伦强暴,杀戮般的性争夺。这篇故事源自白雪公主童话的一个不同版本,虽然格林兄弟也记录了下来,却决定不予出版。这一版本中,白雪公主的出生源于父亲的欲望(而非广为人知的版本所言,是来自母亲的欲望)。“我们看到的……是想象的创造,和心愿的得偿,”卡特在其1990年为《悍妇出版社童话故事集》所写序中谈到,“这也就是为何童话故事松散的象征结构会为心理分析的阐释方法如此大开方便之门。就好像童话故事并非正经的创作,不过是众目睽睽之下做的偶然之梦。”《雪孩》就有这样一种梦境般的气氛和象征,故事里的穴洞灌满了鲜血,哭泣的伯爵哀伤地强暴了死去的女儿,然后送了一束长着利齿会咬人的玫瑰给自己的妻子。
《爱之宅的女主人》又是一篇不同的故事,这是一篇特兰西瓦尼亚的吸血鬼传说故事,而非童话。这则故事最先是作为一部广播剧《女吸血鬼》(首次播出是在1976年,所以这则故事的写作时间可能比本书中其他故事的时间都要早,卡特曾说这本书大部分都是她在谢菲尔德大学时所写,从1976—1978年间,卡特在那里担任艺术委员会委员)而出现的。卡特,作为安妮·莱丝吸血鬼小说的热心读者,曾说过,创作广播剧的念头是她正闲坐着打算工作,用笔在散热器上划来划去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又尖又长的指甲在鸟笼的栏杆上刮出的那种声音。”她觉得自己必须砍去杂乱芜杂的部分,要把这部剧重新写成个故事,于是,这个故事就“变得更精炼,更多地关注故事本身,更少关注它的杂音,语调上也更连贯了”。
最后,是三篇截然不同的狼人故事。虽然不同,但同是源自《血红帽》的故事,借鉴了几个世纪流传的不同版本,围绕着狼人、老妇人和小姑娘这三个形象,进行的改编、再编。《狼人》的篇幅短小,内容残暴,语言冷静而简洁。女孩砍下了狼的爪子,却发现那其实是自己奶奶的手;老女人被人当成巫婆用石头砸死。“现在,小女孩住在外婆的房子里,过得很好。”故事的结语与性无关,只关乎生存。《与狼为伴》篇幅较长,不那么阴郁,风格上也更华丽。故事的第一页是关于狼的一篇艺术气息浓郁,又十分风趣的论文,“人形的肉食性动物”,充满了生动的狼人轶事。这种描述延续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然后,血红帽的剧情才真正开始。
《与狼为伴》在反复修改,并增添了额外的一些剧情后,最终被搬上了电影银幕。影片制作人内尔·乔丹回忆说,“她所写下的——基本就是对这个故事的改编——远远不够一部电影的长度。我建议她把这个改写成一个套盒的结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安吉拉笔下更多的故事和主题结合在一起了。”卡特喜欢叙述的衍生发展,林中的岔路,红鲱鱼,等等。同样,在她的小说中,这样的画面也深深地吸引着她。但,与此相对,《染血之室》中的这些故事,鉴于它们的童话渊源,相对来说,还是保持了线性发展的故事进程。
就这样,《与狼为伴》的故事进行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血红帽的情节出现了。在佩罗为人熟知的版本结尾,她上了大灰狼的床,被一口吞进了肚子里。“和陌生人说话,你还指望会发生些什么呢,佩罗尖刻地评论,”卡特在译本的序言中写道,“且不要绞尽脑汁去琢磨虐恋的迷人之处如何神秘。我们必须在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学会去面对它。”不过,在《与狼为伴》中卡特所要做的,正是去理解这些神秘之处。在这篇故事的最后,血红帽拒绝再害怕(她“大笑起来,她知道自己不是任何人的俎上肉”),再感到恶心(她要给狼捉虱子,还要“在野蛮婚礼”上把虱子吃掉),最后香甜地酣然睡去,身边躺着如今已是“温柔的狼”。
最后一篇,《狼女艾丽斯》又回到了哥特的王国中,回到了狼人公爵幽暗的大宅中。这篇故事也借鉴了一则较早的中世纪与血红帽相似的故事《狼口余生》,讲述的是一个被狼奶大的野孩子的故事。这一次,又出现了对动物本性的厌恶,对虱虫丛生的排斥,重构了一幅“初始的伊甸园,当夏娃和发出咕哝哼声的亚当蹲在长满雏菊的河岸互抓毛皮里的虱子”的画面。当狼人公爵中了弹受伤之际,狼女艾丽斯温柔地从他的脸上把血与尘舔舐而去,救了他。
血从脸上被舔舐而去的画面又把读者带回了《爱之宅的女主人》中,年轻人亲吻吸血鬼的伤口,却不经意杀死了她的那一幕;也让人想起了《老虎新娘》的结局,同样的舔舐带来了新生和兽毛;这又让人想到《与狼为伴》中那个“心中长着毛发”的男人。这篇故事集中充满了这种音乐般的回响——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死亡和处女,套盒结构层层相扣的形象——同时,像“贞洁之星”,或是“染血之室”这样的词汇,在不同的故事里,重复性地间或出现。肉,裸露的肉体,毛发,雪,月经,镜子与玫瑰(长满獠牙的,或其他模样的)的图像,反复出现,如赋格一样贯穿始终,赋予这些故事一种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尽管各不相同,它们的手法和措辞却是相互贯通的。
1980年,也就是《染血之室》出版一年后,卡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短篇小说并非是简约抽象的,它是洛可可式的。让我感觉一切尽在掌控。就像是在写一出室内乐,而不是创作交响乐。”她的语气中显示了自豪兴奋和一种精于此道的感觉。这部故事集将会吸引到更广泛的新读者。《染血之室》让她从民间故事中发现了崭新的领域,也探索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杂糅方式,正和她自己无法归类的天赋相得益彰。从今往后,她的作品将为世界所关注,而她,也将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
海伦·辛普森,2006
用户评价
从主题探讨的深度来看,这本书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类型小说范畴。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悬疑或惊悚的故事,更像是对人性深层结构的一次外科手术式解剖。作者勇敢地撕开了文明社会构建的脆弱外衣,直视了恐惧、贪婪和道德沦丧的本质。我尤其留意到他对“记忆”和“真实”这两个概念的反复叩问。在书中的世界里,你永远无法确定眼前所见是事实的映像,还是被扭曲后的残像。这种哲学层面的思辨,让我不得不停下来反思我们日常赖以生存的认知框架。这种文本提供的思考空间,是很多纯粹追求娱乐性的作品所不具备的,它让你读完后,依然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地回味和咀嚼那些深刻的意象,思考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和存在主义困境。
评分这本书对氛围的营造达到了令人赞叹的境界。与其说是在阅读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在体验一种持续的、挥之不去的心理状态。作者非常擅长利用环境来烘托人物的心理状态,光影、声音、甚至是气味,都被他编织成了一种无形的网,将人物和读者一同困在其中。你几乎能想象出,那些在昏暗走廊里行走的角色,脚下踩着吱嘎作响的地板,耳边只有自己沉重的心跳声。这种高密度的氛围感,使得每一个看似平淡的场景都充满了潜在的危险信号。它不是那种靠突然的尖叫或血腥场面来惊吓人的作品,而是通过一种缓慢渗透的、对未知和宿命的恐惧感,最终形成一种深植于潜意识中的不安。读完合上书本时,那种长久挥之不去的阴影感,证明了作者在构建这种“场所精神”上的成功。
评分故事情节的推进,如同迷雾中循序渐进的灯光,初看之下,线索纷杂,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让人感到一种近乎窒息的压抑感。作者似乎非常擅长描绘那种潜藏在日常表象之下的暗流涌动。他笔下的人物,没有绝对的黑与白,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无法摆脱的阴影和矛盾的动机,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去审视和推翻自己最初的判断。尤其是高潮部分的转折,简直是神来之笔,它不是那种突兀的、为了制造震惊而设计的反转,而是基于前面所有细微铺垫的必然爆发,如同山洪暴发前的溪流湍急,合乎情理又震撼人心。我甚至好几次放下书,闭上眼睛,在大脑中重新梳理一遍逻辑链条,试图理解那些角色在极端环境下的抉择逻辑。这种需要高度脑力投入的叙事方式,恰恰是我最欣赏的文学类型,它挑战读者的智力和情感的接受度。
评分语言风格的运用,展现出作者极高的文字驾驭能力。整部作品的文风是内敛而富有张力的,它不像某些作品那样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采用了一种精准、冷峻的笔调,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像是经过精心打磨的刀锋,直指核心。在描绘场景时,作者的笔触冷静得近乎残酷,却又能精准地捕捉到人物内心最微弱的情绪波动。比如对某个特定环境——比如一个常年不见阳光的地下空间——的刻画,那种湿冷、霉变的气息几乎要穿透纸面,让我的皮肤都感受到了一阵寒意。这种“少即是多”的写作哲学,使得那些关键的、爆发性的情感描写更具穿透力。读起来,你会感觉到作者在控制着叙事的节奏,时而拖沓缓慢,如同凝固的时间,时而又如疾风骤雨,让人喘不过气来,这种节奏感令人着迷。
评分这本精装书的封面设计简直是艺术品,那种深沉的、带着某种古老气息的色调,让我一拿到手就忍不住反复摩挲。装帧的质感非常扎实,一看就是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那种。我特别喜欢纸张的触感,不是那种廉价的光滑,而是略带纹理的哑光,墨水的印刷清晰有力,即便是那些细微的批注和边缘的装饰图案,都处理得极为考究。书本的开本选择也恰到好处,拿在手里既有分量感,又不会笨重到影响阅读的流畅性。我通常偏爱在安静的午后,泡上一杯热茶,伴着窗外洒落的阳光,慢慢翻阅这样的实体书。那种油墨散发出的独特香气,混合着旧日图书馆的气息,是电子阅读永远无法替代的体验。每一次翻页,都像是在进行一次庄重的仪式,预示着即将进入一个完全沉浸的世界。从物理层面来讲,这本书的制作水平达到了我收藏中顶级的标准,完全配得上它所承载的内容的厚重感。
评分商品不错 还会继续支持京东的
评分完美的故事吸引人好好看,京东活动非常赞,一次入了好多书;非常值!
评分比较特别的一本书,值得一读
评分很好的作品,值得一读
评分这是一个纯粹以民间传说和童话为素材的集子,是蓝胡子、美女与野兽、小红帽、白雪公主等故事主题的多重变奏与盛大交响曲。
评分超级棒!爱这本书!
评分严韵,台湾女诗人,译者,伦敦大学戏剧研究专业硕士。《焚舟纪》是其翻译代表作,曾获台湾十大翻译好书奖。出版有诗集《日光夜景》。
评分冲着经典去的
评分是从精怪故事开始关注安吉拉卡特的,这个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更有作者自己加工过的文学色彩,书很精致,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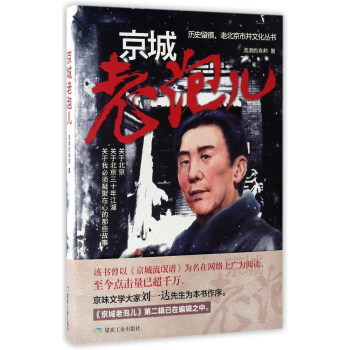
![异形:走出阴影 [Alien: Out of the Shadow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57020/58d2278eN18c7e5e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