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英国,有一种说法认为,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今世界英语表达优秀的人之一。他的思想表述和修辞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力量,他的语言充满了复杂的张力和隐喻。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可以看作是特里?伊格尔顿的思想传记,对我们了解特里?伊格尔顿复杂又充满争议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海报:
内容简介
特里·伊格尔顿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小说家和戏剧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不受时代思潮约束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由于他的干预,使得一种枯燥乏味而又墨守成规的文化变得有生机起来。他的笔锋,就像他的学术同仁哈罗德·布鲁姆、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所熟知的那样,是犀利和不留情面的。这卷包罗广泛的访谈集,涵盖他的个人阅历以及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的发展过程,既生动又深刻。不仅会吸引那些对伊格尔顿本身感兴趣的读者,也会吸引那些对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思想史、社会学、语义学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现状感兴趣的群体。
作者简介
特里·伊格尔顿(1943- ),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系,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1964-1969)、牛津大学(1969-2001)、曼彻斯特大学(2001-2008),兰卡斯特大学(2008-),并在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享有客座职位。精彩书评
★伊格尔顿是见闻广博的、风趣的和睿智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在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文化批评家中首屈一指。
——《卫报》
★一位好战的、言辞激烈的与诙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国家》
★作为英国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批评家,甚至跨越了F.R.利维斯。
——《独立报》
目录
致谢序言
一、索尔福德/剑桥
二、新左派/教堂
三、个人/社会
四、政治/美学
五、批评/意识形态
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七、理论/实践
八、牛津/都柏林
九、文化/文明
十、死亡/爱
结论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索尔福德/剑桥
可以首先谈谈你的家庭情况吗?1943年你出生在索尔福德……
我出生在索尔福德,这座城市中少有的令人感到愉悦的地方之一,我家就在荒郊边上,一个世纪前那里曾是曼彻斯特宪章运动者的聚集地。我们很穷,家里的房子是租来的,很简陋;房东恃强欺弱,总想把我们赶出去。不过,跟我们那些住在市中心的穷亲戚比起来,我家那儿的空气要好得多,景色也很宜人,尽管我们都没钱。我父母是第一代爱尔兰裔英国人。也就是说,我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都是爱尔兰人,外祖父母来自爱尔兰共和国,他们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共和主义意识;祖父母来自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我7岁的时候就会唱一些很老的爱尔兰起义曲,有一次还坐在巴士车顶上放声高歌,但还没唱完就被母亲制止了,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虽然无法言状,但却在心底留下了痕迹。我父亲有十二个兄弟姐妹,这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爱尔兰家庭模式。我的外祖父母一开始移民到兰开夏郡的一座工业小镇,那
是我母亲出生的地方;后来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他们不得不迁往更大的城市讨生活。我外祖母是酒吧女侍,外祖父在一家瓦斯厂工作,祖父刚好也在那里上班我父亲的家庭是非常底层的工人阶级家庭,母亲家族里的一些势利眼根本看不起他们。
我父母都接受过一部分中等教育,是有志气的工人,他们努力工作,渴望让孩子也能接受中等教育。我就读的那所小学环境很恶劣,周围到处都是查尔斯?狄更斯笔下那种肮脏可怕的工厂。我知道我必须通过11+考试 离开那里,否则将永无出头之日。考完试后我被校长告知可以去当地的一所天主教文法中学读书,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的几个解放性的时刻之一,即使我很快就意识到继续升学会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和人际交往上的压力。
我父亲15岁时就辍学了,据说本来可以去一所文法学校读书,因为家里负担不起,所以没有去成。他其实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去了当时坐落在曼彻斯特老特拉福德的英国最大的电气公司大都会威格士(Metropolitan-Vickers)上班。一开始进去干的是体力活,虽然他不太提。后来,在我还小的时候,他被提升为白领,一个级别不高的事务员。但父亲其实一直想自己当老板,他后来冒着很大的风险把自己几百磅的离职金拿去做投资,买了一个能在索尔福德的贫民区卖酒的执照。那个贫民区当时就在拆迁,现在已经找不着影儿了。总之,父亲很努力,他很高兴地当起了老板。他是个有进取心的人,做事主动,足智多谋。从阶级的角度来说,他正在向小资产阶级靠拢。但是,开店后仅一年他便因癌症去世,正好是我进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在把店面盘出去之前,母亲独力支撑了一阵子,她非常担心小店会倒闭。由于要经营小店,她几乎没有时间去哀悼死去的丈夫,葬礼结束,她便回来开店了,她无暇顾及自己的悲痛和孤独。
你父亲参加工会了吗?
应该没有。不过我想他的家族中不乏这样的历史。我对伊格尔顿家族知之甚少,尽管有一位爱尔兰族谱学专家曾经给我提供过一些信息,但我也只是知道他们多是19世纪后期的反叛者而已。伊格尔顿家族有着激进的基因。我的一位祖先马克?伊格尔顿是神父,他因为在圣坛上公然抨击当地的一个地主,被主教撤了职。讽刺的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地主是反共和党历史学家罗斯?福斯特的妻子艾思林?福斯特的祖先,而罗斯?福斯特正是我的老对手。历史再一次重演,而我只是希望这一次不是闹剧。我还知道另一位祖先约翰?伊格尔顿博士,二十几岁时家境没落,死于伤寒,当然,这跟大饥荒脱不了干系。他想谋得爱尔兰高威大学医学教授的职位,出于宗教原因被拒绝了,因为他不是新教徒。我现在在高威大学获得的教授职位算是为他报仇雪恨了。
尽管我的父亲没有参与政治,但伊格尔顿家族在政治上的激进表现在历史上却是有迹可寻的。我父亲有时候会跟我聊政治,他曾说:“我觉得耶稣基督是位社会主义者。”在那个天主教高度专制的年代,他作为一名正统的天主教教徒,说出这样的话让人颇感震惊。我父亲虽然话不多,但思维活跃,他经常思考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现象,只可惜他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讨厌待在工厂里的每分每秒。
你的兄弟姐妹呢?你在回忆录《守门人》(2001)中讲到你弟弟在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天折了,但其他的你没有提。
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姐姐安妮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她本来在利物浦大学读英文系,但父亲去世后,因为母亲需要她帮忙打理小店,她不得不转学到曼彻斯特大学,在那儿她只被允许拿一个普通学士学位(general degree)。她是个极为聪慧的女性,幽默风趣,富有演艺天分,而且很健谈,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或文学家,但现实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妹妹幸运些,她是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现在是利兹城市大学的准教授(reader)。这样看来,我们兄妹三人或多或少都与文学扯上了些关系。这有点让人吃惊,因为我父亲对文人既不理解,也没有同情。这曾导致我跟他之间有些矛盾,那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矛盾,他就早早地离我而去了。
你家培养出了三个知识分子,你能描述一下你家的文化氛围吗?是不是家里有很多的书或报纸杂志?
没有。我记得家里有一本名为《天主教婚姻:神父和医生》的书,书名有些邪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这就是我家的文学文化层次。在《守门人》中我说过,我曾让我母亲帮我买一套二手的狄更斯文集,她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到手。我都忘了怎么会想要买狄更斯的书。
《守门人》中没怎么讲你看书的事情,也没有明确地交代你爱看书的那股劲儿是哪里来的。
可能是因为一本很破旧的英国文学史,不知道我家怎么有这本书的,没人看,我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里面有专章介绍萨克雷和狄更斯,我想这些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也可能是我想买狄更斯全集的原因。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从3岁起到大概14岁都患有比较严重的哮喘,那个年代连缓解症状的法子都没有。父母一直为我的病忧心忡忡,到处寻医问药。有几次我差点儿就死掉了。这意味着我要长时间地待在家里休息,不能去学校上课,可我真的是个很认真的小孩儿,常让父母到学校把老师发的书拿回来给我看。我想这是我能战胜病魔的原因之一。小时候因为觉得自己时日无多,所以喜欢提前计划一些事情。很多书我都是躺在床上看完的,哪怕是像《马丁?翟述伟》这些看不懂的书,我也会读得很仔细。我想自己那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具体读了什么书,而是产生了对文学的热爱。
你还记得狄更斯在哪些方面吸引你吗?
我欣赏狄更斯的雄辩和活力,尽管前者是理解其作品的一大障碍。我也很欣赏他的文字功底,我从他作品中学到的幽默不是一点半点,我可能不理解他书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但我很喜欢他对人物的刻画。狄更斯是我文学道路的引路人。我觉得他极富智慧,总是能得心应手地运用那些艰深的词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反智分子。
继狄更斯之后,你又读了哪些书呢?
我母亲说她记得我说过:“小说家萨克雷比狄更斯更优秀。”她可能记错了,也可能是我故作少年老成!在某些时候,像萨克雷的《名利场》是必须读的。我不记得我是从哪里找来这些书的,肯定不是附近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充其量就是当地的一个摆设。我大概8岁的时候去借过一次书,图书管理员训斥我,说我当天就把借的书还了,肯定没有读完。
你有没有家里藏书比较多的亲戚?
没有。我甚至怀疑他们家里面是否有书。不过我母亲家族里有一部分人继承了爱尔兰的口传文化,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表演家、演员、歌手、谐星和说书人。回想起来,我似乎跟他们一样有这方面的天赋,而不是只会阅读经典文学。他们在与人交流、玩幽默和激发人的想象方面有窍门,那时我很欣赏他们的这些才能。我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些才能融进了自己的写作里,对我而言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你的这些亲戚有在教堂工作的吗?有没有人是神父?
我家的亲戚中没有几个神父,有个堂兄是,我父亲这边的家族里可能只出过一两个神父。小时候最让我心烦的一件事情就是父母都渴望我将来成为一名神父,可我不想,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我在教堂做过祭坛侍童,是个虔诚的孩子,大家都认为或者期望我能当神父,但我不想。一方面,我内心里觉得自己还不够虔诚;另一方面,是我认识到神父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你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会告诉你我想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但不是神父那种。或许我已经是一名世俗中的神父了。以前我认为神父是非常圣洁的人,后来没多久我就发现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回忆录里我提过,我曾接受修院的一个无聊透顶的宗教团体的一种可先试用、不满意保退的符咒。一也没有感觉很糟糕,但却坚定了我不再去修院的决心。这大概是我14岁时发生的事情,我在修院待了一个星期后终于逃离,包括精神上。
如果神父在你成长的那个环境中不算典型的知识分子,那么谁才算是呢?
我觉得没有人是。我生长的环境中没有人可以被当作知识分子的典范。
当时你已经注意到了知识分子这个范畴?
是的,我想我已经注意到了狄更斯所代表的那种知识分子——写作、思考。随后,我上了文法中学,那里的老师,特别是跟我现在还有联系的英文老师,他们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不过话说回来,并没有特定的知识分子的模式。你看,当年在索尔福德这样的地方甚至没有中产阶级,那里有医生,有神父,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所以我没有接触过工人阶级以外的阶级生活。即便如此,从我15岁时起,我就知道我不想成为货车司机,而要成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我那时就对左翼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十分熟悉了。说实话,我对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仍然有些不适应,就好像有的人在艰苦跋涉达成目标并获得了一定声望后,发现自己仍然开心不起来一样,我们总觉得眼前的事物不真实,我们并不属于这里,一切都好像是别人的故事
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索尔福德的天主教社区,你还接触过哪些文化?
我的父母没有什么社交活动,他们很孤立,甚至可以说是自我封闭。他们深感自己缺乏教育,跟人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没有自信,这种不自信也遗传给了我,我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太会跟人打交道,尽管我对自己的智力很有信心。很少有客人来我家,我们也很少出门拜访其他人。偶尔有几次,父母带我到索尔福德或曼彻斯特的娱乐场所去看艺术和魔术表演。我很着迷,尽管没有闻到演员化妆用的油彩味,一也不是去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RADA)看演出。住在街另一头的阿尔伯特?菲尼上了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他比我年长些,在索尔福德的另一所中学读的书,是书商的儿子,我母亲和他的叔叔交往过一段时间。阿尔伯特考上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在我家那一带是很件轰动的事情。他回到曼彻斯特后在约翰?奥斯本 的戏剧《路德》中扮演路德,我去看过。我也知道另一个从索尔福德走出去的演员本?金斯利,虽然他后来改了名字。不管怎样,我记得我父母带我去过两三次市里的音乐大厅,可能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个同事在那里的乐队里兼职吹长号。我记得自己非常着迷,尤其是对魔术,可能当时信天主教让我成了一个容易受骗的小鬼。
你什么时候克服了社交上的不自信呢?
直到中年才克服。有时还是会害羞,只是现在掩饰得比较好罢了。
虽然以前你需要克服社交上的不自信,但你给人的印象不错……
好吧。在剑桥的一些比较负面的生活经历大大加剧了我的这种不自信,现在想想,很大程度上是因我父亲的过世而造成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坐在剑桥大学人学考试的考场里,这是个太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很不幸的关联。除此之外,那个年代的剑桥也是个偏见很深的地方,能让你感受到一种社会压迫。
必须说,当时我作为一个孩子,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通过十年寒窗摆脱了贫苦的工人阶级。所以尽管我成功地脱离了原来的环境,进人剑桥,但相比之下,我的社交和情感发展是落后的,尤其缺乏为人处世的技巧。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腼腆,甚至可以说我整个青年时代都这样。我意识到自己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我的家庭没有教导我在知识分子的生活圈中如何待人接物以及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公共压力。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发展了一种幽居式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以抵御冷漠的外部环境。我获取知识的能力让我在同学当中显得比较突出,这种突出一也让我有些不知所措,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问题。
这或许是一种错觉,不过有人也许会问,你读过那么多人文类的书籍,为人处世方面应该比较在行才对,虽然这种涉及情感的东西难以言传。
是的,按道理应该如此我的父母在这方面很不擅长,这不是他们的错,很多工人跟他们一样。有句话说:“外面的世界很艰难,你不得不强化为人处世方面的情感。”但情感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
但文学作品可以展现出来,不是吗?
是的。我父母他们对此是茫然,而我是一种隐约的害怕,害怕情感外露。我成长于一种冷酷的功利主义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工人阶级边沁主义的产物。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中,一切服务于生存,文学是最不重要的活动。因此,尽管我反抗情感上的匮乏,我的情感还是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制约。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克服。在此期间,我写了一部关于王尔德的剧本,王尔德是爱尔兰人中最杰出的非功利主义者。我觉得自己对艺术、美学等的兴趣也不含功利主义的色彩,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为了一颗圣心(Sacred Heart) ,这跟培养我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工人们的梦想很现实。
讲讲这种冷酷的功利主义吧,它对你的童年影响很大吗?你在《守门人》中没有谈到这一点。
不,实际上微乎其微。我是战争时期出生的孩子,出生时战争临近结束。我父亲没能参战,可能因为当时他在工厂的工作已经跟战争有关,他是防空队员。我记得战争的废墟—奇怪的烧焦的痕迹、防空洞等。我记得这些苦难,当时很难把日常生活的苦难和战争带来的苦难分离开来
我想再跟你聊聊你童年时的政治影响。你已经谈到一些你家族的政治遗产,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呢?1950年代的时候,你关心国际大事吗,比如苏伊士危机或斯大林之死?
是的,我关心。在学校我还跟保守的朋友就苏伊士事件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我通过电台和报纸了解这些事。我的外祖父不识字,每天我都要读《每日快报》给他听。他会说:“我在货币市场上表现如何?”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作为一个青少年,我受“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en)作家的影响很大,那些人现在不是去世、老了,就是成了右翼分子。我寻找的是艺术、政治和持异议的交叉点。我想象自己是波西米亚人,虽然我是个听话的天主教男孩儿。我进剑桥前所受的影响就是这些。
不过,首先对我造成影响的政治无疑是爱尔兰共和主义。我之前说了,7岁的时候我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我记得自己还写了一些充满英雄情绪的很次的爱尔兰共和军歌曲,会让爱尔兰历史学家很不安吧。我甚至将歌词填进自己知道的爱尔兰曲调里,然后唱出来,忘了是唱给谁听了。所以,我的政治不满感一开始不是源自阶级,而是源自爱尔兰问题。注意到阶级问题是后来的事。
你小时候去过爱尔兰吗?
没有。老一代移民会满怀深情地回忆他们热爱的故土,但不会回去。我的亲戚中一也没有人回过爱尔兰。直到21岁,我才第一次去了爱尔兰,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的亚里士多德学会讲天主教左派。
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呢,你是什么时候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16岁时加人了“斯托克波特青年社会主义者”(Stockport Young Socialists)组织,不是“索尔福德青年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来自斯托克波特。他叫伯纳德?莱根,后来成为一名出众的、不可或缺的英国左派分子,当时我俩一起上学,一起参加会议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所谓极左组织,我觉得它很吸引人,我去听当地左翼工党议员的演讲,我还参加过其中的一两次辩论。然而,调整与天主教的关系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天主教有反对哪怕是温和的社会主义的传统。我是个过于有良心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向来顾虑多,我身处的状况是令人痛苦的。我在矛盾中挣扎:我从不怀疑自己接触的政治,但我不知道我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该怎么去接受它。博纳特的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当我在剑桥遇到天主教徒对我说“你说什么哪?你当然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左派”时,我觉得是莫大的解放,这说来话长。
当你在“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解决这个矛盾吗?
没有。我曾以左派分子的口吻给天主教右派出版社写过几封滑稽的信,内容都差不多,充斥着愤怒的年轻人的情绪。信中提到若干问题,尤其是核武器问题。16岁的时候,我在身上别了一枚核裁军运动(CND)的徽章到学校和教区去,惹来了麻烦,一个神父叫我拿掉。校长告诉我学校的牧师对我颇有微词,但因为这个牧师是很年轻的赫伯特?麦凯布神父,他是位激进的神学家和坚定的核裁军运动成员,所以指责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即使我才16岁,我已经隐约注意到,有一部分天主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是反对核武器的,但我不知道怎样跟他们取得联系。后来,在剑桥,我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
你参加“青年社会主义者”的会议给了你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信心,是吗?你说你只参加过一两次辩论,这是不是为了说明你的社交缺陷?
不,不。这是一个腼腆的孩子急切地想改变的故事。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开始时他们跟人交流很羞怯,后来突然在人前变得很活跃。……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以对话的形式,将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批评的任务,展现得淋漓尽致。伊格尔顿的文字充满了智慧的火花,也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但同时他又非常善于用一种亲切、引人入胜的方式来阐述,让我这个非专业读者也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书中对于“文本”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探讨,尤其让我着迷。他强调了文学文本并非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存在,而是深刻地反映并参与塑造着我们的现实。我曾经对一些理论感到望而生畏,但通过伊格尔顿的引导,我发现这些理论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这本书不仅提升了我对文学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让我更加敏锐地去观察,更加深刻地去思考。它是一种启蒙,也是一种召唤,召唤我成为一个更清醒、更独立的思考者。
评分当我第一次在书店里看到《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这个书名时,我的好奇心就被深深地勾住了。特里·伊格尔顿,这个名字本身就承载着学术界沉甸甸的分量,是那种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作品,但绝对听过他的名字的学者。而“批评家的任务”,这个词组更是激发了我对“批评”这个概念本身的好奇。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接收海量的信息,如何辨别真伪,如何理解深层含义,如何进行有意义的评价,这些都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难题。这本书的标题承诺了一个深入的探讨,一个与权威对话的契机。我设想,这不会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学术论述,而是更像一场智慧的碰撞,一场思想的盛宴。想象一下,伊格尔顿这位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著称的文学批评家,将如何剖析批评的本质,他的见解会是如何的深刻,又会如何地挑战我们固有的认知?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文学批评,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理解文化,以及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立场。
评分阅读《批评家的任务》的过程,就像是在一次思想的冒险。我曾以为批评就是挑剔,就是找出文章中的不足,但伊格尔顿颠覆了我对批评的认知。他将批评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将其视为一种对现实世界进行深入理解和介入的必要途径。书中关于“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讨论,让我对世界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伊格尔顿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了那些被遮蔽的历史和被压抑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张力与对话。他并没有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框架,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我发现,这本书不仅仅是给文学研究者看的,对于任何一个希望深入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教会我如何去辨识那些看似中立的表述背后可能存在的偏见,如何去理解那些看似遥远的话题与我们生活的紧密联系。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和吸收。伊格尔顿在书中展现出的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让我惊叹不已。他能够将文学、政治、哲学、历史等诸多学科融会贯通,并以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展现出来。我尤其对他在谈论后现代主义时的观点印象深刻,他并没有简单地批判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弊端,而是深入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我们理解现实的影响。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文学批评远不止于对文本的表面分析,它更是一种介入社会、介入现实的强大工具。伊格尔顿的对话方式也极具启发性,他并非在自说自话,而是充满了互动和回应,仿佛真的在与一位充满求知欲的读者进行交流。这本书鼓励我去思考,去探索,去挑战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它让我明白,真正的批评并非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是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
评分拿到这本书,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想看看伊格尔顿是如何构建这场对话的。这本书似乎并不遵循传统的学术著作的线性结构,而是以一种更为自由、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展开。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会停下来,反复咀嚼其中的某些观点,仿佛置身于一场与伊格尔顿本人促膝长谈的场景。他的语言风格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充满了一种接地气的智慧,即便讨论的是深奥的理论,也总能用通俗易懂的例子加以阐释。我特别喜欢他对于“意识形态”的解读,这不仅仅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议题,也是理解当代社会运作的关键。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隐藏在日常表象之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所接收的信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它不仅仅是关于“批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如何批评”,以及为什么批评如此重要。它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批判精神,让我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而是渴望主动去分析、去质疑、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解。
评分读圣贤书,所谓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评分悲剧是自由与命运的搏斗。造成悲剧的是宿命论,是个人无法抵抗的毁灭,是自由意志无法避免的必然。他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无知;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道主义对人类脆弱性的视而不见。悲剧是命运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宿敌。启蒙运动带来人的无限拔高,将命运、神的操纵统统抛弃身后,启蒙是对神话的去魅,然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却带来神话的复魅,启蒙的结果不过是由理性代替了从前的神意,科学代替了预言,神经生物学、社会学则是命运在现代社会的伪装,悲剧告诉我们无论多少世代,命运依然存在,悬在命运头上的,是一种冷漠的公正。
评分非常好,下次还会买,哈哈哈哈哈好!
评分这个商品太好了, 非常喜欢~继续支持京东~~!
评分伊格尔顿区分了悲剧的两种层次,一种是作为对当事人的悲剧和一种作为旁观者的悲剧。当一个人在车祸中失去双腿时,这宗悲剧对于旁观者的我们和对于当事人的他是两重意义。我们悲怋,叹息,但对于他则是一种摧毁性的打击。伊格尔顿说,当我们面对一出出悲剧时,很不幸,我们的感觉只能是前者。生活的悲剧只能由个人的身体去亲自体验,而不存在于文本之中。
评分吴藕汀《孤灯夜话》里有戚继光一则,曰戚继光,通过买美姬送张居正的手段从而飞黄腾达,生活奢华,人品低下,西湖边不应该建他的塔。余觉甚为迂腐可笑,戚乃王阳明心学传人,知行合一,若他不知道审时度势,岂有后来的一番作为。
评分读圣贤书,所谓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评分此书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的著作,涉及面逛,并使其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成为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家,也由此使人类学这一学科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米德带着这些问题去到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此书有价值,值得一读。
评分吴藕汀《孤灯夜话》里有戚继光一则,曰戚继光,通过买美姬送张居正的手段从而飞黄腾达,生活奢华,人品低下,西湖边不应该建他的塔。余觉甚为迂腐可笑,戚乃王阳明心学传人,知行合一,若他不知道审时度势,岂有后来的一番作为。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腹语师的女儿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38179/54c702c0N5ef09654.jpg)
![白天鹅儿童文学书系·猫的旅店:马嘉恺幻想电影院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8843/5555cb65N0a880fbc.jpg)

![第七条猎狗:30年纪念珍藏本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01521/5667cdfbN243630c1.jpg)
![特种兵学校7:—兵临城下 [7-11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04521/5644552cN0efd12cd.jpg)


![你一定没听过的神秘动物故事·科幻系列:狂野的未来动物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58868/569e13bfNa6ccdde0.jpg)
![小巴掌童话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06634/573acca6N438320f6.jpg)
![哈姆雷特 [Hamle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09992/574271e2N41f099bd.jpg)

![七彩童书坊:上下五千年 上(彩图注音版)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42368/5775dc5bN5d7908b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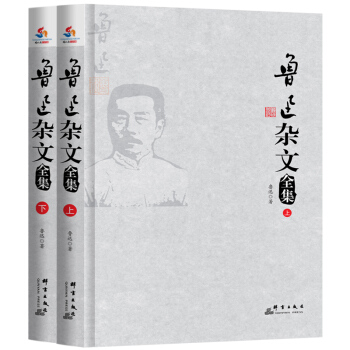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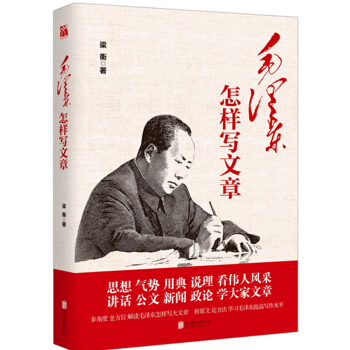




![儿童注音美绘版:四大名著(盒装 套装共4册)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15363/583fc7dcN1900247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