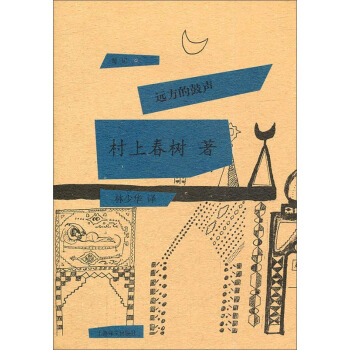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远方的鼓声》是村上春树自1986年10月开始旅欧三年期间的游记性随笔集或随笔性游记。“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作者听得的微乎其微的“远方的鼓声”,最终成了您手头上这部可触可观的《远方的鼓声》。内容简介
《远方的鼓声》是村上春树的游记,时间为1986-1989年,游历地区为欧洲,主要为希腊、意大利两个国家。村上的游记具有个人特色,他几乎不写人所熟知的名胜古迹,而是与普通居民共同生活,描写他们的日常工作、饮食起居等,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富有深度感,对读者了解这些国家的真实状况有很大帮助,文笔也幽默有趣,可读性很强。
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日本著名作家。京都府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目录
远方的鼓声——写在前面罗马
罗马
两只蜂——乔治和卡洛1986年10月4日
蜂飞了1986年10月6日星期天午后睛
雅典
雅典
瓦伦蒂娜
斯派赛斯岛
抵达斯派赛斯岛
海岛淡季
老港
缇坦尼亚电影院的深夜
来自荷兰人的信、岛上的猫
斯派赛斯岛上小说家的一天
暴风雨来了
米科诺斯
米科诺斯
港口和范吉利斯
撤离米科诺斯
从西西里到罗马
西西里
南欧跑步情况
罗马
比拉·托雷克里
凌晨3时50分的昏死
去梅塔村途中1987年4月
梅塔村
春天的希腊
帕特拉斯的复活节周末和对壁橱实施的大屠杀1987年4月
从米科诺斯去克里特岛、浴缸之战、101号酒宴大巴的光与影
克里特岛的小村庄和小旅馆
1987年,夏天和秋天
赫尔辛基
马洛内先生的房子
雅典马拉松和退票还算顺利1987年10月11日
雨中的卡瓦拉
卡瓦拉驶发的客轮
莱斯博斯
佩特拉(莱斯博斯岛)1987年10月
罗马的冬天
电视、意武疙瘩汤、普雷特
罗马的岁末
米尔维奥桥市场
隆冬时节
伦敦
1988年,空白年
1988年,空白年
1989年,复原年
康纳利先生的公寓
罗马停车种种
蓝旗亚
罗得岛
春树岛
卡尔帕索斯岛
选举
意大利的几副面孔
托斯卡纳
雉鸠亭
意大利的邮政
意大利的小偷
奥地利纪行
萨尔茨堡
阿尔卑斯的麻烦事
尾声——旅行结束
文库本后记
精彩书摘
《远方的鼓声》:对不起,接下来还是谈疲劳的文章。两只蜂——乔治和卡洛继续出场。我将结合对星期天下午波各赛公园的描写讲述他们究竟如何发生的。也有就作者本身所做的一点点思考。
乔治和卡洛仍在我脑袋里飞来飞去。但我尽量不想它们,努力想其他事,尽量。毕竟今天是星期天,大好的天气。
我在波各赛公园的草坪上坐下来晒太阳。喝着从货摊买来的橙汁,一个人呆呆看天,或打量周围的男男女女。虽说已届10月,可是热得就好像夏天卷土重来。人们戴着太阳镜,揩额头的汗,吃冰糕。有在长椅上偎在一起的情侣,有脱去衬衣赤身裸体仰卧着享受日光浴的小伙子,也有放开狗独自在树阴里静静休息的老人。两个修女坐在喷泉前面聊了很久很久。
到底聊什么呢?身穿战服样式制服的警察(或宪兵)挽起衣袖,肩上斜挎着甚是不合场合的来福枪从我身旁走过。很有可能被19世纪印象派画家选为题材的平和、亲切而纯净的周日光景。
一个看上去年龄十四五岁的美少女头戴红色骑马帽、牵马朝马场那边走去。她的脚步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时间的存在。世上偶尔是有人以那种方式走路的,简直就像时间本身在行走。刚才最后一响是ll时35分40秒。
“哔——”,11时35分5JD秒——便是如此走法。她收敛下颌,挺直腰背,聚精会神地行走,绝无矫揉造作的样子。她十分怡然自得地、如时间本身一样流畅地沿着公园甬路往马场走去。
广场上,一伙人想放大型热气球,却因某种缘故放不顺利。三四个人手忙脚乱调整器械,其余人显得有些无聊。这么切近地目睹热气球还是第一次,不过并非什么令人动心的劳什子,至少滞留地面时相当乏味。人们拼命折腾,但气球偏偏鼓不起来,就好像硬被叫醒穿衣服的肥胖的中年女人,浑身瘫软,显得老大不高兴,时而不耐烦地扭一下身体。
一条大狗从旁边经过。狗忽然止步不动,看了一会儿气球,看得十分专心,仿佛寻思这是什么呢。可是谁也不肯告诉它。再看也看不出名堂,狗径自离去。
离我坐得位置不远的地方,一对年轻男女紧紧抱在一起接吻,吻得非常之久非常之认真。半看不看地看人接吻的时间里,觉得自己本身也接起吻来。吻了很久很久,久得让人担心窒息过去。他们,以各种角度、各种激情、各种姿势吻个不止。就好像剪辑得恰到好处的学术性记录片,动作紧凑地变换姿势,兴致勃勃地展示接吻的变化之妙。他们幸福吗?我倏然心想,如果幸福,那么要求人那般接吻的幸福究竟具有怎样的形状和特质呢?最大的问题是我实在太累了。
为什么累到如此地步呢?不过反正我是累了。至少写小说写累了,这是我身上最大的问题。
我打算四十岁之前写出两本小说。不,与其说是打算,莫如说非写不可。这点极其清楚。然而我还没能着手。写什么以及怎么写也大体心中有数,但没能动笔,不幸。甚至觉得如此下去很可能永远写不出来。况且脑袋里有蜂“嗡嗡”飞个不停。吵得要死,想东西都想不成。
脑袋里又有电话铃响起。那也是蜂发出的声音的一部分。电话。电话响。“叮铃铃铃铃铃铃”。他们向我提出种种要求:为电子打字机或什么物件做广告、去哪里的女子大学讲演、为杂志彩页做拿手的“料理”、同某某人对谈、就性别歧视环境污染死了的音乐家超短裙卷土重来发表评论、担任某某音乐比赛的评审员、下个月20日前写出三十页“都市小说”(所谓“都市小说”究竟为何物?)……并非我有多么生气。当然不会生什么气。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已然被决定的事项,我不过被包含在那里面罢了。不是谁不好,也不是谁错了。
这我晓得。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那种情况的一个帮凶。说起来相当曲折相当啰嗦,总之我在那上面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所以我没有权利为之气恼。
应该没有的,我想。给我打电话的,也是我自己。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双重性让我心烦意乱,让我徒呼奈何。
无奈感——疲劳大概是从那里涌出来的。在那里,出口是入口,人口是出口。任何人都不能从那里走出。那里笼罩在凉瓦瓦的昏暗之中。作为夜晚则过于明亮,作为白天则过于黑暗。被这奇异的昏暗包拢之时,我势必迷失方向和时间。我已不明所以,不知到底什么正确、什么错误。
电话铃依然响个不止:叮铃铃铃铃铃铃。稍顷,一只蜂飞进我的脑袋。不管怎么说,蜂们喜欢疲劳的气味,一瞬之间即嗅出它的位置。喏喏,这里有美味疲劳脑浆!旋即一针扎下,使之鼓囊囊闷乎乎膨胀起来。
正因如此,我才离开了日本(不能不离开,我再次明确认识到)。但即使是在这罗马,我的疲劳也没终了,却穿越八小时时差和北极圈延续了下来。而且蜂一分为二,成了乔治和卡洛。疲劳如油汗腻乎乎沁出肌肤。去哪里都一回事,他们对我说。无论跑多远都一成不变,嗡嗡嗡嗡嗡嗡。哪怕你跑去天涯海角,我们也会紧随不舍,所以你一筹莫展,归根结底。你将在一筹莫展的时间里年届四十,就这样变老变衰。
没有谁喜欢你这个人的,往后越来越糟。不,不对,我说,往后我会好端端写小说,消失的倒是你们。
即使那样,乔治和卡洛开口了:我俩也迟早要回来的,回到你这里。
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循序渐进,来日方长。没有谁喜欢你这个人的,大家都要憎恨你。写小说也什么作用都起不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罗马。
沐浴着夏天一般灿烂阳光的午后的罗马。我“骨碌”一下歪倒在草坪上悠然望着马、人、云絮等缓慢的动作,心想假如两千年后今日的罗马像庞贝那样彻底化为遗迹该有多妙:诸位,那是楚沙迪(Tmssardi)遗址,这是华伦天奴(Valentino)遗址,那边展柜里的是美国运通金卡……女孩仍在牵马前行,看上去她像要直接融入雾霭之中。身穿和刚才不同的制服的两个警察吃着雪糕走来,沿路走了过去。他们对热气球几乎毫无兴致。喷水池的水柱喷得高多了,顶端倾珠泻玉,炫目耀眼。
热气球还是升不起来。那三个人依然手忙脚乱地拧拧螺丝或者看看仪表,然而看上去根本没有升空动静,尽管是气球升空最好的天气。
午后1时45分,到天黑尚有不少时间。
……
前言/序言
这是村上春树自1986年10月开始旅欧三年期间的游记性随笔集或随笔性游记。“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作者听得的微乎其微的“远方的鼓声”,最终成了您手头上这部可触可观的《远方的鼓声》。
兴之所至,刚刚译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捧起了余秋雨先生的《行者无疆》和《千年一叹》。同是旅欧游记(,《千年一叹》包括中东),同是拥有庞大读者群且依然走红的东方当代作家,两人笔下的欧洲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结果发现,找出二者的相同之处比找出其不同之处不知困难多少倍。这是因为。,第一,秋雨先生是带着历史去的,每到一处,首先凭吊历史遗迹,抒怀古之情,发兴亡之叹,探文明之源,观沧桑之变。而村上对各类遗址和出土文物基本上不屑一顾,他感兴趣的更是眼前异国男女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和日常性行为模式及其透露的个体生命信息。第二,秋雨先生是带着中国去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看什么,总忘不了将异邦和故国比较一番,有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意识或士子情怀。而村上基本上把日本潇洒地扔去一边,“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第三——这其实是先决原因——两人身份不同、任务不同。秋雨先生两次都是受香港凤凰卫视之邀,考察“人类历史上所有产生过整体影响的文明遗迹”,而村上纯属个人行为,不挂靠任何公司任何组织,自己掏腰包带着老婆想去哪就去哪,既非走马观花的游客又不是安营扎寨的居民,“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
例如,同是第一次到罗马,秋雨先生当即诗兴大发,由衷感慨“伟大”一词非罗马莫属:“只有一个词……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行者无疆》)村上则懊恼地断言:“罗马是个吸纳了无数的死的城市,所有时代所有形式的死尽皆充斥于此。从凯撒的死到剑客的死,从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罗马史连篇累牍尽是关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议员若被宣布荣誉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设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开血管,一边畅谈哲学一边悠然死去。”(《凌晨3时50分的昏死》)当秋雨先生神色凝重地面对元老院废墟反复解读罗马如何伟大的时间里,村上百无聊赖地坐在公园草坪上看修女、看警察、看美少女、看热气球、看狗,还看人接吻:“离我坐得位置不远的地方,一对年轻男女紧紧抱在一起接吻,吻得非常之久非常之认真。半看不看地看人接吻的时间里,觉得自己本身也接起吻来。”(《蜂飞了》)旅居罗马两年多时间里,印象最强烈的是罗马无所不在的小偷扒手之流。村上的太太也被抢走了挎包(包里有护照、机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一个开摩托车的年轻男子从后面赶来,一把抓住她的挎包带。她本能地握紧不放,大约持续了三十秒。尽管周围有几十人之多,但都往别处看,佯装未见,不愿意介入,作出浑然不觉的样子。互相抢夺了一会,最后挎包带断了,男子拿包离去。众人这才如梦初醒地来到她身边,七嘴八舌安慰道‘真不得了啊’、“啊请在这儿坐一下’、‘我给警察打电话去’、‘那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这种时候的意大利人又可谓亲切之至——嘴皮子上的亲切,倒也容易。”此时此刻,村上到底怀念起祖国日本来——东京断不至于有如此表演。
再说一下希腊。当秋雨先生面对爱琴海立有很多洁白石柱的悬崖峭壁沉思埃斯库罗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至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时候(《千年一叹》),村上则对着海滩游泳女郎“朝着初秋太阳挺起的乳峰”,认真总结“爱琴海规则”——“具体地说,来到爱琴海以后,(A)女孩子心想反正是爱琴海,这么做理所当然,遂以习以为常的手势暴露乳房;(B)男人也做出视而不见的神情,就好像说毕竟是爱琴海,那么做也无所谓一当然,偶尔也会用眼角斜瞥一眼,但即使那种时候他们也显得从容不迫,仿佛在说这东西见得多了。此乃基本规则,从容才是至关重要。”(《海岛的淡季》)如此说来,秋雨先生一定活得愁眉苦脸而村上一定活得一身轻松了?却也未必。“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思考人与人关系。”(《千年一叹》)在人际关系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这点上,同为东方人的秋雨先生和村上似乎颇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感受,这点双方在书中都按捺不住。旅欧期间村上写了《挪威的森林》,书很快出版。“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他最后概括道:“罗马充满罗马才有的麻烦事,东京充满东京才有的麻烦事……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只能和麻烦事相伴而行,同麻烦事一起生存。”(《意大利的小偷》)不同的是,秋雨先生归结于“中华文明的杂质”,村上则概括为自身的“经验教训”。
以上所言,纯属兴之所至,并不是想就两人的游记作品进行系统性比较。何况二者在时间上至少相差十年——尽管欧洲十年间变化不会很大——且两人旅途所花时间也长短有别。但不管怎样,对比着翻看几页确是一件颇有兴味的事。
村上在他的书中最后这样写道:“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或许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惟独自己听得见的远方的鼓声,一如小时候在乡下每次听到山那边传来的演戏或扭秧歌的鼓声,心里就怦怦直跳急着出门。人生途中的每一阶段都会有鼓声在远方呼唤自己整装待发,声音再弱我们也会听见,即便不是在“安静的午后”。
林少华2005年2月25日于青岛·窥海斋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它不像许多 contemporary fiction 那样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句式,而是以一种返璞归真的姿态,用最朴素、最真挚的文字,诉说着最动人的故事。然而,正是这种朴素,却拥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却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读起来,仿佛是在聆听一位老朋友在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没有矫揉造作,只有娓娓道来。每一次翻页,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画面感的世界,那些人物的表情,环境的描绘,都仿佛触手可及。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彻底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全身心地投入到书中的世界。它证明了,真正的力量,往往蕴藏在最平凡的表达之中。
评分我必须说,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远方”的认知。它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一种内心的追寻,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作者巧妙地将现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些看似平静的日常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暗流涌动?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又该如何去触碰?这本书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鼓励读者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人物复杂性的描绘,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人物更加真实,也更具魅力。这本书就像一场心灵的探险,带领我穿越了内心的迷雾,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评分这部作品给我带来的,是一种久违的、纯粹的阅读快感。它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我从现实的琐碎中抽离出来,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我被作者构建的世界深深吸引,那些鲜活的人物,曲折的情节,以及贯穿始终的深沉主题,都让我欲罢不能。每一次的阅读,都仿佛在经历一场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时而紧张,时而感动,时而又陷入沉思。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放下手中的书,迫切地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渴望与书中的人物一同经历他们的喜怒哀乐。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到,好的故事,是有生命力的,它能与读者产生强烈的连接,并留下长久的影响。它是一次令人心潮澎湃的艺术体验,也是一次自我发现的奇妙旅程。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已经足够吸引人了。深邃的蓝黑色调,仿佛是浩瀚星空下的远方,而那隐约传来的鼓声,更是勾勒出一种神秘而充满力量的意境。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被这种莫名的召唤感所吸引,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关于冒险、探索、以及内心深处的呼唤的画面。迫不及待地翻开,文字的排版疏密有致,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沉静的力量,仿佛作者在用最温柔的笔触,描绘着最壮阔的风景。每一页都像一扇窗,透过它,我能感受到远方的气息,听到那穿越时空的鼓点,它们时而激昂,时而低沉,牵引着我的情绪,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要跟随。这本书的气质,是那种能让你在喧嚣的世界里找到片刻宁静,又能点燃你内心深处那份原始的冲动,让你渴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远方。它不只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一种精神的对话,一种灵魂的共鸣。
评分读罢掩卷,心中那份久违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故事的起伏,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叩问。它以一种极其细腻而又富有张力的方式,展现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成长。那些在命运洪流中被推搡着前行的人物,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坚持,他们的迷茫,都如同镜子般映照出我们自己的人生片段。作者的叙事手法非常高明,节奏的把握恰到好处,时而如春风拂面,温情脉脉,时而又如惊涛骇浪,让人心潮澎湃。我尤其喜欢作者对细节的刻画,那些微小的动作,不起眼的对话,却往往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勾勒得栩栩如生。这本书让我深刻体会到,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内心的勇气和希望永远是照亮前路的灯塔。它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也是一次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探索。
评分远方的鼓声数量x5¥149.5
评分好看
评分东西已经收到,非常不错的商品,下次还会再来光顾贵店。
评分有塑封!好……与商品符合,全新正版品相优,京购物首先,物流很快,第二天就到货了!
评分非常不错 值得购买非常不错 值得购买
评分书不错,质量棒棒哒
评分非常喜欢村上春树的书,建议大家多看看!
评分东西不错,值得购买,感谢京东商城!
评分京东618活动,满减加抢券,合算得不要不要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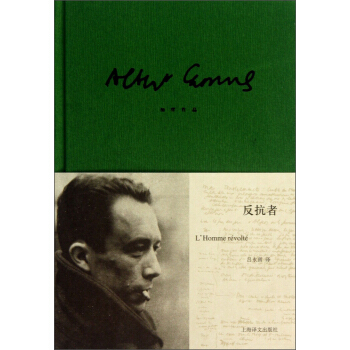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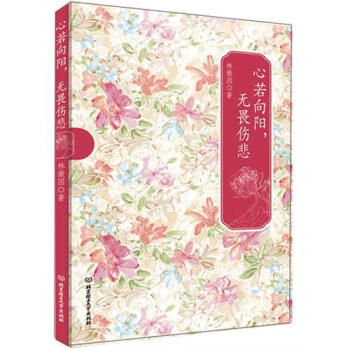
![兽王:星使降临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14206/rBEHalCkVuQIAAAAAAGHMyMKFwMAACz5gBoiZkAAYdL56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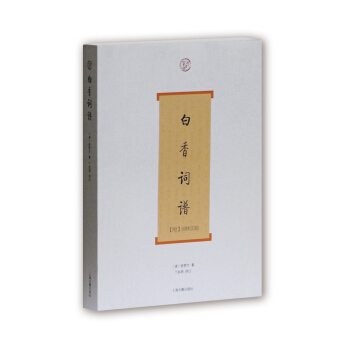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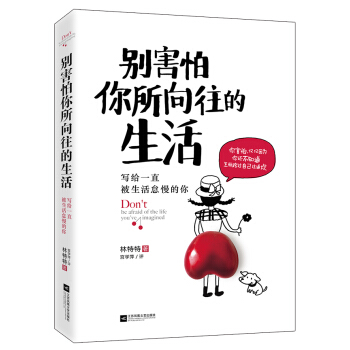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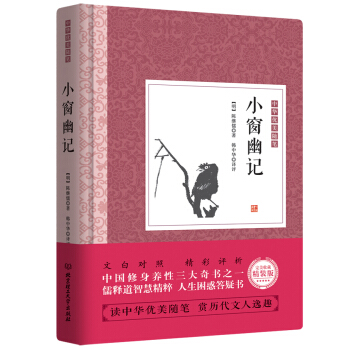
![蒙田随笔全集(套装共3卷) [Les Essais de Michel de Montaign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107428/d0894ced-b454-4f54-8448-3ce8c19e7d38.jpg)




![大个子老鼠小个子猫4(注音版)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09830/54367d93N7882736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