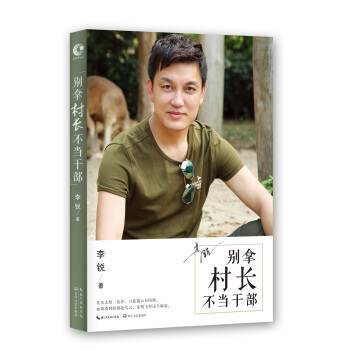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北大回忆》是北大中文系78级学生、作家张曼菱回忆北大生活(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的新作。该书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要内容,涉及北大的领导、老师、同学等各种人物,以及发生在北大或者与北大有关联的种种事件,描述生动、人物鲜活,传达了作者体验和理解中的独特北大,为了解那罕见的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以及北大的风格和传统,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材料,也可从中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书中有各种知名人物,有同学间大大小小的冲突,有作者自身性格带来的戏剧性,可读性强。
内容简介
《北大回忆》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要内容,涉及文艺界、北大领导、老师、前辈、同学等大量人物,以及发生在北大或者与北大有关联的种种事件。
作者简介
张曼菱,云南华宁人氏,中国当代知名女作家、红学家、电视制作人、社会活动家。青年时代曾在云南德宏傣家边寨当知青,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以“文科论文一”的成绩毕业,到天津作家协会做专业创作。在校期间即发表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时轰动京华,后改编为电影《青春祭》,饮誉海内外,被誉为中国大陆知青电影的巅峰之作,成为一代人心灵的丰碑。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到好莱坞进行学者访问,在美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女性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名动东西海岸。是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未曾深入新疆地区考察民间文化,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发表小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唱着来唱着去》等,名动天山南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海南创办文化企业,为海南省制作首部电视连续剧《天涯丽人》,热播全国,掀起第二次“海南潮”。获海南“开拓”奖。
近年来出版随笔集《北大才女》、《中国布衣》,风行大江南北;以深邃之笔墨记录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是为中国“布衣文化”的旗帜之作。
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其担纲制作的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深得海内外联大校友所认同,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高度评价与认可,已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此片昭示与抢救了中国民族文化史上重要篇章,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目录
序 “值得回忆”第一章 燕园春潮
“作家梦”
逝去的教授
历史的邂逅
“青青子衿”
小“段子”
试探性的讨论
燕园春潮
第二章 “隔代亲”和“守望者”
“隔代亲”
校园路
朱光潜湖畔抛书
林庚登台讲《楚辞》
金克木戏说时势
王力写推荐信
朱德熙“隔代亲”
季羡林“不默而生”
“守望者”
语法课——卢甲文
“文学评论”课——闵开德
为“朦胧诗”呐喊——谢冕
课前点评——袁良骏
曾经“流放”——倪其心
辩论《苦恋》——周强
“可以像林庚先生那样”——孙玉石
“真文字更有价值”——马振芳
相教何必曾相识——金开诚
功夫在课外——严家炎
“为了人的尊严”——袁行霈
第三章 竞选细节
闻风而动
“问答”之海
“人性解放”旗帜
遭遇“大多数革命群众”
保护《开拓》
帷幕落下、谁是“小乔”?
“照片失踪”案
喊出“振兴中华”
第四章 学子投稿
秦兆阳的小院
在韦君宜家吃炸酱面
与《当代》相处的日子
“让她到大地上去”
“活化石”马波
荒煤“老友”
第五章 勺园岁月
“蚩尤文化”
“南极梦”
《青春祭》兔年访美
花神庙、硅谷魂
“候鸟”群聚
第六章 寻觅“校园魂”
历史的链接——季羡林、郝斌
警觉“被放大”——沈克琦
“人淡如菊”——任继愈
雅“俗”之间——徐葆耕
获奖与“获罪”——王汉斌、彭佩云
曾经是“钻石”——费孝通
仁哉!科学——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
《日记》问世——吴宓及其女
坦诚与保留——台湾行(一)
校风与业绩——台湾行(二)
后记:我们这一代人
精彩书摘
第一章 燕园春潮
那是一个时代更迭的日子。
中国大地上,火车载着一批批抖落岁月风尘的录取新生,日日夜夜,从四面八方,向着大学奔驶。
到了!就是这里。
昨夜之我,还在火车上倚着一只打补丁的旅行袋,坐在硬座上摇摇晃晃,难以入眠。今日之我,已来到轩昂华丽的北大校园,成为人皆羡慕的天之骄子。
恢复高考后的77、78届学子,如春潮般涌入北大,顿时更新了整个燕园。青春在这里重新展开,细节饶有趣味。到处是勃勃生机和意味深长的邂逅。
在校园内,光明与阴影,方生未死依然纠结,但一往无前的进步,已是大势所趋。
“作家梦”
驰名中外的北大中文系,所在的五院是那么小,小得像是一户旧式人家。
五院是独一无二的。
梦中常看见五院,院墙上的爬山虎散发着盛夏馥郁。初来乍到的我们,站在小草地上,聆听中文系副主任费正刚训话:
“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费老师的话没错。中文系历来培养的是学者和教学者。在我们此前和此后,出来的人才,基本如此。
而当时,这话令我们每个人都震了一下。
站在这里的这批学子,很多人都正做着“作家梦”。
在77、78级学生进校期间,中国文学出现了大潮。一批描写“右派”和“知青”命运的作品成为主流,成为人们反思“文革”的教科书。文学,承载着苏醒的精神与反省的力量,迅猛地复盖社会,使得中国社会的开放改革,及时地获得了新生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我们“文学78”这个班,以及“文学77”,实际上都是以“发表率”来论英雄的。
当时,我们班比“文学77”差得太远了。他们的“发表人次”高达三百多。刚入学,他们就有“五大才女”,记得是:黄蓓佳、王小平、李志红、查建英等。
黄蓓佳已经出了短篇小说集。她衣饰妍美,时而佩小首饰,烫发,风韵温婉,在我们这两届素衣女生中,很眩目。中秋节,她与袁行霈老师出现在央视的赏月节目中,可谓风情占尽。
现在活跃着的“小查”,当年头发扎成双丫,高个儿,天真样。而门头沟煤矿来的作家陈建功,一派成熟,群雄之首。
一个“五四文学社”,77、78级是主力。
中文系迎新晚会后,系里的人“名符其实”地认识了我。
因为在晚会上我登台唱云南民歌:《绣荷包》、《小河淌水》。同学伯陶为我胡琴伴奏。在那个朴素的带着拘泥的晚会上,尚且陌生的人群中,我的乡野之音引发了一阵掌声。
早上两节课完,跑进图书馆,已是到处满员。我叹口气,拎着书包正要走,一位男生抬起头来:“我让你,我有课。”他站起来收东西。
走时他扔下一句话:“你的民歌唱得真好!”
那天,五四文学社的社长李志红来宿舍找我,我很高兴。可原来她是来请我去“唱堂会”的。五四文学社的茶话会安排节目,我就到那里给人家唱民歌去。
写作还没有找到路子,唱歌倒唱出名气来了。
有一天下午,我回到宿舍,见到一位高大和悦的男生正在与舍友悦和莎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说:“人家学生会主席登门来请你去唱歌呢。”
来人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说:“我是孟晓苏。”
多年后,我们曾经在海南相遇。孟晓苏告诉我,他正在运行“股份制改革”。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往往有从政的前景。
我在乡下当知青“野学”时,读过一点美学的书,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一类。一进五院,我就去找“美学教研室”,楼上楼下跑遍了,找不到。
我即兴写就一篇《哀高丘之无女——中国的美学到哪里去了?》,交给“文艺理论”课的闵开德老师了,我那气势好像就是声讨他一样。
闵老师把我这篇东西拿给中文系书记吕良,吕看后说了一句:“张曼菱,罗曼蒂克!”他是与我的“唱歌”结合起来看的。这话传出来,人们可以感到,一个宽和的时代开始了。
在五四文学社的刊物《未名湖》第一期,我有一首诗发表。大意是讲,一个青年即将被捕,他遥望着女友的窗口告别。没有人知道,这是我的亲身感受,也是我当年在那种情境中写就的。
那一期《未名湖》,我们是骑着自行车出学校去卖的。每人一捆,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面。
走的时候,系里专门叮嘱:“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不要反抗,也别吵架,到那里就静静地等着,学校会来领你们。”有人还带上了英语单词本,准备到公安局去“背单词”。
金秋时节的北京,黄爽爽的秋叶铺满林荫大道,配着琉璃瓦、红墙、白塔,显出华丽高贵的气派。
仰头,可见秋树删繁就简,天空澄澈。
这么干净利落的换节景色,我的家乡没有。昆明“四季无寒暑”,气质混沌温和。
那次去大街上卖刊物,没有什么人来抓我们。我们都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人们见了油然起敬。
沿街叫卖“非正式刊物”的这番经历,学校的这种交代,让我们领略到了“北大学生”的特殊身份:我们是有些自由的,我们的自由是受保护的。我们得创造一些新鲜的东西来,超前于这个社会,回报于我们的身份。
至今我保存着《未名湖》1980年第一期。打开它的卷首语《给八十年代》,在那泛黄的纸页上,学子的壮心依然令人激荡:
上溯八十余年的岁月,未名湖似乎并非风月宝鉴。它卷过多少浓云密雨,掠过多少刀光剑影啊!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蓄’,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李大钊传播马列主义,伟大的五四运动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历史在它上面的折光,真是灿烂晶莹,奇异夺目。我们在这样一块土地上耕耘播种,的确是得天独厚的。为此,更使我们感到惶惶不安,我们很可能有负于我们的前人而愧对今天的读者。
可是,这一页历史毋庸置疑地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受任于两个时代的更替之际。七十年代给予我们的感受和教益,是我们对八十年代认识的出发点。我们对八十年代充满希望,充满憧憬,充满热情。但是,我们是冷静的,沉着的,踏实的。
封面是黑色的,以白色线条划出地平线和日月,鲜红的三个字“未名湖”为茅盾所题,封底是木刻。这样的设计,有点模仿“五四”时代那些启蒙先驱的刊物。
这一期上,白桦的诗歌以长者的口吻说:“因为你们非常年青,或许可以少受很多罪。但道路仍然很不平坦,愿我们都像屈原那样‘虽九死其犹未悔’!”
……
前言/序言
序:“值得回忆”
2007年11月进京,参加在清华园举办的西南联大七十周年纪念,携所编撰之《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到“五棵松”,探望季羡林先生。
先生说,“这事很有意义”,指我多年来在做的寻访联大校友口述史一事。
接着他问我:“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说,“只有零星文章,没有完整地写过。”
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
我问先生:“怎么写?”
答曰:“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我顿时有些白云深处的感觉。我和他都一时沉静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
他突然对我提及的《浮生六记》,那一部是贵在心灵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
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
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
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
其实他一直想回校园。
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那天相见,季有一段话令我伤感。他说:“那年我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当时杨锐秘书在旁问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说:“(一九)五七年。”
我与杨不禁相视莞尔。那时候我还在童年。
敏锐清晰的他,开始对岁月模糊了,而牵念之情油然。
他对杨锐说:“拿纸来。”遂写给我一幅字:“为善最乐,能忍为安。”这令我感到他晚年的无奈。“忍”这个字,听起来不是那么舒畅。他写道“赠曼菱”。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先生从来不会写错,他心中有我。
翌年夏日,远在西南的我收到挂号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四字,连写两遍,他已为我的未竟书稿题词了。
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有他深邃的智慧。这段岁月对于北大和整个社会都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来年,风雨如晦,光明时现。我有幸与北大结缘,聚而不散。散而又聚。知我者,先生也。
每一次见面,他都要求我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说,“曼菱要能坐下来,必能成正果”。“坐冷板凳”,其实正是季羡林的本分,本色 。
由于校园反复动荡,季羡林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 还在朗润园家中时,有时一天不断地来人,这样持续着,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板凳”的时间。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羡林全集》。
季羡林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为主。这在他的《学海泛槎》一书中一一作了交代。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
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符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国学’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关于名誉,他曾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实至名归。”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床榻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陪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咸菜。 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份量。
这样的温馨时刻,从他离开朗润园的家后,再也不复有。
当大学与“考试选拔”制度在文明古国中断达十年之后,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又提出了“择优录取”的原则,这意味着古老的民族又恢复了它的传统与生机。
那数千年在中国大地上川流不息、滚滚向前的人才洪流又开始集结和流动。龙的脉博跳动着,民族的希望和生机,随着这股年青的人才洪流在集结涌动,流向一个“为国所用”的渠道。大陆中国重新构建它的信心。
到1978年,高考制度不止是“恢复”,而且取消了建国以来各种所谓“政审”以及各种“政治推荐”等等藩篱,只以“分数”,作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透明的尺度来招生。
如果只是延续建国以来的培育制度,像我,和许多人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有很多“潜规则”阻拦我们进入第一流的大学。
我的祖上曾经“一门五进士”,至今家乡立有“进士碑林”。当“登科”之事到我,却百味遍尝。所谓的“政审”,其实罗织无中生有的罪名。用父亲的话说:“不是怕你考不好,而是怕考得太好了,却上不了。受刺激啊!”
在我们那个时代,进入北大的人有那么几种:平民考生是完全靠着出类拔萃的分数;还有一些已经具备基层干部的阅历,当过小领导的;高干子弟有一批,经历过大劫的他们很是朴素和低调。而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还在学校继续读完他们的那一年。
每天学子们匆匆忙忙,汇成往来于校园中的貌似“划一”的大流。这形形色色的人群带着大地的泥土,带着豪门的坎坷,带着书香的曲折;有机巧,有朴拙,有潜志,有执着;为了民族的同一个理想而混同,数气相搏,风起云涌。
精英由此生成,人脉由此贯通。
那个年代铸造了我们这批人,也铸造了我们与耄耋之年的校园学者们的跨世纪之情。
季羡林所说的“像《浮生六记》那样写”,“浮生”者,不只是说生命之短促,更指这生命不系于任何重物。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这种欣赏与角度,十分接近于我的父亲。
上月我到京时,有人送来一个珍藏的书画匣。展开后发现,竟然是我父亲书写的一幅字:“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 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 托父代书”
来人说,这是受季羡林之托,一定要在他逝世后,交代到我手里的。
时光忽然倒流,想起了当年我离昆之时,父亲拿出一张写好的宣纸,郑重地说:“你要我写的字,写好了,我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羡林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又是别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当年我把这一幅毛边的宣纸送到季先生桌前,向他说明了没有裱的原因,季沉默了,用手抚摸着这纸,喃喃地说:“不易。我自己裱。”
那一天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幅。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
如今父亲和季先生都走了,这幅字却回到了我手边。它已经被精美地装裱过,色泽淡雅,收藏于锦匣之中。来人说,季羡林在若干寿礼中,只取了这一幅字画收存,装裱后就挂在他的小书房中。直到临终前,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给我。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我带着它又回到了昆明。在这幅字中,在这件事里,季先生的灵魂与我的布衣父亲,他们都超越了世俗,同去了一个独立精神的归宿地。
还是“像《浮生六记》”,贵在心灵之自由。恬淡之中,隐藏了多少不愿从俗的辛酸。风雅之下,留取了一根纤细的书生傲骨,显示了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和功利的飘浮。
父亲在我“大一”的时候来过北大。在未名湖畔拍照时,他特意摘下帽子,秋风吹乱了他的额发。这是一个边地知识分子对北大的敬仰之情。
父亲逝后,他的老友之漠伯伯说:“你考上北大,是对你父亲今生最大的安慰。”
父亲一直很想知道北大的种种,想知道我的学习生活的所遇所感。然而女儿总是一付天之骄子的模样,语焉不详。
父亲辞世一个年轮了。
写此回忆,也算是不孝之女当年没有回答父亲的一份“补卷”吧。
2013年10月21日 昆明
用户评价
说实话,一开始拿到“北大回忆”这本书,我并未抱有多大的期望。我以为它不过是一本泛泛而谈的校园回忆录,充其量能带来一些消遣。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却被书中那种不动声色的力量所打动。它没有激烈的语言,没有夸张的修辞,却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深沉的情感和一种对过往的眷恋。我并非北大的校友,也与那个年代的校园生活相去甚远,但书中所描绘的那些场景,那些人物,却能够激起我内心深处某种共通的情感。可能是对青春的怀念,可能是对知识的敬畏,也可能是对那个时代那种纯粹精神的向往。这本书,更像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它将那个时代的记忆,那些人物的情感,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传递给后来的读者,让我们得以窥见一段不曾亲身经历却无比珍贵的历史。它让我反思,在如今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保留着那份对知识的纯粹追求,那份对理想的执着坚守。
评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读到“北大回忆”的那个夜晚。窗外夜色渐浓,室内只有一盏孤灯,而我,则完全沉浸在那字里行间。这本书,与其说是在讲述一段具体的经历,不如说是在勾勒一种精神的轮廓。它没有浓墨重彩的戏剧冲突,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更多的是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温润如玉的叙述。我仿佛能看到那些身影,在未名湖畔漫步,在百年讲堂里聆听,在实验室里挥洒汗水,在宿舍里彻夜长谈。那些面孔,或许稚嫩,或许坚毅,但都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憧憬。书中的语言,不似时下流行的那些快餐文化,它有着一种淡淡的诗意,一种对过往的眷恋,一种对岁月的敬畏。它没有刻意去渲染悲伤或喜悦,而是将那些细微的情感,那些转瞬即逝的思绪,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来,散发出一种内敛而持久的光芒。读完这本书,我没有感到强烈的震撼,却有一种淡淡的怅然,仿佛自己也曾是那个时代的一员,而今,物是人非,只留下无尽的回味。
评分那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我偶然在书店的角落里瞥见了它,书名是“北大回忆”。没有华丽的封面,没有吸引眼球的标题,只是一种朴素而沉静的气质,像一位历经岁月的老友,静静地在那里等待着。我拿起它,指尖滑过书脊,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我虽然不曾亲身经历过那段青葱岁月,但“北大”这两个字本身就承载了太多我心目中的理想与憧憬。翻开扉页,那熟悉的校徽,那略显泛黄的纸张,瞬间把我带入了一个充满书卷气和青春气息的世界。我无法预测这本书里会讲述怎样的故事,是关于深夜的图书馆,是关于辩论台上的唇枪舌战,还是关于青涩的爱情萌芽,亦或是学术探索的艰辛与喜悦。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一段珍贵的时光,一段属于许多人的共同记忆,也可能是一段能够点燃我心中对知识、对理想的向往的旅程。我迫不及待地想走进这个故事,去感受那份属于北大的独特韵味,去聆听那些无声的诉说,去理解那份在时光中沉淀下来的情怀。
评分“北大回忆”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阅读的乐趣,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独特的风貌,也映照出那些年轻的心灵是如何在那个熔炉中淬炼与成长。我并非一个对历史或教育有着特别深入研究的人,但通过这本书,我仿佛窥见了中国高等教育曾经的辉煌与坚守。那些前辈们,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年代,依旧能够保持对学术的热情,对真理的追求,这种精神力量,足以穿越时空,触动人心。书里对人物的刻画,没有脸谱化,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他们有各自的困惑,有各自的坚持,有各自的成长轨迹。正是这些鲜活而立体的形象,构成了“北大回忆”最动人的部分。我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更是时代变迁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的命运,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忧思与欢喜,共同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赞歌。
评分这本书,我是在一个连绵阴雨的日子里读完的。窗外的雨声,似乎与书中描绘的场景产生了奇妙的共鸣。那是一种略带忧伤,却又充满力量的氛围。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于细节的捕捉,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片段,却往往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和深刻的寓意。比如,一段关于集体食堂的描写,就能勾勒出那个年代人们的朴素生活和同志情谊;一段关于课堂笔记的描述,就能展现出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和认真的态度。这些点滴的汇聚,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时代图景。读“北大回忆”,我没有感受到任何说教意味,而是完全沉浸在一种叙事之中,仿佛化身为其中的一个旁观者,静静地看着故事 unfolding。它没有试图去定义或评判,而是将那些往事,那些人物,以一种最自然、最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感受,去思考。
评分挺不错的一本书,值得推荐。
评分作者讲述我有多牛逼的故事
评分崔永元亲笔题词,致敬普通口述者和口述史从业人员
评分不错的书,很有内容,慢慢赏读。
评分还没看,帮朋友订的。装帧印刷都很好。
评分快递很好,书也很好!
评分慢慢看,一定会有收获的。
评分好像你是不是我好好、
评分在书店看上了这本书一直想买可惜太贵又不打折,回家决定上京东看看,果然有折扣。毫不犹豫的买下了,京东速度果然非常快的,从配货到送货也很具体,快递非常好,很快收到书了。书的包装非常好,没有拆开过,非常新,可以说无论自己阅读家人阅读,收藏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的说,特别精美;各种十分美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但也不遑多让,塑封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绘图都十分好画让我觉得十分细腻具有收藏价值。书的封套非常精致推荐大家购买。 打开书本,书装帧精美,纸张很干净,文字排版看起来非常舒服非常的惊喜,让人看得欲罢不能,每每捧起这本书的时候 似乎能够感觉到作者毫无保留的把作品呈现在我面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曹文轩说故事:一只叫凤的鸽子 [3-7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5061/55487b73Nbdce5702.jpg)


![遗忘 [10-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78705/5530b1c6N3528a70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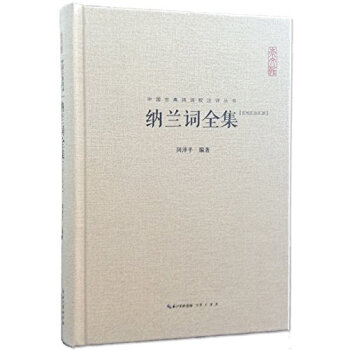



![为你,耶路撒冷(精装) [O,Jerusale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72710/583bff1fNb981776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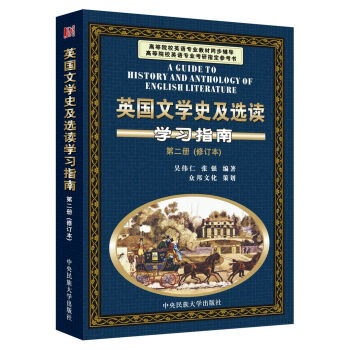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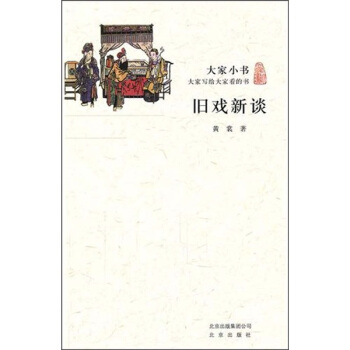
![小米的便便商店 [2-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02078/55d42b7eN56bb5b14.jpg)

![国际大奖小说系列:铅十字架的秘密 [11-14岁] [CRISPIN: THE CROSS OF LEA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06196/rBEhV1HD-ugIAAAAAAdfTbRKTR0AAAaZwBxPbcAB19l338.jpg)
![意林小小姐淑女漫绘馆:紫阳花之夏(第2季)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49608/rBEhWFHBYckIAAAAAAUFLwpa40EAAAWtQHMolUABQVH93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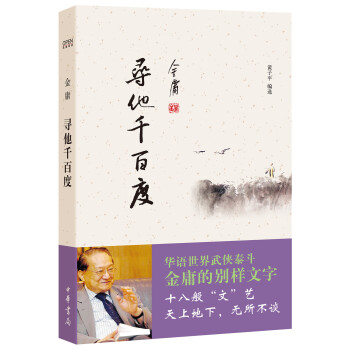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青少版:地心游记(新版)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1968/rBEbRVNrVx0IAAAAAAoheeQ8yGgAAAWngCmqIcACiGR80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