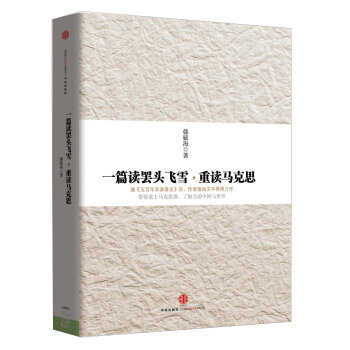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是在一部风靡北大、清华的马克思课讲义的基础上润色而成。·韩毓海继畅销书《五百年来谁著史》后,激扬文字再推力作,带你重上马克思课,了解当前中国与世界。
·韩毓海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和解剖刀,深刻解剖中国几千年来经济与金融困局的动因,以及西方世界债务危机的根源。
·知名经济学家李稻葵、胡鞍钢、李玲等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与金融革命的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漫长历史,重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中国千年兴衰的动因,并就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金融改革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作者韩毓海用平实、生动甚至略带犀利的笔触,援引马克思著作中的精彩部分,充分解读了马克思对当今世界社会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危机的成功预测和判断。针对马克思的三部作品《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者引导读者沿着马克思的足迹解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货币、债务、道德、信用等,并反思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剖析有哪些现实指导意义,从而鞭策现代人要想看懂并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就要回归马克思。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纽约大学访问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计划。并获得第九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七届上海文学奖、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书一等奖等。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名列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总榜**名,并收入《中国高层领导荐书集萃》。《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获评“2012-2013年度全行业****书”。
精彩书评
今天,对真正有头脑和良心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什么工作比向人民群众普及金融知识更为重要,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无疑是一个光辉的典范。
—— 纽约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 廖子光
在《五百年来谁著史》力作之后,韩毓海以不同于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的全新视角诠释100多年前马克思经典著作,并以此剖析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经济金融现象。此作值得心怀理想、关心当前经济金融大势的广大读者阅读并珍藏。
——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 李稻葵
韩毓海重新拿起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和显微镜,剖析债务驱动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发展症结,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命题。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胡鞍钢
韩毓海以中国学者的气度和胸怀,以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的自觉,澄清马克思,还原马克思,回归马克思。这是一部引导我们阅读经典的经典。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玲
目录
前 言第一章
“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
“金箍棒”与“紧箍咒”:债务驱动的暴力
“人”如何成为“世界货币”
文明的辩证法
反对“资本主义”不等于反对“资本”
社会主义与金融
第二章
古典经济学的“扯淡”
“批判”与“扯淡”
市场经济的起源
信用:货币化的道德
银行券:债务货币
怎样读懂《资本论》
古今兴亡多少事
第三章
“人间喜剧”
纤夫的“爱”
“召唤亡灵的行动”
“流氓无产者”与国债
小块农地的金融化
“现代社会靠无产阶级过活”
跋一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李玲
跋二 向马克思学习 胡鞍钢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资本论》第一卷第24 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部分讲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从哪儿来的,讲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我们这一讲便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产力的革命、交换的革命,而是以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为标志。
欧洲16 世纪以来连绵不息、不断升级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战争融资需求,跨国的金融信贷体系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金融”的领域独立了,“国王的债务”被货币化了,成为在银行家们之间投资转卖的财富—资本,一条“由债务驱动”的发展道路由此开辟。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正在于紧紧抓住并率先深刻分析了这条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揭示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崛起的根源、不可避免的危机,真理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限度及其与生俱来的脆弱之处。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最广为流行的舆论里面大概只有一句话庶几正确:“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即使马克思活着,他本人也会同意这句话,但这丝毫说明不了什么。相对而言,另外一种流行的舆论则是不正确的,这种舆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持此观点的人忘记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恰恰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最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资本经济学”,把它理解为“金融经济学”倒庶几接近于马克思的原意。实际上,马克思是在对“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方才建立起他独特的方法论。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采用他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方法,采用资本的语言或者金融的语言,重新叙述了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内容。“马克思的语言”使得熟悉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马克思的方法”也使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于是,经济学家们只好说《资本论》是哲学书,哲学家们则说《资本论》乃是经济学著作。而这不过暴露出现代知识最根本的缺陷与困境:哲学家不懂经济学,从而使哲学变成了玄学和空谈;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这使得经济学缺乏思想的含量,甚至变成了统计。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伊始所遭遇的最广泛的批评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叙述是“极其抽象的”,而马克思对此的回答也很著名:要分析资本和金融,靠化学试剂和手术刀、靠斯密所开创的那种“经济学家讲故事”的通俗方式是完全不行的,因为这需要“抽象力”。
今天,任何对于期货、期权交易和证券投资有一定了解的人,或许都会明白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是指什么,因为资本和金融是高度抽象的领域。华尔街已经开始雇用高等数学家和高等物理学家对资本市场进行分析,只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洞见和预言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马克思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比迄今为止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懂历史。在他看来,16 世纪地中海地区极端活跃的融资活动使得“金融”从各行各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支配性的领域,而这划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资本自我增值的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观察,把债务打包成“信用凭证”进行买卖就绝非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了不起的发明,因为早在16 世纪意大利皮亚琴察交易会上,这种把国王的债务打包成信用券进行买卖的交易,即“债券”交易,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些陈俗老套罢了。
问题并不在“市场经济”—那只不过是一个18 世纪的陈腐话题,问题在信用的垄断和滥用即“资本主义”—这才是自19 世纪以来支配世界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真正力量。由于看不懂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一种流行了500 年的东西当作“新发明”来反复地重新倡导,并徒劳地采用18 世纪苏格兰手工业行会的语言,叙述资本主义的世界,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20 世纪30 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其实就像1787 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和盐税专员的亚当·斯密一样,他们正是因为憎恨“债务型国家”—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方才热烈地倡导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因为哈耶克所憎恨的当时的奥地利政府与斯密笔下的英国汉诺威王朝统治者一样,都迷信依靠借债、发债维持财政和经济活动。因此,如果离开了对“债务型国家”的憎恨,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对于“反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倡导与呼吁。但是,弗里德曼与斯密和哈耶克的出发点都不同,弗里德曼不但是“债务型国家”的积极拥趸,他更是故意混淆了“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之间的根本区别。由于这种致命的混淆,弗里德曼的政策起初使美国的金融机构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随后则使美国的债务绑架了世界经济,最终世界经济就这样被美国的债务拖着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根本不在乎斯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之间这种本质性的区别,而只是说: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都是与马克思对立的,并简单地把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归结为“政府与市场”这种极为幼稚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西方来的,当前的学院分科体系将经济学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是完全说不通的。斯密、哈耶克与马克思在反对“债务型国家”这一点上,起码是高度一致的,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上述三人是完全对立的。
真正把经济学大师们分开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对待政府或市场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待资本、金融和债务的态度。在这方面,马克思恰是一个真正的标杆,《资本论》则划出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欧洲16 世纪那场深刻的金融革命,导源于地中海地区的私人银行家以国王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正是这个创制,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国家的国家能力,特别是战争能力。借助战争国债制度、银行券的发行及其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几个欧洲霸权国家以残暴的殖民战争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通过建立和利用国际信用体系,它们迅速完成了“欧洲对于世界的革命”,并把整个世界以“债务”和“金融”的方式联系起来。
同时,欧洲资产阶级以扩大税收和银行券不断贬值的方式,把国家的开支、战争的开支以及放债者的利润统统转嫁到欧洲大众身上,最终把他们剥夺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从而也把“欧洲对于世界的战争”转变为欧洲内部的革命。
正是伴随着战争国债制度,即以国家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这一创制,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货币交换”方才成为决定性的社会交往方式。竞争性的市场不过是竞争性的国际关系的日常化、社会化表现。
所谓议会民主、代议制均是从政府融资制度中脱胎而来,因此,如果离开了从王权国家向“债务型国家”的转变,就完全不能理解从封建贵族制向现代国家官僚制的演变,当然,也就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选举、代议政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体制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跨国金融体系的形成则是16 世纪以来欧洲战乱频仍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私人银行家的联合。
国家出于战争的目的而发行国债,私人银行家为了经营国债方才建立起以国债为基础、以税收为抵押的银行制度和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财政税收制度,正是这二者根本性地促进了货币交换的发展、“互相预付”的信贷机制的发展、国家管理制度的理性化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而根据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我们一向接受并习以为常的那种(亚当·斯密式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那种观点认为:货币交换与市场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与生俱来的“交换的偏好”, 基于人性的本能,因此,货币交换和市场早在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首先就在于:他对于货币经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富独创性的解释。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至今还被我们视为“真理”的经济学,他认为: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 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
因此,16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引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引发革命。
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特立独行地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而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他是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但很可惜,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金融制度视为产业革命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颠倒”。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以他“对经济学的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为基础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必然地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不是过时了,而是太超前了。当资本主义还戴着产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的面纱时,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在资本和融资活动主导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时代,在“金融业”取得了经济活动主体地位时,人们还固执地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分析资本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前提,这就是极为可悲的。马克思面对和讨论的“市场”是金融市场,而非此前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商品市场,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认识了前者,后者才能被真正理解。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样说: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18 世纪的话题,是手工业行会时代的话题,是小私有者和小业主们的话题;而当西方经济的发展进入19 世纪,这个问题就被金融和资本压倒一切的现象所代替了。从这个角度看,比斯密晚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倒是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他说:当前的问题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人民与银行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已经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真理一向命运不佳,这是因为从没有现成的、已经准备好的耳朵聆听它的声音,而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好的乐章也是白费的。当然,“真理的耳朵”也并不是真理的学说本身塑造和培养出来的,比如,无论晚年的毛泽东怎样要求他的同志和战友读马克思的原著,终究亦是收效甚微,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战友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真理的耳朵”只能在现实的教训和磨难中形成。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指:许多革命者其实是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把监狱当作了研究室,方才第一次系统地阅读马克思的,熟谙德文的列宁 就是如此。用鲁迅的话来说,这就是盗了马克思的火,为的是来煮自己的肉。因为历史的辩证法恰在于恩格斯所说:人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破南墙也不肯回头的驴子,正是因此,“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对于那些真正有教养的人来说,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认识到:人类只不过刚刚真正地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
渺渺大荒灯一瓠,风雨摇看近若无。每临生死需静气,石火光中可读书。
下面,就让我们从头说起,沿着历史的轨迹,与马克思一起思考。
……
前言/序言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说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店主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100。”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80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白占了地方”的“马克思”让我得了大便宜。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那棵梨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40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再到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相联系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作“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即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仅依靠改革上层与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10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市定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的改革所主攻的目标之一,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发行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互相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方才树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提高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为这需要动员全社会、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简而言之,这需要革命。
马克思极懂富强之理,马克思深谙金融和资本之道,这有《资本论》为证;而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则,因而他赞成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欧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号为证。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2008年,我在纽约与廖子光先生畅谈时,廖老曾有言:晚清以来,中国举凡财政、金融、军事、科技均落后于西方,不仅陷入国家民族的大劫难,而且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难,要寻求富强之道,什么办法都尝试尽了,结论则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历史的翻盘。直到湘潭毛润之先生出来,他能焕发中华文明的真谛,一举扭转了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因为毛先生很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近代中国除“人心”之外,再便无富强之“资本”。中国已经一穷二白,欲在如此山穷水尽的条件下求富强只能依靠“行王道”,舍此再无他法,而毛先生“发财的资本”,靠的就是唤起人民的同心同德、空前团结,来打败西方在军事、科技、财政和金融方面的优势,他有“两只手”:“一只手”是理学和心学的“大同”思想,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再到康有为、孙中山,毛润之先生是集大成者;“另一只手”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后一只手能把“王道”与“富强”在现代条件下统一起来。所以,毛先生缔造的新中国就不叫民族国家,而叫“人民国家”,他的战争便不叫“国家战争”而叫“人民战争”,他的科学教育不叫“精英教育”,而唤作“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教育,他的金融叫“人民金融”,而人民金融则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任的基础上的,这是极为高明的设计。
毛先生把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东方大国做了实践,中国最终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他开辟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实践、一些做法,固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自有其“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悲剧,但在大方向上,乃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中国学者的问题却是对美国及西方霸权和霸道之实质既了解不深,对王道传统兴趣又不大、记忆几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长,习人之强,反难免两头皆失之虞,此乃最可担忧之事。
无论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中国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出现复活官二代、封建主义、买办资本、腐败、两极分化等问题。正如历史上的中国,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国,若只求富强,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廖老一直把毛泽东主席称为“毛润之先生”,因为廖氏一族,举凡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半是国民党元老,一半是共产党元勋。廖老一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作为纽约杰出的金融家,他始终关怀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2005年,廖老便提出中国以“货币互换”抑制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以及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面向内需、面向中西部谋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风,至今记忆犹新。
关于“王道”与“富强”这个话题,我还记得20世纪末,费正清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来北大讲学时,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向他请教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的问题,他曾这样说:我们西方实行的是“霸道”,你们中国坚持的则是“王道”,1840年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终究也不能长久,现在要看看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了。与其说将来全世界都要“看中国”,还不如说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这个难题。
墨子刻教授对清代制度,特别是《大清会典》有着精深研究,他更继承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观,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他是少数“真正懂毛泽东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果然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从而为人类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吗?
2011年6月,在世界讲坛上,李稻葵教授曾经面对着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政要这样坚定地说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西方霸权主义的老路,因为我们要复兴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文明,这一文明的核心是“王道”,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变革“始于170年前开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国的失败为中国文明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屈辱,这种屈辱的教训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在学习这些教训。那次屈辱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包括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为了应对这次屈辱的一个决绝的回应。”
“我的文明教会了我,不要去压迫别人,不要强加于人,而是要与人合作;我的文明教会了我,经济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应是掠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
稻葵先生的话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当时舌战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屡仆又屡兴,慷慨期致远。道逢同心人,万里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争取一个文明、进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后继、挖山不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我们的去路,就没有什么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许,我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写完《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气把《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写完,但是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能抓住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如果不能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发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缘,无论下多少功夫都是枉然,而要抓住这样的动力、追求这样的视野,那就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方法。
我从今年9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家人警告我说,倘若再这么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此虽系笑谈,而我心自知,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别的东西吗?不做亏心事,何惧鬼叫门。何况我们的许多前人,例如写出了《封建论》的柳宗元,恰在我这个年龄就死掉了,而像马克思一样,他即使在放逐中,却毕竟也没有低下过自己的头。
本书得以顺利面世,实有赖于多方的全力帮助,今特申明三事:胡鞍钢教授命我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师生讲授此稿,由于鞍钢教授在讨论中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本书的观点更具现实针对性;李玲教授慨然推荐,其辞恳切,令我动容。作为前辈师长,他们的恩义于我,诚可谓是“动心于无情之地,施惠于不报之人,古烈尚难,况在今日”;而北京大学支持我这样一个中文系的教书先生为全校研究生开设“马克思著作精读”课,也凸显了北大学术自由的传统,故清华与北大—此应感谢者一;中信出版社为出版本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此应感谢者二;我的研究生贾嘉、陈澹宁通过录音记录、反复斟酌,把我的讲稿整理出来,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此应感谢者三。
马克思于1883年病逝于伦敦,于今130年矣。今天的我们却正处于他所预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中,而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希望这本小书能为广大读者带来真正的思想与知识的乐趣,而那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希望的。
韩毓海
2013年11月25日于北京
在线试读
第一章 “大国”是怎样“崛起”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4 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部分讲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从哪儿来的,讲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我们这一讲便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产力的革命、交换的革命,而是以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为标志。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在向你述说着一个足以颠覆你固有认知的秘密。“一篇读罢头飞雪”,这究竟是怎样的阅读体验,才能让思绪如此激荡,以至于仿佛一夜白头?而“重读马克思”,这三个字则充满了探索的意味。在信息爆炸、观点多元的今天,为何还要“重读”这位经典作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过去对他的理解存在偏差,或者他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指导意义?“入选2014中国好书”的荣誉,更是为这本书增添了一份值得信赖的品质保证。我深信,一本能够被广泛认可并推荐的图书,必然具备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解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演变,以及它如何依然能够为我们分析和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深刻的启示。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自带一种古朴而又深刻的韵味,像是从遥远的过去飘来的一片雪花,触碰着我内心深处对思想与历史的求索。 “一篇读罢头飞雪”,这句诗一般的开场,立刻就点燃了我对阅读体验的好奇,它预示着这将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心灵之旅,一次足以震撼灵魂的智识洗礼。随后的“重读马克思”,则将这份期待聚焦在了那位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身上。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似乎每天都在接触着无数新的观点和理论,但对经典思想的“重读”,却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可能是一种对过往理解的修正,一种对被忽视的价值的重新发现,更是一种在经典中汲取智慧,以应对当下挑战的必要举措。 “入选2014中国好书”的评价,更像是为这本书加上了一层信任的光环,它说明这本书在内容深度、叙事方式以及对读者的启发性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我迫不及待地想通过这本书,去重新认识马克思,去理解他思想的时代意义,去探索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社会复杂性的洞见。
评分读到这本书的名字,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种强烈的画面感,仿佛穿越了历史的尘烟,与一位思想巨匠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篇读罢头飞雪”,这八个字,简洁而有力,瞬间就勾勒出了一种深刻的阅读体验,一种思想被彻底震撼、被完全颠覆的震撼感。这不仅仅是对一本书的评价,更是对一种思想的力量的赞颂。而“重读马克思”,则精准地指出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在今天,当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挑战时,重新回望马克思,意味着我们并没有放弃对深刻理论的探寻,而是希望从中找到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钥匙。 “入选2014中国好书”的殊荣,则更加印证了这本书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思想史的著作,更是一部能够触动人心、引发思考、获得广泛认同的优秀作品。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带领我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理解他思想的精髓,并将其应用于当下,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初见之下,便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和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 “一篇读罢头飞雪”,这句诗本身就足够引人遐思,仿佛在诉说着一种读史或读思的极致体验——那种震撼,那种颠覆,以至于头发都因之而白。而紧随其后的“重读马克思”,则瞬间将这份厚重感具体化,指向了那位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思想巨人。它不是一次寻常的阅读,而是“重读”,这其中蕴含了多少对过往解读的审视,多少对当下现实的关切,多少对未来方向的探寻?“入选2014中国好书”,更是为这本书盖上了权威的印章,证明了其在中国当代图书界的价值和影响力。 我拿到这本书时,心中涌起的不仅仅是好奇,更有一种责任感,似乎要通过这本书,去重新认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去理解那股曾经席卷全球的思潮,去反思它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记,以及它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一种深刻的洞察,带领我穿越时空的迷雾,与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一场真诚而深刻的对话,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自身的命运。
评分它像是一扇被尘封多年的窗户,突然被轻轻推开,让崭新的光线倾泻而入,照亮了房间里被遗忘的角落。初翻开时,那种熟悉感又带着陌生感扑面而来。马克思,这个名字,在许多人心中,或许已经固化成某种标签,某种遥远的理论,甚至某种早已过时的符号。但这本书,却以一种极为鲜活和动态的方式,将他重新拉回了我们的视野。我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专业研究者,但作为一个关心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普通读者,我始终觉得,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理解现代世界发展逻辑的一把钥匙。这本书的出现,恰逢其时,它并非是枯燥的学术论著,而是带着一种“好书”的姿态,这意味着它在思想的深度、叙述的生动性,以及对读者吸引力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我期待它能像一位睿智的长者,娓娓道来,将那些看似复杂艰深的理论,用一种易于理解,甚至触动人心的语言呈现出来,帮助我拨开历史的迷雾,看到思想的火花,进而引发我对当下现实更深刻的反思。
评分老师们暑假的精神大餐,美美哒
评分弃。不敢读这本书,开头讲马克思的理论就连带批判美帝,难以想象后面提到列宁毛泽东的篇章该如何的疯狂。本书作者的阴阳怪气捧高踩低真的有损马克思的坦荡气魄……
评分物流速度很快,图书质量也很好,很满意
评分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评分一直觉得,原版马克思不是我们课堂里那样的,嗯,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
评分东西不错,物流速度快
评分很不错的书!物流也很给力!知识给人力量
评分好书收藏一套先,经常翻翻。
评分物流快,价格合适,快递小哥服务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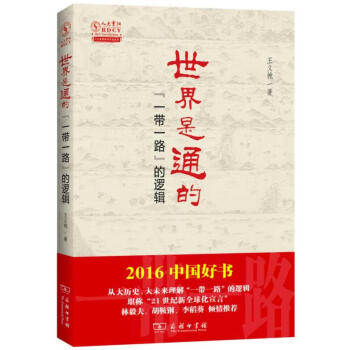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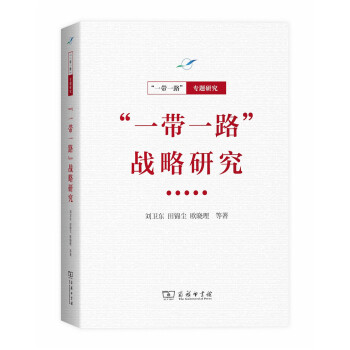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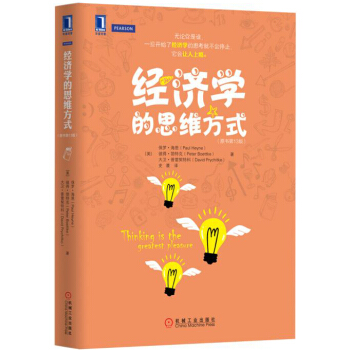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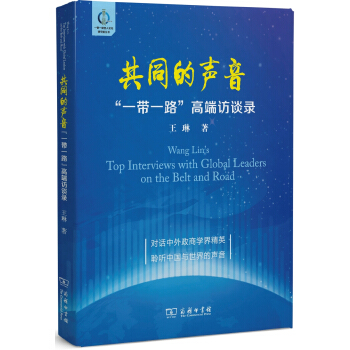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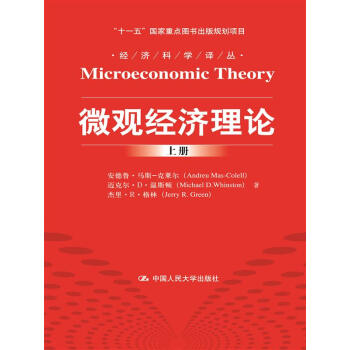
![经济科学译丛:高级微观经济理论(第3版) [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Thire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57792/rBEHZVDrga8IAAAAAAi2oZHFmxkAADjLwGNHZUACLa524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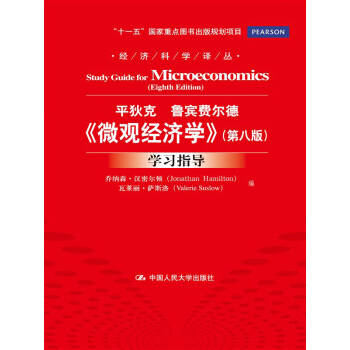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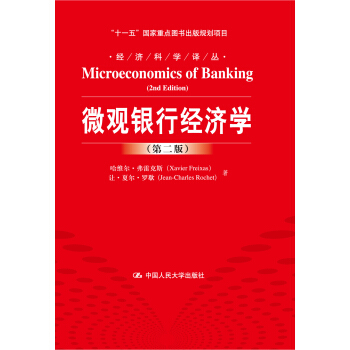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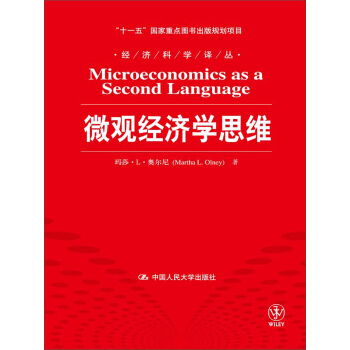

![微观经济学(第2版)/“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经济科学译丛 [Microeconomics(Second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956107/5642a1e1Nad30afb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