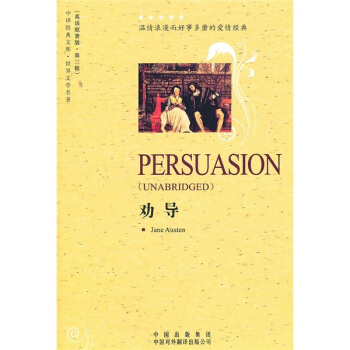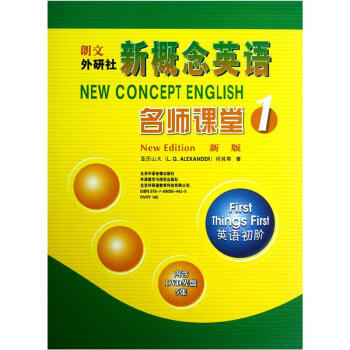![麦克尤恩作品:黑犬(中英双语版) [Black Dogs]](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37784/rBEhU1LobfwIAAAAAA3JB6cJlwoAAIRVQHZstAADckf874.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麦克尤恩作品:黑犬(中英双语版)》以其对视角转换技法的熟练运用,以及在叙事时间回放中进行的多层重构而闻名,生动地刻画了麦克尤恩的主题:我们固有的观念改变着我们看待、感受和铭记事物的方式。在《麦克尤恩作品:黑犬(中英双语版)》中,作者深入人物角色内心进行挖掘的创作手法起到了一贯的良好效果。《麦克尤恩作品:黑犬(中英双语版)》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倾向于纯粹的堕落与绝对的邪恶,以及一种危险的幸福的可能性;那两条如昏暗晨光中的黑色斑点般的恶狗,能以任何形式重新出现。内容简介
你可知道丘吉尔将与自己形影不离的忧郁症唤作“黑犬”?他曾坦言“我有一条陪伴我一生的黑犬”。胸中的阴郁、内心的折磨就像伺机发起进攻的黑狗一样,一有机会就咬住心口不放。而“恐怖伊恩”这一次狠狠揭开的却是整个时代的沮丧,唤起的是文明的心魔,揪住了人性的缺口——“如果一条狗代表了个人的抑郁,那么两条狗就是一种文化的抑郁,对文明而言,这是最为可怕的心态”。出没在长篇小说《麦克尤恩作品:黑犬(中英双语版)》中的凶狠而神秘的动物,比黑夜还要黑,目露红光,像正在燃烧的煤块,觊觎着奄奄一息的欧洲文明的残骸,吞噬着改革与信仰的道德底限,叼住了文明的死穴,企图颠倒善与恶的本质——典型的麦氏黑色,在幽灵黑犬作祟的舞台,暴力,真爱,邪恶,救赎,演绎了一则有关我们时代的惊悚寓言。目录
前言第一部 威尔特郡
第二部 柏林
第三部 马伊达内克,列-萨勒赛,圣莫里斯-纳瓦塞勒,1989年
第四部 圣莫里斯-纳瓦塞勒,1946年,1946年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琼·崔曼的床头柜上有一张镶着镜框的照片,这张照片放在那里,令琼回忆起年轻美貌时的自己,同时也提醒着她的访客,照片中那位漂亮姑娘的脸庞,不像她丈夫的那样,没人能看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张快照摄于1946年,是在他们结婚后的一两天里,也就是在去意大利和法国度蜜月的一周前拍摄的。这对夫妇挽着胳膊,就在离大英博物馆入口不远的栏杆旁边。或许这是他们的午饭休息时间,因为他们都在附近工作,而且直到距出发几天前,他们才最终获准离职休假。他们斜倚着靠紧对方,看样子都格外惦记着不要被拍到相框外面去。他们对着相机露出笑脸,透出发自内心的欢悦。你不可能认错伯纳德。他的样貌一直没变,六英尺三英寸高,手脚都非常粗壮,下巴大得有些可笑,但看上去却仍显得和蔼友善,还有那头仿军人样式的发型,使他那对茶壶柄状的耳朵显得更加滑稽有趣。四十三年的光阴只给他留下了可以预见的岁月痕迹,而且这些变化都只发生在边缘地带——头发稀疏了点,眉毛更浓了,皮肤也更粗糙了些——然而,这个令人惊讶的怪老头,从1946年到1989年(这一年他拜托我带他去柏林),在本质上始终还是同一个伯纳德,那个手脚笨拙、容光满面的大个子男人。
然而,琼的面容就如她的人生一般,偏离了预定的发展轨道,而且,当有人进入她的私密房间时,也几乎不可能从这帧快照里预见到她这张绽出满面慈祥、笑容欢迎的老脸。照片里,二十五岁女子那美丽的圆脸蛋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她趋于散开的烫发依然太紧,显得太拘谨,一点也不适合她。春日的阳光照耀在她业已松散的发丝上。她上身穿一件带高垫肩的短夹克衫,下面搭一条很相配的百褶裙——这种低调的奢华体现了战后的“新貌”服饰风格。她穿的白衬衫带有V字形的宽松领口,领口朝下越来越窄,一直大胆地延伸到她的乳沟。衬衫衣领翻在夹克衫外边,这让她看上去清新活泼,带着战时招贴画里的姑娘们那种英国玫瑰般娇艳新鲜的气质。从1938年起,她就是阿默珊姆社会主义骑行俱乐部中的一员。她用一只胳膊把手提包拢向自己,另一只胳膊挽着丈夫。她依偎着他,头还没到他的肩膀高。
这张照片现在就挂在我们在朗格多克的家中的厨房里。我经常独自一人端详它。我的妻子詹妮,也就是琼的女儿,怀疑我本性难移,对我迷上了她的双亲感到生气。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他们,而且她感到我的兴趣会将她拉回到父母身边,这一点没错。我把脸靠近照片,试图瞻望未来的生活、未来的面孔,以及在那次非凡的勇猛表现后所产生的忠贞决意。欢乐的微笑让她光滑的额头泛起了一道细小的皱纹,正好在她的眉心上方。这道皱纹后来成了琼那张老脸上最明显的特征:从鼻梁上隆起,垂直地把她的额头分成了两半。或许我只是在想象这微笑背后被隐藏在下巴褶皱里的艰辛,一种坚定的态度,观念的执着,一份对未来所抱有的科学的乐观。就在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早上,琼和伯纳德刚刚到位于格拉顿大街的英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在那里签了字,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即将离开工作岗位,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忠诚心已经发生动摇。如今,党内对这场战争的定性依然没有统一结论——这到底是一次高尚正义、为自由解放而战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侵略战争?——这种动摇让许多党员产生了怀疑,一些人还退出了党,而就是在这个时候,琼和伯纳德毅然加入了进去。
除了希望建立一个理智、公正、没有战争和阶级压迫的世界之外,他们还觉得,作为党员他们就可以与青春、活力、智慧、勇敢作伴相依。他们即将跨越英吉利海峡,奔赴混乱的北欧,虽然有人劝他们不要贸然前往,但他们仍执意要去尝试他们新的自由,无论那自由是指个人的还是地域上的。从加莱出发,他们将一路南行,去享受地中海的春天。那里的世界崭新而和平,法西斯主义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了资本主义末日危机的明证,温和的革命即将开始,更何况他们年轻,新婚,而且相爱。
虽然颇为苦闷,伯纳德仍保留着党籍,直到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他才觉得自己已经把退党的事拖得太久了。这种变心反映了一种众所周知的逻辑,代表了一段为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灭的历史。
而琼的党龄只有几个月,到她在蜜月途中经历的那次奠定本回忆录标题的遭遇为止。那次遭遇给她带来了剧变,令她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转世重生,那副面孔就是证明。一张圆脸蛋怎么会拉得如此之长?或许不是基因,而是生活,使她微笑时额头上现出的小小皱纹深深扎根,长成了一棵大树,一直延伸到她的发际线上?她自己的父母年老时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怪事。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她住在疗养院里的时候,她的脸和奥登老年时的面孔很像。或许,多年来地中海的阳光使她的面孔粗糙变形,长期的隐居与思索令她的皮肤扩张,然后又重叠堆到了一起。她的鼻子和下巴都随着脸部而拉长,然后仿佛又改变了主意,试图折回去,以弧线形式朝外生长。在她休息的时候,她的脸如斧凿一般轮廓鲜明,表情抑郁阴沉,仿佛是一个雕像,一张萨满教巫师为抵御恶灵而雕刻的面具。
……
前言/序言
八岁那年,在一场车祸中,我失去了双亲,从那以后,我就对别人的父母格外在意。在青少年时代,我尤为如此,当时许多朋友纷纷丢弃自己的父母,而我形单影只,用别人用旧的东西,倒也活得十分自在。左邻右舍,略显沮丧的为人父母者比比皆是,对至少有那么一位十七岁的青年愿意留在身边,来分享他们的玩笑、建议、菜肴甚至金钱,他们可是连高兴都来不及。与此同时,我自己倒也算得上身为人父。那时,我的姐姐琼和一个名叫哈珀的男人结婚没多久,而这场婚姻正濒临瓦解。在这个不幸的家庭中,我所保护的对象和亲密伙伴就是我那三岁的外甥女莎莉,琼的独生女儿。大公寓里——琼已经继承了一半遗产,我的那一半则由他人托管——这对夫妇的争吵与和解如潮汐般汹涌澎湃,此起彼伏,把可怜的小莎莉冲到一边。自然而然地,我和这个被遗弃的孩子同病相怜,于是我们经常舒心地窝在一间俯瞰花园的大房间里,她玩玩具,我听唱片。而每当公寓彼端的某处风云变色、使得我们不想抛头露面的时候,我们就躲进一间小厨房里。对我来说,照顾她是件好事,它使我保持了文明的品性,并让我远离自身的烦恼。直到二十年后,我才感到自己扎下根来,就像当年照顾莎莉时那样。最令我享受的时光是在琼和哈珀离开公寓外出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我会读故事给莎莉听,直到她悠然入睡,然后我就坐在靠着敞开的落地窗的大写字桌前,开始做我的家庭作业,迎面的窗外飘着树木散发的清香和车辆带起的尘埃。那时,我正在埃尔金新月街上的比密西——一所喜欢自诩为“学院”的学校——念书,正在为高考苦读。当我停下手中的作业,回头朝身后望去时,我看见,在光线逐渐黯淡下来的房间里,莎莉仰面睡着,被单和玩具熊都掀到了膝盖下面,四肢完全展开,一副纯洁无邪、毫不设防的可爱姿势。在我眼里,这是她在自己那仁爱善良的小小世界中对我百分之百的信赖。一股狂野而令人痛苦的保护欲望激励着我,令我一阵心痛,而且我确信正是出于这种欲望,我后来才会生了四个孩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你一辈子都是孤儿身;照料孩子就是照料你自己的一种方式。
有时,出于愧疚或是与哈珀和解后余留的满心爱意,琼会突然闯进来,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会把莎莉抱到公寓里属于他们的那一边,柔声细语地逗她,拥抱她,给她做出种种毫无价值的承诺。每当这时,一种失去归属的空虚感就会如黑夜般袭上我的心头。我没有躲闪逃避,也没有像其他孩子们那样去靠电视排遣寂寞。我会遁入茫茫夜色,沿着拉德布罗克·格罗夫大街,前往目前对我最为热情的那户人家。二十五年过去了,当我重温往事时,在脑海里所浮现出来的,是那些用灰泥粉刷过的灰暗公寓,有些墙面已经斑驳脱落,有些却依然干净整洁,也许是在波伊斯广场吧。接着,前门打开了,一道强烈的黄色灯光照亮了站在阴影中的那个面色白净、已经身高六英尺、脚下趿拉着那双切尔西球靴的年轻人。哦,晚上好,兰利夫人。很抱歉来打扰您。请问托比在吗?托比多半正和他的一位女朋友混在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们呆在酒吧里。于是我连称抱歉,开始沿着门廊台阶往回走,这时,兰利夫人把我叫了回来。“杰里米,你想不想进屋来坐坐?来吧,和我们这两个无聊的老东西喝上一杯。我知道汤姆看见你会很高兴的。”几下惯常的推却之后,这只六英尺高的布谷鸟还是进去了。他被领着穿过大厅,走进一间汗牛充栋的巨大书房,房里还装饰着叙利亚式匕首,一张萨满教巫师使用的面具,以及一根亚马逊吹管,里边装有头上浸满箭毒的飞镖。敞开的窗户旁,托比四十三岁的父亲正坐在台灯下,读着普鲁斯特或修昔底德或海涅的原作。他微笑着站起身来,向我伸出手掌。
“杰里米!见到你真高兴。一起来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吧。坐这儿来听听这个,告诉我你怎么想。
”他很热情地与我攀谈,找着与我的学科(法语,历史,英语,拉丁语)有关的话题。他把书往前翻了几页,翻到了《在少女们身旁》中的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回旋语句,而我呢,也同样希望能表现自己并被他接受,便直面这一挑战。他和蔼可亲,不时地给我做些纠正。后来我们可能还谈论起了斯科特一蒙克里夫,而兰利夫人则会端着三明治和茶水走进来。他们向我询问了莎莉的情况,也想知道在哈珀和琼,这对他们从未碰过面的夫妇之间,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汤姆·兰利是位外交官,在外办工作。他曾先后三次旅居国外,执行外交事务,回国后便常居白厅。
布兰达·兰利操持他们和和美美的一家,还教授大键琴和钢琴课程。就像比密西学院里我许多朋友的父母们一样,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充裕富足,在我这个收入中等、藏书全无的人看来,这简直是一种高雅理想的生活。
……照理来说,理性思维与感性领悟本就相互分离,在它们中间挑起对立并无道理,但这样讲却毫无作用。伯纳德和琼向我阐述的理念往往水火不容,难以并存。比如,伯纳德坚信,是人类的思想指引着人类生活的方向,而不是什么固有的天性或者宿命的缘故。
琼无法接受这一观点,在她看来,生命存在特定的目的,敞开自我去拥抱这一目的,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同时认可这两种观点是行不通的。在我眼里,相信一切,不作出任何选择,就等同于什么也不信。
我不能确定,我们这处于千年之交的文明,是因过于崇尚信仰还是过于缺乏信仰而遭致诅咒,也不知道到底是像伯纳德和琼这样的人,还是像我这样的人才造成了祸端。
但是,假如我不宣告我坚信真爱可以改变人生,可以救赎人生,那就有违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谨将这部回忆录献给我的妻子詹妮,还有我那仍被童年阴影所困扰的小外甥女莎莉,祝愿她也能找到这份真爱。
通过婚姻,我走进了一个分裂的家庭,这个家庭中的三个孩子出于自我保护,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双亲。而我与岳父母过于亲近、有些夺人所爱的做法,给詹妮和她的弟弟们带来了某些不悦,对此我深表歉意。我曾有若干冒昧之举,其中最为冒昧的是将某些绝不该记载的交谈一一作了陈述。然而,由于我对他人,甚至对我自己表明我“上岗”的机会少而又少,故而几多轻率冒昧之举在所难免,绝有必要。我恳望琼的幽魂,还有伯纳德的幽魂——假如与他的一切信念相左,他个人意识的某些要素继续存在了下来——能够宽恕我。
用户评价
这部作品的氛围营造得相当到位,一开始读进去就仿佛被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作者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细腻入微,那些潜藏在日常表象下的焦虑与不安,都被他用近乎残酷的笔触一一剥开。你会跟随主角一起在迷雾中摸索,感受那种难以言喻的疏离感。故事的节奏把握得很好,张弛有度,偶尔会突然抛出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转折,让你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之前读到的所有细节。读完之后,那种久久不能散去的压抑感,像极了夏日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漓尽致却又让人心生回味。它不像那种情节飞速推进的商业小说,更像是一幅需要你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油画,每一笔触都蕴含着深意。我特别欣赏作者对环境的描摹,那种冷峻而又充满诗意的笔法,使得整个故事的背景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方,它本身也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会呼吸的角色,时刻影响着角色的命运和选择。
评分整体而言,这本书带来的情绪体验是复杂而深远的。它不像一部读完就合上的消遣读物,它更像是一段旅程,结束后你发现自己带回了新的思考和一些难以名状的“后遗症”。它挑战了我们对于“叙事完整性”的传统期待,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探讨了创伤如何塑造和扭曲个体身份。我非常欣赏作者的克制,他没有滥用戏剧性的场面来煽动情绪,而是通过气氛的积压和细节的堆砌,让那种沉重感自然而然地渗透出来。读完后,我会花很长时间去回味其中几段标志性的场景,它们像电影镜头一样清晰地烙印在脑海里。对于那些寻求精神刺激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厚礼,它要求你付出努力,但回报的,是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对道德困境的探讨。它毫不留情地将人性中最复杂、最不光彩的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只有一团纠缠不清的灰色地带。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跟随情节发展,不如说是一场深入自我拷问的旅程。你会忍不住代入角色的处境,思考在那种极端的压力下,自己会做出何种选择。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更深刻的问题。每一次翻页,都像是在揭开一个新的迷宫入口,让你对“真相”的定义产生动摇。特别是对于记忆与现实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巧妙,真真假假,虚实难辨,让人不得不怀疑,我们所坚信的一切,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般牢不可破。这种智力上的挑战和情感上的冲击,使得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极为丰富和立体。
评分这部作品的结构设计堪称一绝,它仿佛是一个精密的钟表,每一个齿轮——无论是时间线的跳跃,还是不同人物视角的切换——都咬合得天衣无缝。它不是线性的叙事,更像是一个不断向外扩散的圆,每一次扩展都让你对中心事件有了更全面、但也更令人不安的理解。作者对于“缺失”的表达非常到位,故事中总是有意无气地留下一些关键信息的空白,这些空白反而比明确的叙述更能抓住读者的心。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拼图中,你拥有的碎片很少,但每一个碎片都异常清晰,迫使你去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那些巨大的鸿沟。这种开放式的叙事手法,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参与感和主动性,让你感觉自己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故事的共同建构者。这种文学上的冒险,我非常享受。
评分从语言的层面来看,作者的文字功力简直令人叹服。那些句子,时而如冰冷的匕首般精准刺入核心,时而又化为温柔的溪流,缓缓流淌过心灵的创伤。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最平凡的场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措辞,瞬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层面。我尤其喜欢他处理内心独白的方式,那种跳跃性思维和碎片化的叙事,完美地模拟了人类在困顿中思绪万千的状态。这本书的节奏感非常独特,它不急于让你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是耐心地引导你感受“此刻”的重量。读起来有点费劲,需要集中十二分的注意力去捕捉那些潜藏在字里行间的微妙暗示和讥讽,但一旦进入状态,那种被高质量文学作品所包裹的感觉,是其他类型小说难以替代的。这绝对是一本需要二刷的书,因为初读时错过的那些语言的精妙构造,在回味时会给你带来新的惊喜。
评分[ZZ]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sm]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SM],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 书的内容直得一读[BJTJ],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NRJJ],内容也很丰富。[QY],一本书多读几次,[SZ]。 快递送货也很快。还送货上楼。非常好。 [SM],超值。买书就来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BJTJ],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书是非常明智的。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抹杀了。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中国人讲“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思想,“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从而获得对于“道”的体悟,“唯道集虚”。这在传统的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中国古代的绘画,提倡“留白”、“布白”,用空白来表现丰富多彩的想象空间和广博深广的人生意味,体现了包纳万物、吞吐一切的胸襟和情怀。让我得到了一种生活情趣和审美方式,伴着笔墨的清香,细细体味,那自由孤寂的灵魂,高尚清真的人格魅力,在寻求美的道路上指引着我,让我抛弃浮躁的世俗,向美学丛林的深处迈进。合上书,闭上眼,书的余香犹存,而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缀叶如雨”的冲淡清幽境界。愿我们身边多一些主教般光明的使者,有更多人能加入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世界需要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我们的生活,[NRJJ]希望下次还呢继续购买这里的书籍,这里的书籍很好,非常的不错,。给我带来了不错的现实享受。希望下次还呢继续购买这里的书籍,这里的书籍很好,非常的不错,。给我带来了不错的现实享受。
评分很好很实惠,我喜欢!!!
评分不错 可以的 还行吧 哈哈哈
评分好书,正版,快递额,不用说,快,,建议买这本,买一套都可以!!!
评分收藏双语版,包装不错,物流似乎遇上京东卖书爆仓,有点慢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自从在一个公众号里读到这个作者的一段文字,秒变狂热粉丝。双11大量收集他的作品。大量心理活动的描画,赞!慢慢地读吧。
评分1970年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后,恰逢东英吉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课程改革,著名批评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开设了首期“创造性写作课程”(creative writing course),学生无需提交毕业论文,只要交上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合格者即可戴上硕士帽。这简直是量身度造的绝佳机会,麦克尤恩即刻报名,并于1971年获得文学创作硕士学位。迄今为止,东英格兰大学创造性写作班最成功的毕业生,依然是麦克尤恩,紧随其后的是日裔英语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u)。
评分好书,618用券买书简直白菜价,还会继续在京东买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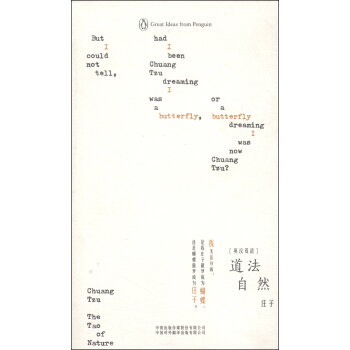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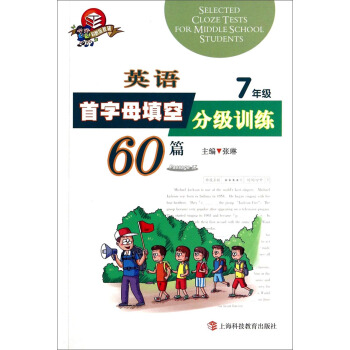

![义教教科书:英语(一年级上册 一年级起点) [Englis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92113/5488196cN505abfb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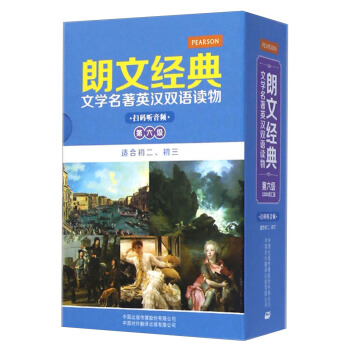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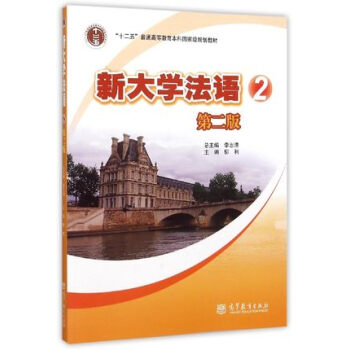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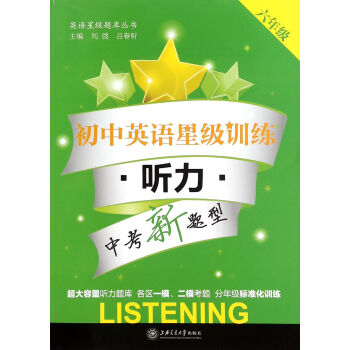





![迪士尼英语情景图解单词书 [4-8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70345/57ce55deN31a3c96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