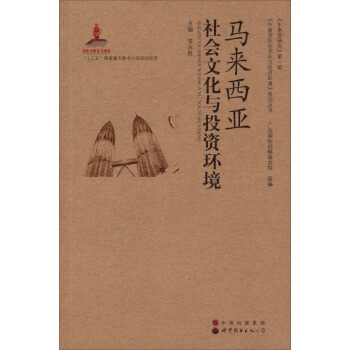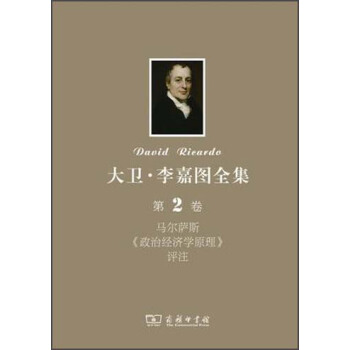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介绍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作者介绍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等。
关联推荐
《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新浪网“2013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目录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第-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第五讲 世民治国:zui盛的王朝与zui小的政府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zui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三个zui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跋
在线试读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zui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zui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zui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zui早。”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
用户评价
翻阅《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典藏版)》,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沙盘,看着吴晓波先生用他的笔触,细致入微地描绘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发展的起起伏伏。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列举了历代王朝的经济成就,更着重于分析那些变革过程中的得失,以及那些被忽视的、甚至是失败的尝试。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一些历史转折点的经济原因的深度挖掘,例如,为何某个时期会出现经济繁荣,又为何会因为某种政策的失误而走向衰退。这种“得失”的视角,让我看到历史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反复。吴晓波先生的叙述,既有史学家的严谨,又不乏故事的趣味性,能够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他能够将一些看似宏大的经济概念,通过生动的语言和翔实的案例,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运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本书让我明白,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关乎政策、技术、制度,更关乎人性的复杂。阅读这本书,就像是在上了一堂生动的经济史课,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了更深的思考。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拿到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典藏版)》的时候,我并没有抱有多大的期待,毕竟“经济”这个词听起来就有些距离感,我更偏爱那些充满人文关怀或叙事性的作品。然而,当我翻开第一页,便被作者吴晓波先生的独特视角深深吸引。他没有用那些晦涩难懂的经济术语,而是从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人物入手,将抽象的经济概念具象化。我尤其喜欢他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经济政策的“得”与“失”的辩证分析,这让我明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并非一帆风顺,每一次的进步都伴随着代价,每一次的错误也可能埋下伏笔。书中对不同朝代经济制度的对比,让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也让我看到了其中的一些必然规律。例如,在讨论某个朝代因为过于依赖某种单一经济模式而导致的衰落时,我联想到了当下的一些产业结构问题,不禁让人拍案叫绝。吴晓波先生的文字功底相当了得,读起来流畅自然,却又信息量巨大。他能够将复杂的经济史梳理得条理清晰,并且深入浅出,让即使对经济学不太了解的读者也能轻松读懂。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更是一本关于“如何发展”和“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智慧之书。
评分我必须承认,《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典藏版)》带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离不开对其经济发展的深入剖析,而这本书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吴晓波先生以宏大的视角,将中国两千多年的经济史浓缩于一卷之中,却又不失细节的精彩。他不仅仅是讲述了“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带来了什么影响”。我特别欣赏他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演变过程的梳理,从重农抑商到海禁政策,再到洋务运动的艰难起步,每一个节点都充满了故事性和深刻的洞察。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像是走入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变革博物馆,亲手触摸到那些曾经影响中国命运的政策和思想。书中对于那些曾经辉煌一时,最终却因为经济上的停滞或失误而走向衰落的朝代,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这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的走向,甚至对于我们当下如何应对经济挑战,都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我喜欢书中那种不回避问题、敢于直面历史教训的勇气,这种勇气也体现在吴晓波先生的笔触之中。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政治和文化的层面,而是有了更坚实的经济根基。
评分坦白说,我之前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了解非常有限,总是觉得那些关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论述过于枯燥,难以提起兴趣。《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典藏版)》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看法。吴晓波先生的叙述方式太有感染力了,他把一个个看似遥远的历史事件,与经济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让我看到了历史人物的决策是如何受到经济因素影响的,也看到了经济政策如何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命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对不同时期税收制度的分析,这让我明白了为何有些朝代能够国富民强,有些朝代却民不聊生。此外,书中对土地制度的讨论,也让我认识到土地在古代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吴晓波先生的文字,如同穿针引线,将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经济碎片,编织成一幅宏伟的画卷。他不仅仅是呈现历史,更是在解读历史,让我看到了经济发展背后的人性、欲望、以及那些充满智慧或愚昧的选择。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远超我的预期,它让我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评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典藏版)》简直让我醍醐灌顶!我一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感到好奇,但又常常被那些繁杂的细节和宏大的叙事所淹没,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切入点。《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这本书,在我看来,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者,娓娓道来,将那些被时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经济变革,以一种极其生动且逻辑严谨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作者吴晓波先生的笔触,既有学者般的深度,又不失故事性的吸引力。他不是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深入挖掘每一次经济变革的驱动力、过程中的博弈、以及最终带来的得与失,特别是那些被历史掩埋的“失”,往往更具警示意义。读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亲眼见证了唐朝的开放与繁荣,宋朝的商业文明,明清的保守与衰落,每一个朝代的兴衰,都能从经济的角度找到深刻的解释。特别是书中对税制、土地制度、货币政策等具体经济措施的分析,让我对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候,读着读着,会不禁感慨,古人的智慧与局限,在经济发展这条道路上,其实和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本书绝对不是那种堆砌史料的枯燥读物,而是能够引人深思,甚至对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能提供不少启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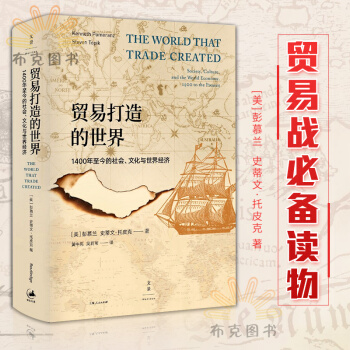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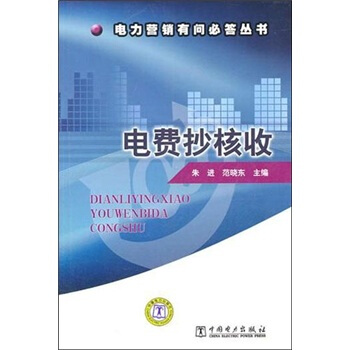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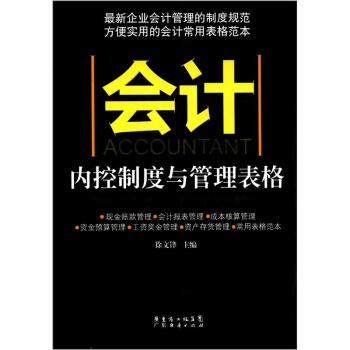

![关务通·监管通关系列丛书:通关疑难解惑720例 [720 FAQs of Cleara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45369/rBEQYVGTSCkIAAAAAARJt_24QowAABOcQHm_-UABEnP75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