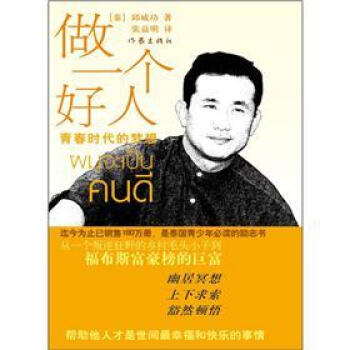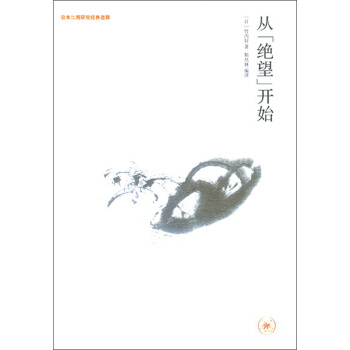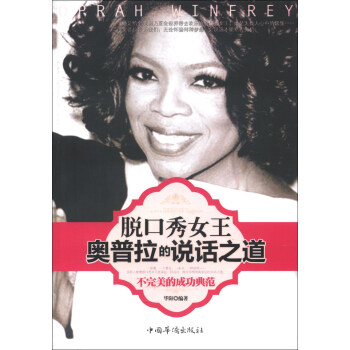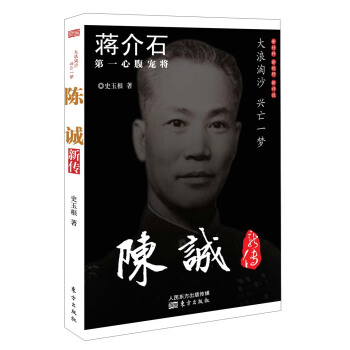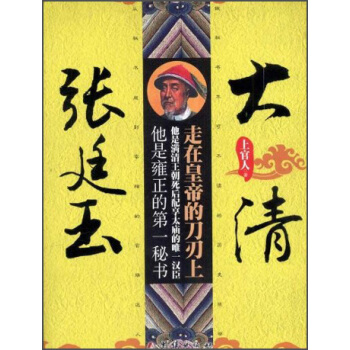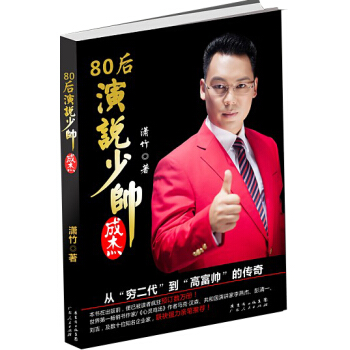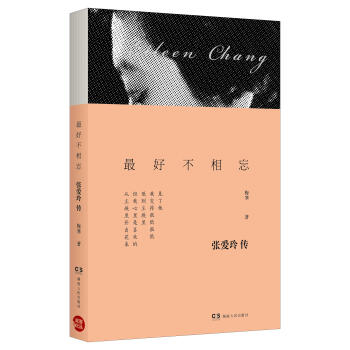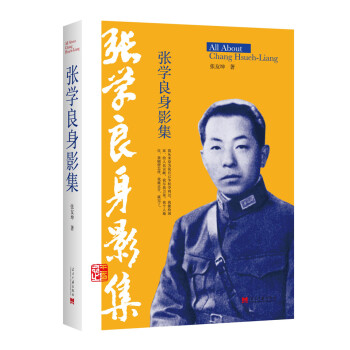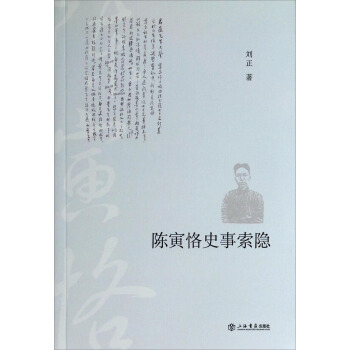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是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自传性质的作品,几易稿本,本次出版前,作者才正式定稿。《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涉及的不仅是作者个人及其家族的经历,更有一个时代的风雨云烟,作者以见惯白云苍狗之后的淡然,书写了共和国以来的世事苍茫。大量收入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老照片、新照片,展现了不可多得的人事记忆。书中彩插为刘心武先生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可令在阅读之余玩赏。
内容简介
《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自传性作品,一部极为难得的文学佳构。本次出版前,作者才正式定稿。自新时期以来,刘心武先生以自己的创作和学术研究,参与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文明迈进,从而也成了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三十年斗转星移,而作者思想不息,时发其新。在这部作品中,他以非常平静的心态,饱满的情感,纯净的文字,坦陈自己的人生经历:童年生活、家族记忆、亲人呵护、求学经历、人际交往、文学创作、红学研究,乃至由此引起的各种诡诞风波。虽然俱是个人的经历,但天地万物、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人世的百态,尽在笔端,往事并不如云烟。
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05年起陆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系列节目共计61集,并推出同名著作,2011年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引发国内新的《红楼梦》热。除小说与《红楼梦》研究外,还从事建筑评论和随笔写作。
目录
是的,这就是我 (自序)
我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
祖父、父亲和我--挣不脱的生命链环
炸出一个我
父亲脊背上的痱子
能够善良
免费午餐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美丽的藩篱 41 神圣的沉静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楸树花
我的元记忆
童年:火的记忆
小颗颗
硬木棍
隆福寺的回忆
哄堂大笑中的启示
白石的乳汁
恐怖
羞涩
“鸡啄米”
有《第四十一》吗?
从“豆腐块”开始
我给小哥当哑奴
闲为仙人扫落花
姐弟读书乐
瓜菜代·小球藻
风雪夜归正逢时
走出贝勒府
我的平民朋友
惜别老罗
五十自戒
我爱夜凝珠
关于《班主任》的回忆
讲那照片的故事
1978年春:为爱情恢复位置
珍藏激动
何处在涌泉?
守候吉日
从1985年那一晚说起
永失我车
我的心理保健操
好一趟六合拳
那边多美呀!
抚摸北京--刘心武与北京
红故事
精彩书摘
风雪夜归正逢时“丫就是一中学教员!呸!啐他一口绿痰!”
这是2007 年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则针对我的“帖子”。
我真的没有想到,奔70岁去的人,还能再次引发出轰动,这就是2005年至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里断续播出了四十四讲《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是我一生中的第几次轰动?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尽管事后的轰动程度出乎我自己意料,但我得承认,那效应正是我谋求的。我写出、投出《班主任》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下,那真是一次冒险,而幸运的是,只遭受到一些虚惊,总的来说,是“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了。第二次,是1985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我又在《人民文学》上连续发表了纪实小说《5o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前一篇至今仍让许多球迷难以忘怀,有人说那是中国大陆“足球文学”的开篇作之一;后一篇则被认为是较早捕捉到改革所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试图以相互体谅来化解社会风气的代表作。正当“春风得意马蹄疾”时,1987年我刚当上《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就爆发了“舌苔事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本台刚刚收到的一条消息”宣布,我因此被停职检查。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都将这一条新闻放在头版,跟着,我在境外的“知名度”暴增,这样的轰动对于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来说,那是名副其实的惊心动魄。有谁会羡慕这样的轰动呢?从此低调做人,再不轰动才好。可是,没想到花甲后竟又“无心插柳柳成行”,因《揭秘〈红楼梦〉》再次轰动。
我曾对不止一个传媒记者说过,我上《百家讲坛》是非常偶然的。但竟没有一家媒体把我相关的叙述刊登出来。这是为什么?不去探究也罢。现在我要借这篇文章把情况简略地描述一下。我研究《红楼梦》很久了,从1992年就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又陆续出了好几本书。2004 年,我应现代文学馆傅光明邀请,去那里讲了一次自己从秦可卿这个角色入手理解《红楼梦》的心得。其实傅光明那以前一直在组织关于《红楼梦》的讲座,业界的权威以及有影响的业余研究者,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那时现代文学馆是跟《百家讲坛》合作,每次演讲电视台都同步录像,然后拿回去剪辑成一期节目,那些节目也都陆续播出,只是收视率比较低,有的据说几乎为零收视。傅光明耐心邀请我多次,都被我拒绝,直到2004 年秋天,我被他的韧性感化,去讲了。当时也不清楚那些录像师是哪儿的,心想多半是文学馆自己录下来当资料。后来才明白那就是《百家讲坛》的人士。《百家讲坛》把我的讲座和另外五个人的讲座剪辑成一组《红楼六人谈》,我的是两集。播出时我看了,只觉得编导下了工夫,弄得挺抓人的。没想到过些天编导来联系,希望我把那两集的内容扩大,讲详细些。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那两集的收视率出乎意料地高。电视节目不讲收视率不行啊,观众是在自己家里看,稍觉枯燥,一定用遥控器点开。我想展开一下也好,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研究一定高明,但《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峰,先引发出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阅读它的兴趣,是我应尽的社会义务。我录制讲座时,以蔡元培“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为基本格调,以袁枚“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为贯穿姿态,为吸引人听,我设计了悬念,使用了现场交流口吻,每讲结束,必设一“扣子”,待下一讲再抖落“包袱”,这样做,引出了不小的收视热潮。后来有传媒称我录制节目时,常被编导打断,要求我设悬念、掀高潮云云,这完全是误传,我从未被编导打断过,所谓“《百家讲坛》是'魔鬼的床',你长把你锯短,你短把你拉长”,这体验我一点也没有,总之,编导们让我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从未进行过干涉。当然,他们在剪辑、嵌入解说词、配画、配音等方面,贡献出聪明才智,才使我的《揭秘》系列播出后,出现了自称是“柳丝”的“粉丝群”。
前些时一位美国来的朋友约我到建国饭店聚餐,餐后饮咖啡时,她说朱虹要来看她,听说我在,希望能见上一面。朱虹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语文学部分的负责人,她基本上不搞英译中而擅长中译英,她先生柳鸣九则是法国文学专家,两口子都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于名牌机构,到国外也是到名牌学府做访问学者,或与当地文化名流直接对话。我对他们都很崇敬。但在他们面前也总有些自觉形秽。我就对美国来的朋友推托说,替我问朱虹好吧,我还是要先走一步。谁知就在这时,朱虹已经翩然而至。她坐下来就说,是我《揭秘〈红楼梦〉》的“粉丝”,柳鸣九没有她那么痴迷,但也一再说“当今若从八十回后续《红楼梦》,非刘心武莫属”。又说,为了看每天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开播的《百家讲坛》,她总是提前吃好午餐,后来发现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有下午四点半的《百家讲坛》,就为自己安排相应的下午茶,边饮边看,“作为一种享受”。我听了受宠若惊。她可不是一般的“粉丝”啊。她又说特意为我带来了美国电影《时光》的光盘,里面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由影星妮可·基德曼饰演。为什么推荐我看这部电影?她说伍尔芙的遁世正是“沉海”。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塑造的奥菲利亚是“沉溪”。她觉得我根据古本线索分析出曹雪芹所构思的林黛玉的结局为“沉湖”,有一定道理,“古今中外,薄命女子多丧水域,或许其中有某些规律,也未可知!”交谈到这个份上,我不能不相信,朱虹女士对我的红学研究的鼓励是认真的,绝非客气。
正当我获得极大心理满足时,朱虹忽然淡淡地来了句:“你当年是北京师院毕业的吧?”
这就戳到了我的痛处。不知道她和那位美国朋友是否看出我的尴尬。还好,朱虹并没有等待我的回答,又说起别的来。
有一利必有一弊。轰动会引来“粉丝”也会引来“愤丝”。讨厌我、抨击我的人士里,有的就“打蛇打七寸”,不跟我讨论观点,只追究我的“资格”,文章开头所引的那个“热帖”就是一例。
我“学历羞涩”。我1959年进入、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尽管这所学校后来部分并入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但我只念了两年专科就分配到北京十三中担任语文教师。至今我填写任何表格,上面若有“学历”一栏,都无法填入“大本”,只能老老实实地写明“大专”。
从北京师专毕业到北京十三中任教,吸粉笔末有十三年之久。之所以能写出《班主任》,当然与这十三年的生命体验有关。但我执笔写出和发表出《班主任》的时候,已经不在十三中了,我那时已经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名编辑。最近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些报道提到1977年1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登出《班主任》,还说“作者当时是中学教师”。《班主任》刊发后很轰动,那时候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士都读过它,但后来许多人或兴趣转移或没有空闲很少甚至不再阅读文学作品,任凭我如何辛勤创作,持续发表作品,乃至于写出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对不起,他们只对《班主任》有印象,因此遇到我不免就问:“你在哪个中学教书呀?”改革开放以后,大城市的中学,尤其是所谓重点中学,包括我曾任教的北京十三中,教师的受尊重程度和工作报酬都大幅提升,但总体而言,中学教师在社会文化格局里,仍属于比较下层的弱势群体,“他不就是一个中学教师吗?”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样的话语还算客气的,像我文章开头的那一声恨骂,“丫”是北京土话“丫头养的”的简缩,含义是“非婚私生子”,“中学教员”被骂者视为“贱货”,他这样对我恶骂,似有深仇大恨,其实我真不知道究竟我于他有何妨碍?说要啐我“绿痰”,倒让我忍俊不禁了,能啐出“绿痰”,他得先让自己的肺脓烂到何种程度,才能够兑现啊?
师专学历,中学教员出身,这是我的“软肋”,鄙我厌我恨我嫉我的人士,总是哪里软往哪里出拳。
也有绝无恶意的说法,指出我和《百家讲坛》上的一些讲述者因为曾经当过或现在仍是中学教师,所以“嘴皮子能说”。中学教师面对的是少男少女,深入必须浅出,寓教于乐才能受到学生欢迎。而电视观众的平均文化水准正是“初中”,作为一档必须通俗化而且具备一定娱乐性的节目,《百家讲坛》找几位因教中学而练就的“能说会道”者充当讲述者,实属正常。
但在一些人意识里,不正常的是,“不就是教中学的嘛”,却因这一档节目而获得暴红的社会知名度,由节目整理出的著作热销,名利双收,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我而言,“曾经沧海难为水”,去录制《百家讲坛》,有一搭没一搭的,我早在1977 年就出过名了,以前的书虽然都没有《揭秘》那么畅销,但种类多,累计的稿费版税也很不少,名呀利呀早双收了,这绝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因《揭秘》闹出的风波很令我烦心,我始终躲着传媒,尽量少出镜,躲到一隅求个清净。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是非总要惹上身来。别的且不论,我的低学历又被人拎出来鄙夷,确实心里不痛快。
“那么,1959年你考大学的时候,怎么就只考上了师专呢?”这是无恶意者常跟我提出的问题。很长时间里,我无法圆满地回答。因为,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各科成绩一直不错。是高考时失误了吗?考完后,对过标准答案,挺自信的。是志愿填得不合理?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吧。那时候,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到头来以服从国家分配为己任,只考上个师专,倒霉,但还是乖乖地去报到。
没想到去报到那天,在学校前楼的门厅里,遇到了六十五中同届不同班我签名的字体很漂亮,真的。演讲后为听众签名的一位同学,他也被师专录取,我跟他打招呼,他却爱答不理,满脸鄙夷不屑,我再试图跟他搭话,他从鼻子里哼出一声:“你也有今天?”然后大步离开我,仿佛逃避瘟疫。
我深受刺激。但事后细想,也不奇怪。就在两三个月前,大家准备高考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了广播剧《咕咚》,那剧本就是我编写的。在那以前,高二的时候,《读书》杂志刊出我一篇书评《谈〈第四十一〉》,到高三,我的短诗、小小说,常见于《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版面。那位同届不同班的同学,高考前见到我满脸艳羡、钦佩的谄笑,甚至说:“北京大学中文系不招你招谁啊?”但是,等到揭榜,他认为自己被师专录取毫不奇怪,而我竟沦落到跟他一起跑去报到,真是“今古奇观”,那是我的“现世报”,也是他的“精神胜利”-他终于从我也有那样的“今天”里,获得了一种原来失却的心理平衡。
记得收到师专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拿给母亲看,她说了句:“我总觉得我的孩子能上北大。”
我伤了母亲的心。然而最深的痛楚还是在我的身上。在六十五中时,我和同班的马国馨最要好,他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他到清华报到后立即往师专给我寄了封信,希望继续保持联系,我把那封信撕了,直到30多年后,才再次跟他见面,那时候他已经是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设计出了亚运会启用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筑群,而我那时不仅凭借小说获得名声,也从事建筑评论,在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里,我高度评价了他的作品。记得应邀参加一次建筑界的活动结束后,我约他和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建筑师-到天伦王朝饭店大堂茶叙,他这样向他的夫人介绍我:“六十五中同班的,他那时候功课棒着啦!”我很感激他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那时候就只配被师专录取。
上师专,教中学,这也许是我的宿命。我从少年时代就想当作家。“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没上成北京大学或别的名校,难道我就不能自学成才吗?何况北京大学或别的名校的中文系也并不承担培养作家的任务。记得老早就看到过孙犁的说法,大意是写文学作品不一定需要高学历,具备初中文化水平就可以尝试。我激赏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认同他的说法。是的,作家的养成主要靠社会这所大学校,作家最必需的素养是对人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构思作品时有悟性,驾驭文字时有灵性,就可能成为不错的作家。我在“师专生”、“教中学”的压抑性环境中顽强努力,终于成为一个无论如何无法一笔抹杀的作家而自立于社会。我知道有的人无法承认我以作家而存在的事实,甚至恨不能将我撕成两半,但也确实感受到有不少人喜欢我的作品,包括我对《红楼梦》的揭秘,乃至喜欢我这个人本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天地又有仁,它让“有志者事竟成”的故事一再上演。
1988年3月,香港《大公报》纪念复刊四十周年,邀请内地一些人士为参与纪念活动的嘉宾,受邀的有费孝通夫妇、钱伟长夫妇、吴冷西夫妇,另外是两位不带夫人的相对年轻许多的人士,其中年龄最小(45岁)的是我。吴冷西当时是中国新闻界的老领导、大权威,他的夫人肖岩,曾任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我上师专时,常坐在下面听她在台上作报告。此前我从未近距离地接触肖岩校长,更不曾设想能跟她平起平坐,寒暄对话。肖岩知道我写过《班主任》,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并且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我在1987 年初惹出的“舌苔事件”那时已经了结,我在1987年9月复职),把我当作一个“文坛新秀”十分尊重,但有一点是她未曾知道的,我主动告诉她:“肖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是1961 年北京师专中文科的毕业生。”这让她吃了一惊。她微笑地望着我,迟疑了一下,说道:“啊呀,真是鸡窝里飞出了凤凰啊。”我听了感慨万千。怎么连肖岩校长也认为北京师专是个“鸡窝”?
是的。我从“鸡窝”里飞出。当然,我未必是凤凰。但能展翅飞翔、开阔视野,也就有幸接触到一些原来对我来说只存在于文学史和教科书的大作家:冰心、叶圣陶、茅盾、巴金、丁玲、艾青、艾芜、沙汀、萧军、孙犁、周立波、秦牧……当然,许多见面都是托赖中国作家协会那时候的一些安排,比如让我和丁玲一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和艾青一起到某国大使馆赴宴……主动被邀请到家里做客的,则是吴祖光和新凤霞伉俪。
大约是在1980 年的某一天,我接到电话,是吴祖光打来的,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欣然前往。那回吴老还邀请了另一位中年作家。还有一位美国汉学家在座,他是专门研究中国评剧的,对新凤霞推崇备至。从那以后我就和吴老有了较密切的来往。我发现他和新凤霞是一对最喜欢自费请客吃饭的文化人。1955年4月3日他们曾在北京饭店请夏衍、潘汉年吃饭,饭局结束不久,潘汉年即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予以逮捕,成为一桩流传甚广的“巧事”。
我早在少年时代就心仪吴祖光。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时,我每天从钱粮胡同的家里步行去学校,总要路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近水楼台嘛,我也就往往“先得月”,屡屡购票观看新排剧目的首场演出,记得1956年北京人艺演出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我看得上瘾,首场看了,后来又买票去看。那出戏演的是京剧男旦和豪门姨太太自由恋爱遭到迫害的故事,像我那么大的中学生一般是不爱看甚至看不懂的,但也许是受到父母兄姊喜爱京剧的熏陶,我却觉得那戏有滋有味。至今我还记得北京人艺当年演出的那些场景乃至细节。张瞳和杨薇分饰的男女主角,他们的一招一式固然记忆犹新,就连舒绣文、赵韫如扮演的戏迷小配角,我也闭眼如见。那时头晚看了演出,第二天到了学校,课余时间,我便会和同学们眉飞色舞地聊上一阵。《风雪夜归人》这出戏北京人艺直到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初期,还在上演,我大概去看了第三次,看完聊兴更浓。
吴祖光一生结交甚广,我在他的人际网络中不占分量,他的经历事迹自有研究者描述,对他的评价更有通人发布,我本无资格置喙,但在和他的接触中,有些细琐的事情和只言片语,总牢牢地嵌在记忆里,也许略述一二,能丰富人们对吴先生的认知。
有一次他在他家楼下一家餐馆宴客,我去晚了,记得在座的有香港《明报》记者林翠芬,还有他弟弟吴祖强。闲聊中,我说少年时代读过他的剧本《少年游》,被感动,还记得剧里有一件贯穿性的道具-孔雀翎。他说那时候写剧本,一口气,几天就完成,也不用再改,《少年游》他自己也很看重,可惜上演不多。又说人们多半把他定位于剧作家,其实他自己觉得,他是个电影导演。我说当然啦,《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嘛,还有程砚秋的《荒山泪》。我年纪小,只知道解放后吴先生导演过那样一些戏曲艺术片,林翠芬虽然来自香港,生得也晚,和我一样,并不清楚吴先生上世纪40年代,在香港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片导演,像《虾球传》《莫负青春》等贴近社会现实的影片,他导起来都得心应手。吴先生说解放后他从香港回到内地,分配到的单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职务就是导演,而且开头也并不把他视为适合拍摄戏曲艺术片的导演,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拍摄表现天津搬运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故事片《六号门》,他看了剧本,觉得是个好剧本,应该能够拍成一部出色的影片,但是他跟电影厂领导说,可惜他对这部戏所表现的生活和人物都不熟悉,那也不是短时间“下生活”就能解决问题的,总而言之,“不对路”,于是敬谢不敏。那时候,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电影从业人员,都积极地“转型”,拿演员来说,像原来擅长演资产阶级太太的上官云珠,努力去转型演
了《南岛风云》里的共产党战士,以出演资产阶级“泼妇”而著名的舒绣文,则刻意去扮演了歌颂劳动模范的《女司机》,一些原来只熟悉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导演,则去导演了表现工农兵的影片。吴祖光怎么就不能转型呢?厂领导一再动员,吴先生也带摄制组去了天津,但开机不久,他还是打了退堂鼓。《六号门》最后由别的导演接手,最后拍成了一部很不错的影片。
一次在吴先生家书房,见到一样奇怪的东西,他告诉说是钉书器,怎么会有一尺长的钉书器啊?他家有什么东西需要用它来钉啊?原来,他家不远就是蓝岛商厦,他常去闲逛,有一天到了卖文具的地方,见到这玩意,他觉得真有趣,售货员认出他来,不知怎么地连哄带劝,最后竟说动他买下,他与吴祖光先生在一起,吴先生对1957年他竟牵连到我,感慨万端(1988)把那活像铡刀的东西扛在肩膀上回到家,把新凤霞吓了一跳。但吴先生并不后悔这次购物。“买东西不就图个高兴吗?”他笑着说,“你要不要?你使得着,我割爱!”我自然婉谢。那一回,更觉得吴老是个大儿童。
有回他从湖南访问回来,说起参观领袖故居的情况。在刘少奇故居,他触景生情,想起这位国家主席死得那么惨,坐在故居床上珠泪涟涟。有一起去参观的人,回到宾馆问他:你好像也没被刘少奇接见过啊?是的,他跟刘少奇没什么接触,更谈不到有什么知遇之恩,但那位那么一问,他仍觉得心酸,连说:“太惨了,太惨了。”眼里又泛出泪光。后来又去参观毛主席故居,他从留言簿上看到王光美不久前写下的留言,签名前,王给自己加了个定语“您
的学生”,吴先生说他对此不解。最近我重读199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的《吴祖光选集》,吴老在前面的自序里说,他划右后在北大荒,与难友王正编写了《卫星城》和《回春曲》两部话剧,从剧名就可看出,当然是歌颂“大跃进”的,按我们晚辈的想法,弃如敝屣也无所谓,但吴老却说:“这两个剧本是我们这两个'右派'在北大荒的艰难岁月里,并未灰心丧气,而是淬励奋发,力争上游,充满生活情趣与泥土气息,寓有地方特点的剧作。然而由于时迁岁改,人天变幻,这两个剧本既没有发表,也不会出版,更谈不到在舞台上演出了。”我就想,个体生命镶嵌在一定的时空里,身心都无法遁逃的,王光美“文革”后下笔自称“您的学生”,和到了1995年吴先生仍珍爱自己划右后劳改中的颂歌式作品,其实是可以用同一把钥匙揭秘的。
到晚年,吴老常约浩亮、庄则栋等“文革”后政治上沦落的人士餐聚。有人不解,他不是“文革”中文化部系统钉死的“老右派”吗?那时浩亮是有权有势的文化部副部长,何尝对他施行仁政?吴老自己跟我说到,他是文化部“五七干校”里学龄最长的学员,到最后,全“干校”只剩张庚和他两位还没给落实政策,他脱掉“牛鬼蛇神”的身份,是很晚的事情。但他后来却只把浩亮当成一个“打小看着出息”的“大武生”看待,有回去他家,见浩亮正在厨房里炒拿手菜,但人已患病,体态虚胖,吴老小声对来客们说:“可惜了呀,难得的大武生啊!如今有几个比得上的?”
自恃和吴老比较熟了,有次我就问:“您总这么请客,从来不开发票,您的稿费就经得起这么花吗?”他爽快地回答我:“我这人倒是从来没缺过钱花。我从来自费。”说着从抽屉抓出一把出租车司机撕给他的小票,笑着说:“据说我都能拿去报,可我报销它们干吗?留下它们,原是为了记录每次的行踪,现在发现根本起不到那样作用。”随手就把那些“的票”扔进纸篓。我知道一些餐馆老板对吴老优惠,有家烤鸭店请他题写店名,在那里请客免单,我也曾去过那里的饭局。有人提醒吴老,如此利用他的名人价值,而且往往加上新凤霞,利用“双名人”效应开拓生意,应该签约,让对方付出应有的报酬才是,怎能进餐免单就将他们打发?吴老却置若罔闻。我也曾进言:“您能多富有呢?怎么能如此大方?”他竟干脆给我一个透明度:“把所有的钱加起来,有十来万吧!”那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十来万算什么富有?但吴老和新老二位在待客上依然那么毫不吝惜。
1996年春天,六十五中高中同班同学里的热心人,组织老同学聚会。地点是在当年班长李希菲家里。李希菲和她先生是同一研究所的研究员,都有学科方面的专著问世。他们享受到四室一厅的住房待遇,在她家聚会有足可令大家都舒适的开阔空间。从她家窗户外望,玉泉山的宝塔清晰入目。参加那天聚会的有十几位同窗。大家回忆起1956 年至1958 年的青春岁月,感慨良多。李希菲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大家不客气,觥筹交错,足吃足喝,十分热闹。过了午,李希菲把我单独叫到她家一间离聚会处最远的房间,进了屋,她还关上门,我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么神神秘秘的。
“你知道高中毕业后你为什么没考上好大学吗?”李希菲问我。
事情过去37 年了。没考上好大学,我现在也有相当于教授、研究员的编审职称,而且,在文学上也算取得了一定成绩,尽管那是我的隐痛,但命运给予的补偿也足够令我心平气和、不再追究了。
李希菲却偏要告诉我究竟。看得出,她憋了37年,她觉得到了必须对我和盘托出的时候了。
她细说端详。原来,起因竟是《风雪夜归人》!是吴祖光!
1957 年夏天,那时上高二,一天中午,在教室里,我和一些中午不回家的同学,吃学校食堂给熥热的自带饭食,闲聊里,我又说到北京人艺演出的《风雪夜归人》如何精彩,正在兴头上,忽有一同学截断我说:“你别吹捧《风雪夜归人》啦!吴祖光是个大右派!”
据说,当时我不但不接受其警告,仍然继续坚持宣扬《风雪夜归人》如何好看,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是吗?吴祖光是右派?啊,吴祖光要是右派,那我也要当右派!”
这样的言论,事后被那警告我的同学,汇报给了组织。
到1959 年高中毕业前夕,要给每一位同学写政治鉴定。操行评语是与本人见面的,政治鉴定却是背靠背的。那一年,对于政治上有问题的毕业生,在鉴定最后,要写上“不宜大学录取”字样。李希菲虽然不是政治鉴定的执笔人,但写每个人的鉴定时,作为可信赖的青年团员、班长,她在场。她见证了那一刻:因为有我说过“吴祖光要是右派,那我也要当右派”的文字材料,于是,我的政治鉴定的最后一句就是“不宜大学录取”。
那一年我们班有若干同学的政治鉴定的最后一句和我一样。最惨的是全班功课最好、成绩最拔尖的一位女生。她是青年团员。据说,她的问题之一,是那天我眉飞色舞地大谈《风雪夜归人》,而且说出“反动言论”时,她不仅没有以青年团员应有的战斗性对我予以严词批驳,还一直在微笑着听我乱聊。
那我怎么又还是捞了个师专上呢?后来知道,是那一年师范类院校招不满,于是,只好从写有“不宜大学录取”字样的档案里,再检索一遍,从中拣回一些考分较高而“问题言行”尚可“从宽”的考生,分别分配到一些师范类院校。
而那位那天自己并无不妥言论,只是面对我的“反动言论”微笑的女同窗,却因为作为青年团员“严重丧失政治立场”,连师专都不要,她接到不录取通知书后,就去科学院一个研究室的实验室当了洗试管的女工。1996年春天李希菲家里的聚会她也去了。在李希菲把我叫去个别谈话之前,大家聊起37年来走过的路时,她告诉大家,后来她自学了大学课程,通过了所有相关的考试,取得了本科文凭,如今也获得了副研究员的职称。后来有同窗告诉我,她近年来还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专利登记。她与命运抗争,付出了怎样艰辛的代价啊,而这些代价,竟是为她那个中午面对我的短暂微笑而付出的!
李希菲提供的信息令我震惊。特别是我还牵连到一位女同窗这一情况。
我会在那天说出“吴祖光要是右派,我也要当右派”那样惊心动魄的“反动言论”吗?会不会是汇报者把我的糊涂言论予以“精加工”,才构成了那样一个句子呢?又有谁来找我核对过呢?但这一切都不值得追究了。我,还有那位女同窗,以及另外若干遭遇“不宜大学录取”恶谥的同龄人,毕竟没有就此沉沦,终于穿越历史烟尘,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为社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也从社会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当然也有悲壮的牺牲者。六十五中那一届跟我不同班的一位叫遇罗克的,他敏感地意识到,他之被大学拒之门外-他1959年以后又连着考了几次,无论他考分多高,都无改收到不录取通知书的结局-是政治歧视造成的,而就他个人的具体情况而言,是出身不好-他母亲是资本家,父亲是右派。于是,到了“文革”期间,他逮着一个机会,就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解除以出身把人分别对待的“错误做法”。就因为这篇文章,他被逮捕,并于1970年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到工人体育场示众批斗,然后直接拉往刑场枪毙。1980年他得到平反,但再无机会跟我们一起享受新的岁月。
话说那天李希菲把我单独请到一间屋子里,揭破一个笼罩了我37 年的谜团,我听得发愣,她却意犹未尽,跟我说:“你知道是谁揭发你的吗?我清楚。你要我告诉你吗?”
我立即制止了她。
“事情过去那么久了,你知道一下就行了,你现在也功成名就了,你还会记恨人家吗?”
“不。如果你告诉我,我会恨。所以,恳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告发我的是谁。事情过去37 年了,我记忆已经非常模糊。除了你说出的那位受我牵连的女同学,我完全不记得那天中午还有谁在教室里。今天晚上,我会失眠。我难免要努力去猜测,告发我的是谁呢?是男生,还是女生?那时候像六十五中那样的男女合校而且合班的中学,是很少的。这也好。在是男是女上,就够我瞎琢磨的。但我一定得不到准确答案,即便我锁定了几个当年对我不友好的同学,也终于还是没有办法把我的愤恨落到实处。这样,没有多久,我的探究兴趣,就会被生活里接二连三的新事物消磨。到头来我无人可恨。慢慢的,我会更加心平气和。真的恳求你,千万别告诉我。也永远别告诉别的同学。我们都需要平静,不是吗?”
李希菲懂得了我。她叹了口气说:“也好。其实说出那名字,对我来说也不是轻松的事。我们应该原谅。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好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已经不怕那样的人了。你不是茅盾文学奖都得了吗?什么时候送我一本签名的《钟鼓楼》?”
我们的谈话渐渐走出沉重。我告诉她:“其实我最好的作品还不是《钟鼓楼》,而是《四牌楼》。《四牌楼》里有我们青春期的印迹。我会送你一本《四牌楼》,希望你一定通读。”
李希菲和我回到大家中间。似乎没有什么人在意我们的一度离开。那天的同窗聚会经历了怀旧、伤感、戏谑、兴奋,最后以一派达观结束。
过了些日子,我见到吴老,把37 年前的这段故事讲给他听。听完,他喟叹:“没想到,我竟连累到你-还是个孩子啊!”
这个“孩子”长大成人,而且,现在也成了一个老人。
吴老晚年最喜欢写的四个字是“生正逢时”,他将这一主题的书法作品赠予了很多朋友。
在他于我诞生的那一年-1942 年-创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末尾,两个争取个人自由的主人公虽然都在风雪中回到原来他们相爱的空间,但一个冻饿而死,一个不知所终。这比唐代诗人刘长卿那“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意境悲惨多了。唐诗里风雪夜的归来者尽管饱受严寒饥渴,最后总算进入了温暖的空间,在那里面等候他的不仅会有热茶热饭,更会有亲情友情乃至爱情。生正逢时,也就是尽管有坎坷有挫折,但毕竟穿越风雪迎来了温暖赢得了真情。
现在回想往事,我甚至想深深感谢那位告发我的同窗。如果不是他或她的告发,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生命轨迹,我如果没有上师专,没当中学教员,后来又怎么写得出成名作《班主任》?风雪夜归,正逢吉时。
我现在时时深感遗憾的,反倒是我的自我遮蔽。因为《班主任》引出的反响过度强烈,遮蔽了我后来的所有努力。因为《钟鼓楼》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遮蔽了我更好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尽管我一直在坚持写小说,更有大量随笔,还写建筑评论,但因为《百家讲坛》连续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同名的四部书畅销,又遮蔽了我的其他文字,“你现在为什么不写小说,改行搞红学了?”这是近来随时会遇到的提问。
至于他人对我的刻意遮蔽,比如尽管我当过出版社编辑,当过《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有编审职称,但总还是以师专学历和“不就是个教中学的嘛”来鄙夷我,我已经习惯。但我相信只要不自弃,那么,我的生命之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当然,以己度人,我需要深深检讨的是:自己是否恶意地遮蔽过别人?我在《四牌楼》里,就挖掘过自己内心的恶,并为此进行忏悔。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我不应再计较他人对我的施恶,而应为自己曾伤害过他人-哪怕是无意中,哪怕是因大环境而左右-而深深忏悔,以此救赎。
《四牌楼》里的一章《蓝夜叉》,可以独立成篇。2006年,巴黎出版了它的法译本,我为这个译本绘制了独家插图。其中一幅是小说中的“我”-以我自己为原型-以忏悔的双臂高举象征性的“月洞门”,挣扎于救赎的心灵攀登中。
我不知道会有几多人抛开我的其他文字,找本《四牌楼》来读。我另外还有本《树与林常在》,在其中《走出贝勒府》一章里,我就“文革”中一位女教师自杀,进行了自我心灵拷问。但《四牌楼》也好,《树与林同在》也好,都并没有产生出“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一部分人恨得牙痒”的效应。一颗愿意忏悔的心,是寂寞的。我感到深深的孤独。
2008年12月27日完稿于绿叶居
……
前言/序言
估计愿意看这本书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早就知道了我。多半是1978年前后,读了我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后,就一路追踪阅读我那以后的作品,长篇小说《钟鼓楼》,纪实小说《5·19长镜头》……但是,进入上世纪最后十年,我的生活和写作都边缘化了,这些读者随着年龄增长,也都遇到了人生当中许多的关坎,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文学作品,我后来又写了些什么,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就不大清楚了。但是,2005年,我忽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连续讲了23讲《揭秘(红楼梦)》,跟着又出了两本共36讲的书,引出了不亚于当年《班主任》那样的社会性轰动,有人甚至认为比那时候还更热闹,这些我的老读友或兴奋,或惊讶,因此,他们或者就想了解: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来的?
另一种是非常年轻的一代。我发表《班主任》,甚至因《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及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时候,他们或者根本还没诞生,或者还是没上小学的幼童,他们上到中学,或者刚考进大学,他们对早已边缘化的我,完全不知道,或者只是模模糊糊有点印象,也是因为《揭秘(红楼梦)》,我才弓l起了他们的注意,到2011年年初推出《刘心武续红楼梦》,他们更就好奇,这人是谁呀?什么?以前写过《班主任》,还有《钟鼓楼》?哪儿能找到这些古董?他们开始有了对我揭秘的兴趣。
那么,这本书,就主要是奉献给这些读者的。
这还不是一本自传。我还没到七十岁,也许过了七十岁我会静下心来写一部“从头说起”的自传。但这本由许多篇不是一个时间段里写成的文章组成的书,确实又有自传性因素。
这也还不是一本回忆录。回忆录跟自传是两种文体。自传是把自己的一生展现出来,回忆录可以不去完整地交代自己的生平,而把重点放在写出自己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所见所闻,往往会较多地写到别人别事。那么,这本书却也具有一定的回忆录的因素。
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我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值得一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总之,这就是我。我面对大家,有些羞涩,却也坦然。
我的命运一贯如此:还真有喜欢我的,总在关注、支持、鞭策我,这些人士对我的理解、谅解、指正、宽容、善意、爱护,是我生命赖以存活、前行的宝贵动力,我对他们总是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激之情,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跟他们更加亲近。也真有讨厌我的,以至讨厌到咬牙切齿的地步。这本书当然首先是奉献给喜欢我的人士。但如果有讨厌我的人士愿意翻翻,我会高兴,因为,我总觉得,讨厌我的人士里,其中有一些恐怕是对我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如果读了这些文字,能多少增进些对我的了解,减轻些因讨厌我而生发出的痛苦烦忧,那么,对我来说是得大福气,对他们来说岂不也有利身心健康?当然,无论如何还是要讨厌我的,总会存在,那么,我祝他们幸福,祝他们能在所喜欢的人士那里,去获得快乐。毕竟,人活着应该把更多的情感赋予喜欢,而不是讨厌,爱比恨,肯定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生命的良性运转。
1996年团结出版社出过一本《我是刘心武》,200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在那基础上增加新资料编成一本《我是刘心武》,现在漓江出版社所出的,保留了前两种的精华,又补充了近两年篇幅不菲、内容茁实的新文章,更可以使读者产生亲切感,但愿读者们读后,不仅是知道了一个人,更可以从中多少增添些对时代、社会、人生、命运、人性的感悟。 刘心武
2011年10月8日
用户评价
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真挚。作者没有试图去刻意营造某种戏剧性的冲突,也没有刻意去煽情,而是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将生活最真实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些平凡的日子,那些细微的情感,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被赋予了生命力。我看到了普通人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时所展现出的坚韧,看到了亲情中蕴含的深沉的爱,看到了友情在岁月中沉淀出的珍贵。这些看似寻常的点点滴滴,却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温暖着读者的心。它让我意识到,生活的美,往往就蕴藏在这些最平凡的瞬间里,只是我们常常因为忙碌而忽略了它们的存在。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的心境也变得平和了许多,对生活多了一份感恩和珍惜。
评分书的封面设计就足够吸引人,那种写实的笔触,仿佛真的能感受到凛冽的寒风和厚重的积雪,而“风雪夜归”四个字,又带着一丝沧桑和宿命感。虽然我还没来得及深入阅读,但仅仅从这个名字和视觉感受上,就预感到这会是一段充满故事的旅程。它让我联想到很多古诗词中描绘的孤寂行者,在恶劣天气中跋涉,心中怀揣着某种执念或期盼。“正逢时”这三个字,则又注入了一丝希望和巧合的意味,仿佛一切的颠沛流离,最终都将汇入一个恰到好处的节点。这种对比和张力,使得书名本身就具备了强大的叙事潜质,让人好奇,这风雪夜归之人,究竟是谁?他又将迎来怎样的“正逢时”?是人生转折的契机,还是命运的馈赠?或者,只是一个关于坚持与等待的隐喻?我对作者的笔触充满期待,希望他能将这种意境化为文字,带领读者一同感受那风雪中的温度,和那“正逢时”的感动。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与一位久违的老友进行一场深刻的对话。作者的文笔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它不华丽,不卖弄,却字字珠玑,句句锥心。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他仿佛也在与我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那些关于时间、关于记忆、关于成长、关于失去的思考,如同暗夜里的灯塔,照亮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些角落。我常常会在读到某一段话时,停下来,反复咀嚼,因为那句话里蕴含的哲理,与我曾经经历过的某段人生经历产生了奇妙的共鸣。这种阅读体验,远不止于消遣,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那些曾经被我忽视的细节,那些被我遗忘的情感,都在作者的笔下重新鲜活起来,让我不禁感叹,原来,生活本身就是最伟大的叙事。
评分不得不说,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到位,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投入感。作者擅长运用张弛有度的笔法,时而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波澜,时而又以一种宏大的视角展现时代变迁的背景。这种叙事方式,让故事既有深度又不失趣味。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情节推进上的巧妙安排,那些看似不经意埋下的伏笔,在后文都会一一得到呼应,给读者带来一种惊喜连连的阅读快感。同时,书中对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描绘,也相当生动,让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也能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感受到时代洪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宏大叙事巧妙融合的写作手法,无疑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让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幅描绘时代变迁的生动画卷。
评分翻开这本书,首先触动我的,是作者对细节的描摹。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场景,比如窗外飘落的雪花是如何在玻璃上凝结成冰凌,屋檐下的积雪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堆积,甚至空气中弥漫的淡淡的松木香和煤烟味,都刻画得如此真实,仿佛我置身其中,能够听到风的呼啸,感受到雪的寒冷。这种身临其境的描写,让我对故事发生的环境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而人物的塑造,也同样细腻。那些生活在风雪中的人物,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动作,他们之间的对话,都透露出一种朴素而坚韧的力量。即便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依然保有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亲情的珍视,这种平凡中的伟大,最是打动人心。我尤其喜欢作者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那些隐藏在沉默和寥寥数语之下的情感,被一点点挖掘出来,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温暖。
评分漓江出版社2012年1月推出的几本刘心武的图书中,《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正是这种自说自话的自传,文笔好像洗去铅华的北岛顾城:诗意有一些,淡淡的;北京味有一些,也是淡淡的。《献给命运的紫罗兰》是刘心武先生的散文随笔集,在多舛的命运中,刘先生一直坚持老黄牛般的奋斗精神,这让他苦思冥想的世界观能够自成体系,蔚为大观。他用紫罗兰似的礼物献给命运,可见对世界与前途的乐观。可惜我们的世界却是一个幽默的世界,嫉恶如仇的刘先生每每不屑与冷嘲热讽的批评抗争。
评分因为红楼梦的解读与续写而喜欢刘心武!这书也很好!
评分买给丈母娘,丈母娘很喜欢
评分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评分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评分书籍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装帧精美,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将司空见惯的文字融入耳目一新的情感和理性化的秩序驾驭,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是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自传性质的作品,几易稿本,本次前,作者才正式定稿。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涉及的不仅是作者个人及其家族的经历,更有一个时代的风雨云烟,作者以见惯白云苍狗之后的淡然,书写了共和国以来的世事苍茫。大量收入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老照片、新照片,展现了不可多得的人事记忆。书中彩插为刘心武先生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可令在阅读之余玩赏。从外表到内文,从天头到地脚,三百六十度的全方位渗透,这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自传性作品,一部极为难得的文学佳构。本次前,作者才正式定稿。自新时期以来,刘心武先生以自己的创作和学术研究,参与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文明迈进,从而也成了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三十年斗转星移,而作者思想不息,时发其新。在这部作品中,他以非常平静的心态,饱满的情感,纯净的文字,坦陈自己的人生经历童年生活、家族记忆、亲人呵护、求学经历、人际交往、文学创作、红学研究,乃至由此引起的各种诡诞风波。虽然俱是个人的经历,但天地万物、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人世的百态,尽在笔端,往事并不如云烟。从视觉效果到触觉感受始终追求秩序之美的设计理念把握,估计愿意看这本书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早就知道了我。多半是1978年前后,读了我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后,就一路追踪阅读我那以后的作品,长篇小说钟鼓楼,纪实小说5·19长镜头但是,进入上世纪最后十年,我的生活和写作都边缘化了,这些读者随着年龄增长,也都遇到了人生当中许多的关坎,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文学作品,我后来又写了些什么,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就不大清楚了。但是,2005年,我忽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连续讲了23讲揭秘(红楼梦),跟着又出了两本共36讲的书,引出了不亚于当年班主任那样的社会性轰动,有人甚至认为比那时候还更热闹,这些我的老读友或兴奋,或惊讶,因此,他们或者就想了解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来的另一种是非常年轻的一代。我发表班主任,甚至因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及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时候,他们或者根本还没诞生,或者还是没上小学的幼童,他们上到中学,或者刚考进大学,他们对早已边缘化的我,完全不知道,或者只是模模糊糊有点印象,也是因为揭秘(红楼梦),我才弓起了他们的注意,到2011年年初推出刘心武续红楼梦,他们更就好奇,这人是谁呀什么以前写过班主任,还有钟鼓楼哪儿能找到这些古董他们开始有了对我揭秘的兴趣。那么,这本书,就主要是奉献给
评分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
评分因为红楼梦的解读与续写而喜欢刘心武!这书也很好!
评分书籍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装帧精美,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将司空见惯的文字融入耳目一新的情感和理性化的秩序驾驭,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是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自传性质的作品,几易稿本,本次前,作者才正式定稿。风雪夜归正逢时我是刘心武涉及的不仅是作者个人及其家族的经历,更有一个时代的风雨云烟,作者以见惯白云苍狗之后的淡然,书写了共和国以来的世事苍茫。大量收入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老照片、新照片,展现了不可多得的人事记忆。书中彩插为刘心武先生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可令在阅读之余玩赏。从外表到内文,从天头到地脚,三百六十度的全方位渗透,这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写成的自传性作品,一部极为难得的文学佳构。本次前,作者才正式定稿。自新时期以来,刘心武先生以自己的创作和学术研究,参与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与文明迈进,从而也成了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三十年斗转星移,而作者思想不息,时发其新。在这部作品中,他以非常平静的心态,饱满的情感,纯净的文字,坦陈自己的人生经历童年生活、家族记忆、亲人呵护、求学经历、人际交往、文学创作、红学研究,乃至由此引起的各种诡诞风波。虽然俱是个人的经历,但天地万物、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人世的百态,尽在笔端,往事并不如云烟。从视觉效果到触觉感受始终追求秩序之美的设计理念把握,估计愿意看这本书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早就知道了我。多半是1978年前后,读了我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后,就一路追踪阅读我那以后的作品,长篇小说钟鼓楼,纪实小说5·19长镜头但是,进入上世纪最后十年,我的生活和写作都边缘化了,这些读者随着年龄增长,也都遇到了人生当中许多的关坎,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文学作品,我后来又写了些什么,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就不大清楚了。但是,2005年,我忽然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连续讲了23讲揭秘(红楼梦),跟着又出了两本共36讲的书,引出了不亚于当年班主任那样的社会性轰动,有人甚至认为比那时候还更热闹,这些我的老读友或兴奋,或惊讶,因此,他们或者就想了解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来的另一种是非常年轻的一代。我发表班主任,甚至因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及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时候,他们或者根本还没诞生,或者还是没上小学的幼童,他们上到中学,或者刚考进大学,他们对早已边缘化的我,完全不知道,或者只是模模糊糊有点印象,也是因为揭秘(红楼梦),我才弓起了他们的注意,到2011年年初推出刘心武续红楼梦,他们更就好奇,这人是谁呀什么以前写过班主任,还有钟鼓楼哪儿能找到这些古董他们开始有了对我揭秘的兴趣。那么,这本书,就主要是奉献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